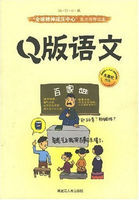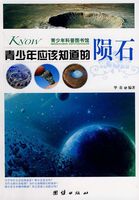当她来开门时,终于可以看清她了。无论怎样,她都不像是个准备要自杀的女人:她的年纪已很大了,但仍娇小玲珑,气质优雅。
她重病在身,病中的她却别有一种美丽:保养良好的肌肤因火气太重而显得容光焕发;那双蓝眼睛在她小巧的面庞上闪亮;头上裹了条素净的白方巾,她自嘲“我是不是像只白秃秃的鸡蛋?”
她刚从外面回来。下午,她先去参加投票,决定是否对学校增加税收;接着她去探望了她那95岁高龄的老母亲。现在,她终于坐下来,安静地等着“临终关怀”机构的一个名叫库克的人来。
她一生都是在无助与困苦中不停地抗争和奋斗。她两岁时就没有了父亲;结婚后几年,孩子们还在上学,她丈夫就无情地抛弃了他们。然而她却没有倒下,她竟然最终成功地拥有了自己的事业,成为一名商界女强人;她还了却了多年的心愿,去非洲和中东历险;她还送儿女们上完了大学……后来,她每周还抽出时间去孤儿院义务劳动,帮助照料那些不能自理的可怜的孩子们。
她毕竟老了,70岁的她如今身患重病,生命垂危,她现在甚至都不能轻松地走到院子里去。然而,她怎么甘心等着让别人来决定她的生死呢?又有谁有这个权力来左右她的身体,左右她的生命呢她唯一信任和允许的就是她的孩子们。女儿是名护士,她早就表示一切尊重母亲的决定。
她的长子一直处于矛盾之中。记得1991年华盛顿提出“安乐死”法案时,他就表示反对。作为医生,他担心这会使人可以合法地去引诱那些心理脆弱的病人轻生。
现在母亲被病痛所折磨,安乐死的确可以使母亲得到解脱,他又怎能阻止母亲的选择呢?他痛苦地在心里对母亲点点头,他的心哭了。
她得到了儿女的支持,于是她开始为生命的终结做准备。她平静地同“临终关怀”机构取得联系,通知他们来人,她要就安乐死作一些咨询。
“临终关怀”派来的库克是个漂亮而丰满的女人,一头鬈发,粉色长裤加上牛仔上衣,充满了活力。库克笑着同她打招呼,面前这个70岁的老妇人一下子深深地把她吸引住了,库克与老妇人相对而坐,她忽然感到一种异样的亲切。库克真是难以想象这样的一个老妇人会怎样吞下药片,怎样平静地等待死亡!库克想,要是自己在最后一刻让老妇人改变了主意该有多好啊但库克忍住了。因为老妇人谈起了自己的病痛,那让库克听来都心惊胆战的折磨,在老妇人嘴里却是那么地平淡。她应该安静地去了。
库克得知她还没有足够的药片,便给她讲了一件事:自己的一位亲戚得了骨癌,最后使用大剂量的镇痛剂而安静地去了。“哦,真不错。”老妇人艰难地笑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她的病日复一日地沉重起来。她挣扎着起草自己的讣告;写好便条,让儿子在她死后交给她的朋友;给女儿写好了信;她还给库克写信,“我将随纽约的寒气而去,在极度困苦中幸得你的同情。春天就快来了,枯树又将发芽,一切充满着希望,空气也清新怡人……”
然而她的呼吸却日渐艰难,已有一个星期了,她吃不下一口东西,女儿守在她旁边记口述,说不了几句她就会昏迷;夜里她根本睡不着,噩梦不断。“帮帮我”,她向女儿喊道。“我快不行了,让我去吧!”女儿哭了。她最不愿见到的时刻终于来了。
最担心的是在安乐死过程中出现差错。万一那些安眠药和止痛剂剂量不够,那母亲就将在昏迷和痛苦中艰难地死去,那太残酷了但女儿明白,母亲必须得走了。母亲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呼吸都很困难。当女儿费力地把便盆从母亲身上移走时,她哭了。她记得母亲不止一次给她说起过,不要让她病到这种程度才死。女儿叫来了哥哥和弟弟,他们必须行动了,母亲再不能受这样的痛苦,时间已经不多了儿女们齐集在她的身边。她一动不动地躺着,孩子们流着泪,一点点地啃着三明治喝着酒。屋里飘着她早年熟悉的老歌,那是儿子特意带来的老唱片。
她忽然转向小儿子,用极清晰的声音问:“还有人要来么?”“没有了,妈妈。”“那好,开始吧,我得走了!”
女儿扶起她,就着水让她将药全吞下去,再给她穿上那件她自己早就选好的桃红丝袍。女儿吻着她,给她说晚安,说妈妈,咱们回家去吧……她倒下去,沉沉地睡去。儿女们围在床边,看着瘦得只有27公斤的母亲。两小时后,她停止了呼吸。
第二天一早,孩子们洗完了餐具,打电话请来了验尸官。
“记得在此前,有人问她是否怕死,她说不怕,死只意味着结束。她说她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地狱,她只相信活在世上。她当然读过圣经,她当然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但她还是开玩笑说,如果上帝因为我对他不敬而惩罚我去死,那该多好!”
但她终于也禁不住有了些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