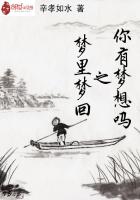不知道这天是个什么日子,萧探骊接二连三遇到意料之外的事情。
回到县衙,才听说阚英已经走了。
“走了?为什么?去了哪里?”萧探骊问道。
“本官也不知。”郭特沉吟道,“他走得极匆忙,都未向我面辞,只是留了一封信,叫王老头送来。”
“什么信?在下能看看吗?”萧探骊道,见郭县令并不答话,忙道,“在下孟浪了,请大人恕罪。”
郭县令道,“也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只是里面并没有提到里,也没有说离开的原因,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再回来,奇特的很。你若是不相信,便拿去看吧。”说着从怀里摸出一封信来,萧探骊一眼瞥见信封上写着“郭大人亲启,阚英草笔”几个字,字迹确实是阚英的,便忙说道,“不必了,在下岂有信不过大人之理?大人对小的恩同再造,小的信不过谁也不会信不过大人。”
郭特点点头,“你好好干。这县尉一职,屡次换人,我已经奏准刺史大人,不准备再用人了,就由本官兼任,等以后从你们捕班中考察人选,若有可堪大用的,便准予升调。”
萧探骊不是傻子,听他如此暗示,忙准备躬身感谢,但这时每日都念的那几句话“敏于事而讷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在脑中一闪而过,到了嘴边的话便变成了,“大人英明,依小的看,我们马捕头就堪大用,当然了,县尉一职掌管全县武装,由大人兼任实在再合适不过。”
郭特一听就笑,“小子,你跟我打什么马虎眼?马银章虽然忠心,但没有通变之才,若非如此,我早提拔他了。你说县尉由本官兼任再好不过也不对,目前不过是权宜之计,按照大唐律令,县令兼任县尉其实是违律的,只不过现在北方乱象已萌,朝中又极腐败,各州监察御史形同虚设,没人认真追究罢了!”
萧探骊也笑道,“小的明白大人的意思了。”
郭特道,“你明白了就好,好好去干,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奏于我知道,我自会帮你。只是你自己要明事理,一定要站对队,不然,我就爱莫能助了。你父亲生前与我交好,我不忍看着他的一根独苗长不成人,成不了器。”说着唏嘘不已。
萧探骊心里感动,说道,“大人放心,小的一定不负大人所望。”
郭特点头,“我知道。”过了半晌,见他还未走,问道,“探骊,还有事情?”
萧探骊笑道,“刚刚大人说小的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可以来找您。”
郭特道,“嗯?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萧探骊将陶溪儿的事情说了,又说了今日悬崖上的事情。
郭特道,“你跑到悬崖上去干什么?”
萧探骊就撒了个谎,“今日去亡母坟前上坟,见坟墓四周并无树木围绕,便去崖上准备挖几棵小松树,没想到便在上面遇到了陶溪儿。”
郭特没有怀疑,点点头,想了一下,说道,“今日摔死两个地痞无赖的事情,倒是可大可小,那帮地痞无赖不过是为了一个钱字,若是有钱,他们也不会将同伴的死放在心上,便不会起诉。但朱家的事情,确是头疼,朱家只有这么一个孩子,虽然不是什么大户,却也是白鹤县清清白白的人家,断了他们家的后,他们岂肯善罢甘休?”
萧探骊道,“多给他们一些银子呢?”
郭特摇了摇头,“站不住理,银子多给反而以后埋下祸乱。你先回去,我明日派人去查查看,童养媳买卖朝廷虽然并不明令禁止,但也曾出过文书要求民间遏制陋俗,我猜陶家和朱家之前并未立过字据,只是口头上达成了交易。陶溪儿父母死去已三年,死无对证,我们可以从这方面下功夫,只要占住了理,再花点钱,便问题不大了,最多判陶溪儿三年徒刑。”
萧探骊听了道,“还要判刑么?”
郭特轻哼一声,“你以为伤人身体是闹着玩的事儿吗?这种事情,朱家若不依不饶,陶溪儿便性命能不能保住也难说呢!”
萧探骊忙道,“是小人无知。此事全凭大人做主,若能救得陶溪儿性命,小的带她来给大人磕头。”
郭特点点头,“这还像句话。你去吧,本官自会用心。”萧探骊方才退了出去。
回到住处跟王老头和陶溪儿一说,陶溪儿一听,就大哭起来,呜呜叫着说自己不要坐牢。萧探骊见她哭得伤心,便道,“你怕什么?就是坐牢,你不还是在这院子里么?这院子里谁不认识你,你在牢里,牢头们也不会亏待你,再说外面还有你外公和我,我们也常会去看你的。”
陶溪儿一把鼻涕一把泪,问道,“真的?”萧探骊点点头。陶溪儿道,“可是我害怕被关在屋子里,你知道,我最坐不住了,整天在牢里,不要说三年,三天我就闷死了!”
萧探骊不耐烦地说,“那你说怎么办?”陶溪儿道,“你陪我一起坐牢好不好?”萧探骊道,“亏你想得出。”陶溪儿道,“你陪我坐三年牢,出来还做你的捕快,岂不是很好?有你陪着我,我再牢里就不怕闷了。”萧探骊道,“姐姐,便是坐牢,我也是在男牢,你在女牢,好不好?”陶溪儿道,“你跟郭大人说说嘛,让他把咱们关在一块儿,他对你那么好,一定会答应的。”
萧探骊便不想再说话,省得费唾沫。王老头对他道,“孩子,你跟我出来。”见陶溪儿也要跟出来,瞪了她一眼,让她回去睡觉。
院子里月光很好。王老头沉默半晌,突然转身拉住萧探骊的手,说道,“孩子,这事就拜托给你了!”说着声音黯哑,眼中迸出泪花。
萧探骊道,“大叔,你放心好了,溪儿就像我的亲妹子一样,我不救她谁救她?”
王老头点点头,收住感伤,问道,“你准备怎么去弄钱?说到底,有了郭大人帮忙,咱们要想的就是钱的事儿。”
萧探骊想了想,道,“想来想去,便只有一条路了。赌。”
王老头点点头,“我想也只有如此了。也只有这事儿我能帮上你一点儿忙。”
萧探骊道,“大叔,您的意思是?”
王老头忽然抬头看着明月,悠悠地长叹一声,说道,“说起赌,当年我是第一把手。我祖上原本家资富饶,传到我这一代,我迷上了赌博。不但将家产输得精光,输红了眼,连老婆赌输了,那时候溪儿她娘才刚满十三,被我输红了眼,也卖给了溪儿她爹那个穷光棍。我爹娘一气之下双双撒手人寰,我还不醒悟,连自己也押上了,输了便给别人为奴。”
萧探骊见他停住不语,问道,“后来呢,还是赌输了?”
王老头点头叹道,“是啊。三十五岁,别人都正是成家立业的年纪,我却将家败得精光,还从一个爷沦落成了奴,后来又被卖给官府,这一眨眼就三十年过去了,一辈子就快走完,所拥有的,却只是一肚子的悔恨!”
萧探骊道,“大叔,您的意思是,不让我去赌?”
王老头摇了摇头,“不,这次你得去,不然溪儿就很可能熬不过这一劫。我已经对不起她娘,不能再连她也保不住。”
萧探骊道,“大叔,您到底想说什么?你尽管说,我听就是。”
王老头道,“我想说一个字:度。”
“度?”
“正是,”王老头道,“嫖若不解风情,便成了狂嫖,赌若没有度,就是滥赌。我这里有积攒下来的二十两银子,你拿去,赢够了两千两就回来,一两也不要多贪。”
萧探骊大惊,“两千两?”
“正是。”
萧探骊道,“我怎么有本事凭二十两就赢两千两呢?”
王老头豪迈的一笑,“这有何难?我教你。”仿佛当年的风采瞬间又回到了他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