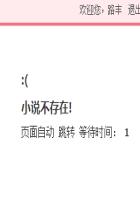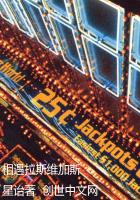————————————
好汉不提当年勇
不是不想提
而是没处提
————————————
8月29日下午五点半,就在伊藤等人从将军墩出发,抵达龙珠假日酒店办理住宿手续的同时,距离此处西南方向约40多公里,嘉禾市,晚晴路,公交客运中心,一辆方头方脑的55路大巴搅着尘土,呼呼开来,又大喘一口气,停在三号站台。
车上的乘客所剩无几,陆续拖着疲惫的腿脚,拎着行李一瘸一拐踱下车。最后一位,是个高瘦的男生,绷着白净的脸庞,脚蹬茶色凉鞋,一身皱巴巴的灰绿T恤、黑色休闲短裤,背个深蓝色的包,耷拉着头,无精打采。
这个男生,正是矢夫。
32个小时前,他从义务劳动半个月的非凡装饰公司,被小保安赶了出来,灌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暗骂一声“东风吹,战鼓擂,老子失业谁怕谁”,开启了古怪离奇的龙珠之旅。然而,初涉一番灵异奇遇后,他选择了逃离。
现在,一路坐到晚晴路的55路终点站,很巧,他那小小的出租屋,就在附近。
晚晴路,是一条百年老街,过去曾叫做大马路,两旁遍植法国梧桐。这些梧桐,见证了嘉禾的沧桑岁月,青白斑驳、数人合抱,又经过不断的修剪,那些本应四处横生的枝干都齐刷刷向上伸展,钢叉一般,直冲九霄。
此时此刻,流动的云,蘸满了鲜红、艳黄的夕光,卷着黛青、靛紫的天色,穿过这条林荫大道,就忽然被扯住了、揉碎了,化作彩旗似的一片片叶子,挂在枝头随风摇曳,又扰起阵阵蝉鸣,忽远忽近,伴着忽左忽右的车流和灯影。与此充满诗意的街景截然相反,灰头土脸的矢夫,如同忙碌一天、疲惫不堪的苦力,弯腰驼背,踩着长长的影子,转过一排灰色的水泥墙,又拐进一条背阴的窄巷。
这条窄巷,有个怪异的名字,叫做螺丝巷。据附近的老人说,不知何年何月,嘉禾古城遭遇一场兵燹,城中尸横遍地、白骨累累,这条巷子里也全是死尸,层层叠叠,摞到了墙顶,所以当地人唤作摞尸巷,后来讹为螺丝巷。说也奇怪,哪怕是正午,巷中也阴森森照不进一丝阳光;巷里那盏路灯也很邪门,总是坏,即使刚刚修好,到了晚上也必然爆掉。
因这非常的缘故,螺丝巷的几栋古宅大多空关着,或只能以很低的价钱,勉强租给两种人:一种是不知情的,另一种,是不信邪的。
窄巷的尽头,长满青苔的砖墙上,砌出一座黑洞洞的石库门,穿过一条潮湿、阴暗的夹弄,就是矢夫的小屋。开门进去,一股奇怪的味道,仿佛是馊了的饭菜、刺鼻的煤油,夹杂着呛鼻的烟味和霉味,说不清楚。
头顶的日光灯弹了数弹,闪电一样,终于亮了。屋子不大,约莫二十平,遍地狼藉,脏乱不堪。矢夫垂头丧气,把深蓝色的背包往当中的破桌上一扔,就倒在左手边的床铺上。床头胡乱堆放着一叠书籍和衣物,床边竖着个三角架,上面斜靠着一幅未完成的画,但根本看不出画的什么。地上簇拥着一只只五颜六色的颜料罐、玻璃瓶,还有半空的方便面桶,插着画笔、一次性筷子和一大盆烟屁股。
肚皮咕噜一声,提醒说该吃饭了,但从头到脚都没有爬起来的意思。
老式的房子,不做吊顶,赤裸裸可以看到一根根木椽,中间码着青红的砖瓦,就像钻入一条大鱼的肚子,抬头就见那血红的肉、白森森的刺。盯着房顶,矢夫呵呵笑着,热乎乎的泪水顺着眼角,流淌到耳根和脖子里,犹如刀割。
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个或一群鬼。
开始还只是藏藏掖掖的,不好意思拿出来示人。
但是,当他也变作鬼时,一切都变作顺理成章,赤裸裸的,无需遮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