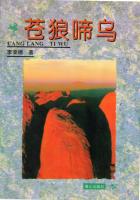好久过去,雨水转小,我们奉命望风。转角是家关张的面馆,他们不管从哪边来,必然通过此地。塑料帐篷下,两张方桌,七八个塑料凳空在外面,暴露在无人的空间里,无人问津。我、王朝阳、龅牙坐了上去。“他们不知道带多少人来呢。”龅牙嘟哝着,眼睛警惕地观望远处,雨水打在蓬顶,发出轻微的滴答声。
也许是逃离群体的自由感,我放下约束,变回自己,悠闲地踢着一个塑料凳,并第一次手插两只牛仔裤口袋,弯腰驼背,忽然觉得此刻自己已经是学会成人那套规则的孩子一般。“要是人多,怎么办咧?”我很孩子气地,奶声奶气地问。
龅牙有些惊异地看了一眼突然变了的我:“怕什么,反正看见他们人多,我们就跑,然后去报告就行。对不对。”他说完,转过脸看着王朝阳,想得到认同。王朝阳轻轻点头。
“你上次打王正宇了?”我眼珠一转,把问题扯地很远,诙谐地问他,脚底依旧踢着那张凳子,那凳子反转着,沾着砖头缝隙里的黑土,我用脚尖勾起它,一会盛土,一会又倒掉,刚开始觉得挺有意思,后来没意思,只是机械地重复着。
“嗯,以后谁再叫我龅牙,我就揍谁。”龅牙讲地很认真,非常认真,整个小学六年都没看到过的认真。“你们注意点,我去撒泡尿,别出情况,看见一伙男的,肯定是他们。听见没。”龅牙命令着。我点点头,这让我很失望,非常失望,小学六年都没对他这么失望。我希望他笑着说:“只是吓吓他而已。”我好与王朝阳跟着笑笑罢,于是我们还可以谈起好多类似的事情,例如偷摩托车什么的。
我们三个好久没有单独相处,我对龅牙变得特别矛盾,以往我们三个一定会开开玩笑,说说好玩的事。王朝阳虽不太说话,就也跟着我们笑笑,如此气氛融洽,现在却为了别人的事,命令我们操这份闲心,而此时我却连怎么称呼龅牙也说不清楚。我以为自己便是从小到大最护着龅牙的人,一直且唯一把他当人看的。直到他华丽的转身,直到他确定自己变成坏人,直到带我们逃离被欺负的地位时。我隐隐约约觉得,以前的我只不过是一种同情,事实上,我并没有公平对待他,把对他如对待其他人一模一样,我内心依然瞧不起他,到现在还是,我只是不说来而已。我是那种渴求有拯救与命令他人权利的人罢,要命的是此刻权利倒转,这一切让我有点糊涂了,我看看王朝阳,他看看我,除了扭动他那股肌肉,什么屁也放不来。龅牙很严肃,我没了心情,放下凳子,沉默。
回来就问:“有没有动静?”我们摇摇头。“看准了?别出事啊。”龅牙叼着烟,眯着眼。
“没有,就没有,来的话,巷子里头早听见喊叫声了。”我呛了他一句,实在忍受不了他这样彰显权利的方式。说完就他脸色不高兴了,像某人说他龅牙时候一样。“别搞出事,搞出事就完蛋了。”他难听的说着,王朝阳点点头,填补我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