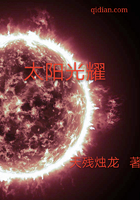曲江县西城墙的敌楼内,四个人映着桌上的烛光,在愉悦地推着牌九。此时,楼外燎炉烧得正旺,室内倒也颇为暖和。
坐在首位的那人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乃是西城墙夜巡的兵头冯岗山。曲江县虽然地处偏僻,但夜巡的规矩还是不敢废除的。再加上最近乱匪颇多,若是结伙个几百人趁着夜色冲入城中,那还了得?
“冯头,您今晚手气很旺啊!”他下首一个尖嘴猴腮的人说道,“都连庄了好久了,也让着我们点啊。”
“汤九你尽放屁,昨晚我和老汪输给你和祁三多少,老子眉头皱了一下没有?今晚老子可要好好地回回本。”冯岗山将牌九一推,接着道,“双天,掏钱!”
“冯头,你看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要不今天就到这算了?”坐在他上首的祁三一边肉痛地掏着钱,一边说道。
他和汤九都是街头的混混,颇为好赌,但赌坊都是靠山雄厚,十赌九输。于是他二人偶然之下和夜晚看守西城门的两个兵油子搭上了线,冯岗山和被称为老汪的汪铁琦都很有赌品,从不赖账,一来二去四人竟成了固定牌友。
还未等祁三将银钱递给冯岗山,一旁的老汪将牌九一推,笑眯眯地说道:“老冯你的庄也该让让了。”
冯岗山眼睛瞪得和铜铃一般大小,笑骂道:“你个狗运真好。”
原来老汪的牌赫然是丁三配二四,至尊宝,压他双天一筹。
四人互相结账后,正码着牌九,祁三突然嘘了一声,道:“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
“这大晚上的能有什么声音?你小子别给我玩这套,赶紧码牌!”冯岗山大大咧咧地说道。
“咴……咴……”
这下牌桌上的四人都听到了夜色中的马嘶声,那汤九天生胆小,脸色发白地问道:“不会我们这边也有乱匪打过来了吧?”
冯岗山在他脑袋上狠拍了一记,笑骂道:“你个孙子,我们这小县城能有什么乱匪过来?老汪,走,去看看。”说完率先走了出去。
汪铁琦却颇为谨慎,将门后的兵器拿在手中,才跟着冯岗山走了出去。
两人借着月色和火光,向城下看去,只见一只白马在城楼下,焦急地鸣叫着。
“这白马好想看着有点眼熟啊!”冯岗山咂咂嘴说道。
“我也好像在哪见过。”汪铁琦附和道。
“这不是那美人孙潇娆的白马吗?”却是一旁壮着胆子出来的祁三出言道。
“哪个孙潇娆?”冯岗山接着问道。
“冯头你连这都不知道啊?就是武堂的那个美女教习啊。”祁三接着道,“这白马我见过,平日里好像宝贝得紧呢!”
“嘿,我管它什么白马黑马,和大爷我有半两银子关系?走,咱们回屋继续。”冯岗山不以为然地挥手道。
“且慢。”旁边的汪铁琦一把拉住了他,长吐一口气道,“若真是那个孙潇娆,恐怕这事就严重了。”
冯岗山将眼睛一瞪,道:“能有什么事?”
汪铁琦出言道:“冯头你有所不知,这孙潇娆来头甚大,据说是八大门派流云宗的内门弟子,父母在门派中的地位甚高,和县令家也颇有交情。如今这白马还在,人却不见了,恐怕真是出了什么事了!”
“乖乖,这么大来头跑我们曲江县当教习干什么?”
冯岗山吸了一下鼻涕,他知道汪铁琦虽然是自己下属,但年纪却比自己大了一轮,当下问道:“那老汪,你说我们该怎么办?这大晚上的,总不能开城门吧!”
汪铁琦沉思了片刻,回道:“我们把这事和县令家的管事讲一声,不管他们怎么办,反正我们是通知到了,到时候就算出了什么事也算不到我们头上。”
他顿了顿,接着道:“这城门却是万万不能开的,万一出什么事,你我二人可是要掉脑袋的。”
冯岗山想了片刻,道:“行,就听老汪你的。你待在这里,我这就去县令家通知他们。”说完急匆匆地下了城楼。
“老汪,到底什么事啊?”那汤九此刻才敢走了出来,出言问道。
“没什么,今天就到这了,你们先回去吧。”汪铁琦摆手道。他活了这一大把年纪了,岂能看不出来冯岗山急火火地去抢功。但有功是他的,有过也是他的,自己不争不抢,也不做不错,追求不同,平平淡淡过完这辈子也挺好的。
县令王泰昆是从被窝里被人喊起来的,知晓孙潇娆好像出事后也不觉皱起了眉头。万一孙潇娆真的出了什么事,她父母找上门来,自己是朝廷命官虽然不怕,但流云宗真的要在曲江县搞事情,这政绩可就难看了。
于公于私,自己恐怕都要出一下力了。
他微微想了一下,吩咐道:“快去请褚老和何老过来,还有,叫上县里所有的捕头,直接在西城门集合。”
。。。。。。。。。。。。
杨开风可不知道他已然搅动了满城风云,此时的他正好整以暇地站在孙潇娆面前。脸上由于蒙着布条看不出丝毫的表情,不过也正因为这样,才更显得狰狞可怕。
孙潇娆依然在拿流云宗的身份给面前的侏儒施压,但当她听到侏儒猥琐的笑声时不由心底发寒,暗下决心,自己就是死也不能丧失了清白,令父母蒙羞。若是这个侏儒敢有不轨之意,自己拼得爆体而亡也不会让他好过的。
却见对面的侏儒在地上翻找了片刻,不知拿起了什么东西,缓缓地走到了自己面前,蹲了下来。
孙潇娆全力运功,就等这侏儒下一步行动,就拼个同归于尽。
不承想这侏儒拿出一根硬草,在自己脸上不断地滑动着。
孙潇娆强忍心中的滔天杀意,默念道:“再进一步,再进一步,只要这侏儒的手碰到自己脸上,宁死也要带着他一起见阎王!”
更出乎她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那侏儒又划了几下,竟收起了手臂,看了自己两眼,将硬草朝地上一扔,拍了拍手自言自语道:“唬唬,我果然是个天才!”
“你对我脸上干了什么?”孙潇娆全然不怕激怒面前的侏儒,喝问道。
那侏儒又是‘唬唬’了两声,回道:“你猜!”
接着那侏儒不顾孙潇娆的质问,将丢在一边的黑色短棍拿至手中,大步流星地消失在夜色之中。
明亮的月光之下,只余下孙潇娆的娇叱声:“风四海,我和你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