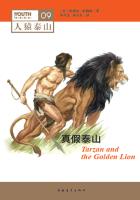詹西初一下学期转到我们班上来了。他是在原来学校打架被开除后,转到我们这个乡下学校来的。詹西原本就背着不光鲜的过去,到我们班后却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成绩差、扮清高、奇装异服、特立独行,但差不多所有的老师都包容着他。那时詹西在我们眼里是异类,而他从落草我们班的第一天起,就似乎抱定了不与众人为伍的决心。我们都很有“自知之明”,也没有谁准备去“高攀”这个城里来的人。
詹西有一辆黄白相间的山地车,据说还是从千里之外的家里托运过来的。有高高的座凳,车把矮矮的,并不高大的詹西跨在上面,上身几乎和大地平行。他骑车总是风驰电掣,像一尾受惊的鱼在密密麻麻的放学人群里麻利地穿梭。这是一个让人生畏而又常被同学私下狠狠贬斥的家伙。
初二一开学,老师实行一帮一对策,倒数第一的詹西被分配给了第一名的我,他成了我的同桌。当詹西嚼着口香糖,将书桌拖到我旁边的时候,我突然趴在桌子上哭了,很伤心很绝望。我的哭没有任何酝酿过程,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原因。
班主任走过来安慰我:“斯奇,你是班长,应该帮助詹西。”我还没说话,一旁的詹西却发话了:“觉着委屈把桌子搬出去,我都没说嫌弃!”哭归哭,我是班长,应该带头承担班上的艰巨任务,所以詹西最终还是我的同桌。但是我心里暗暗发誓,宁愿被老师骂,我也不会帮助詹西提高成绩的,我巴不得他剩下两年的所有考试次次都垫底。同桌三星期,“三八线”分明无比,从没说过一句话。
有天下午,我穿着城里姑妈买给我的一件雪白的连衣裙,一整天都很是得意。最后一节课上了一半,从没跟我说过话的詹西突然塞给我一张纸条:“放学后我用单车载你回家。”我的心突然怦怦地跳起来,14岁的女孩儿第一次收到男生纸条的心情可想而知。即使这个男生是我一向都鄙夷不屑的詹西。我不知道怎么办,动都不敢动。他却在一旁“噗噗”吐着泡泡糖,见我没反应又塞过来一张纸条:“我必须载你,放学后你先在教室坐一会儿,等人都走了后我们再走。”
剩下的半节课我内心充满了极度的紧张和惶恐。心想:这个小古惑仔要胁迫我的话,我是一点儿辙都没有的。何况我靠墙坐着,詹西坐堵在外面,想逃脱都没有一点儿机会。
放学了,同学们做鸟兽散,詹西一反常态没有冲出去。我认为他要跟我说点儿什么,但是他兀自趴在桌子上画漫画,只是头也不抬地甩了句:“再等一会儿我们走。”他说话冷冰冰的,语速又快,我不敢不从,怕今天得罪了他明天就遭到毒打。要知道他曾经聚众打架连人家鼻子都砸歪了。
我们走出教室的时候,发现校园里已经空无一人。詹西先在后座上垫了一张报纸,然后上前去支起车子,也不说话,意思是要我坐上去后他再骑上去。可是他的车子实在太高,我爬了四五次才爬上去。他戴上墨镜,弓着身子,也不事先要我抓好就开始疯狂地蹬车。我惶恐地问他:“詹西,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他说了一个字:“家。”我的声音发抖了:“谁家啊?”他的声音提高八度:“废话!难道我把你带到我家里去?”我不再作声。车子拐出校门,詹西走的是去我们家的那条路,是一段小小的斜坡,詹西很卖力地蹬,我坐在他后面,像一只胆小的小老鼠一样,连大气都不敢出。作为一个14岁的乡下姑娘,这种看不出理由和后果的事情,我还找不到方式应对。
从学校到我家有一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一直害怕在路上碰到同学,但是快要到家的时候,还是碰见了一个。他看到我坐在詹西的车上就大声地嚷道:“哈哈詹西!哈哈斯奇!”我正要说话,詹西怒喝:“理这些无聊的人干什么!”我便闭上嘴,可是心里很不安:同学要认为我和詹西谈恋爱可怎么办呀他一直把我送到我们家院子里,我一跳下车,他转身就走,对我的“谢谢”不做半点儿回应,整个过程我都处于蒙昧和惶恐中,不知道詹西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进屋后,妈妈突然拽住我:“丫头,你裙子后面有好多墨水!”我惊诧地扭过头,看到自己雪白的裙子上有一大块墨水,还没完全凝固。妈妈在一旁数落:“这丫头,裙子脏了也不知道。从学校到家这么远,不知道让多少人看到了!”
如果没有詹西用他那辆鲜艳的单车载我回家,我那被“污染”的白裙子就会被很多同学看到,而那些男生一定会笑死我的。那个一向让我讨厌的詹西,却用那么巧妙的方式避免了我的颜面尽失。
第二天见到詹西,他一如往常地坐在那里,一如既往地视我为空气。我坐下来,轻声地跟他说了声:“谢谢!”他似乎有点儿不耐烦:“没什么啦!”从那一刻起,我对他充满了敬佩和感激。
那以后我很多次主动去帮詹西,他不怎么配合,但是我愿意这样“自作多情”厚脸皮地帮助他:主动给他讲解难题,提醒他上课不要看武侠小说,别人讲他坏话我也替他辩驳。詹西对我的好意从来都不以为然,他似乎对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丝毫没有兴趣;他的成绩后来有所提高但依然够呛;他也没再“强迫”我坐上他那辆很炫的单车。
初三下学期,詹西回到他的城市。他走得毫无预兆,离开之后班主任才通知我们。詹西的离开可能对其他同学造不成任何影响。但是我从那天起,常常想念并感激着他,以及他那辆温暖美丽的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