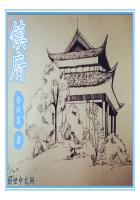在中国西南一带,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则传说。
九代南诏王死后,他们的灵魂都通过一种失传的术法寄托于九个金瓶中,这些金瓶共同在一座人迹罕至的幽山之中守护着一个古老的秘密。
守护着这个秘密的金瓶,由于年代久远,在幽山之中吸收大量天地灵气,早已成精,每当天地阴气浓盛且月星圆满之时便会出来,在南诏绵延群山之中游荡。
据传谁若能在金瓶外出游荡之时,捕捉到它,便能够到达那个幽山知悉那个秘密,然后就可以获得数之不尽的金银财宝,更有可能永生不死。
此刻在大理古城的某座泛着古朴气息的小茶馆内,一位胡须花白的老者悠然地喝着茶,周围围着一大群人听着他讲着有关南诏金瓶的传说。
“阿叔公,这是你瞎编的吧!要真有你说的这么古怪的金瓶,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下来都没有人亲眼见过?如果有的话,早就被人得到了!”刚二十出头的茶馆伙计半开玩笑道。
这时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人说:“年轻后生终究是年轻后生!到底还是经历少,见识少啊!阿叔公所说并非是他满口胡诌,这金瓶传说从很久以前就流传下来了,史书上都有记载。”
“谭先生说得对!我的父亲还在世时就对我说过,二十年前的某个下雨天,他在苍山的一个山洞中避雨时,就曾亲眼看到过九个金瓶悬于半空中发出一片耀眼的金光。当时他还以为遇见鬼了!吓得赶忙冒着雷雨,担着生命危险跑回了家里。
回到家后的那晚,他左思右想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后来他灵光一闪恍然大悟他很有可能遇到了一直在大理民间传说的金瓶了。
知道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的金瓶后,他一宿没睡,第二天一大早就将此事禀报给了当地市政府。谭市长一听说此事马上就调了一批人马跟着父亲去往昨晚的那个山洞。谁知,诡异的事情发生了,父亲按照他脑海中的记忆路线到达原地点,发现本该在那儿的山洞没了!
这种结果让谭市长以为父亲在拿他开涮,差点要把我父亲抓进牢里,后来由于我父亲一再向他保证绝没有骗他,语气诚恳至极,这才免了牢狱之灾。
事后父亲苦思冥想,一遍遍实地往返于苍山之中,并反复和记忆中的线路作验证,确定他所走的路与记忆中的路并无二致,但是明明是那个地方,偏偏那个本该存在的金瓶大放金芒的山洞就不见了!
这件事成为父亲一生的遗憾。他生前常常在嘴上念叨,要是当时他胆大一点,不那么恐惧慌张地跑出来的话,也许……哎!”一位长着山羊胡的中年人感叹道。
胡须花白的阿叔公对茶馆伙计道:“金瓶飘忽莫测,行踪不定,向来难以被发现。况且这等通灵之物,又岂是你说得就得的!你看从古至今,这么多年下来,你听说它被哪一个人得到?这就说明它的诡异莫测!!
不过,这金瓶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被得到,我这儿倒知道一些众人大都不知晓的隐秘。
相传这世上有两卷古老的羊皮卷,这两卷羊皮卷上用古老的密文清楚地标注了金瓶经常出现的季节、气候、地点、路线以及如何捕捉到它和利用它找到宝藏与秘密的方法。
如果谁能得到这张羊皮卷倒有那么一些可能揭开金瓶背后的那个惊天大秘密。
不过这世上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羊皮卷我也不敢保证。”
“阿叔公,听您这么一说,我对那金瓶倒是起了兴趣了!以后我一放假就去西南那带荒山转转,说不定我一不小心走了大运,得到传说中那只游荡的金瓶,那我不就一朝发达了吗?到时候我就娶个美娘皮过日子,吃好喝好穿好住好,也不用成天在这茶馆里累死累活了!说不定还能得个长生果,那时候我肯定忘不了阿叔公,就分一半给您,让您再多活个几百年……”茶馆伙计连说带笑,嗓门大,声音又好听,使得这茶馆内的气氛一时间活跃热闹了起来。
众茶客听着茶馆伙计在那胡侃,也跟着起哄,大谈特谈金瓶,做着他们的金瓶美梦。
傍晚时分,寒冷的天空,下起了毛毛雨,茶馆外寒凉凉,可馆内却被馨香的茶气和热闹的人声给温的暖暖的。
这时茶馆里来了两人。
为首者三十来岁,皮靴踏在地板上发出蹬蹬响,众茶客的目光都不禁被这皮靴踏地声给吸引了过去。
众人只见这位皮靴男,有着一张英俊的脸,脸上挂着温和的笑,但这笑却让他们感受到一股可以刺到骨里的寒气。
第二人是一位穿着僧服的僧人,他的脸上好像始终有着体恤众生的大慈悲,让人看后心中安宁,他的脚下穿着的是一双有些破旧的棉布鞋,跟在皮靴男后面,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他们二人找了个偏僻的座位坐了下来。
众茶客在这二人身上找不到什么有意思的事,便又拐到金瓶上闲聊。
这二人始终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周围人闲聊着金瓶。
当阿叔公再次谈到“羊皮卷时”,皮靴男握着茶杯的手一拧,瞳孔微不可查地缩了缩。坐在他对面的僧人却看不出什么异样,脸上还是那副体恤苍生的大慈悲。
这时外面的雨,已由毛毛细雨变成了滂沱大雨,雷声轰鸣,寒气袭击到天地的角角落落,原本躲得还剩一丝的夕阳,此刻彻底躲入了茫茫苍穹的怀抱,把无尽的黑暗绝情地留给人世间。
就在这时,外面又走进来一个人。
这个人年轻得很,二十来岁,只身着一身灰色的单薄衣衫,右手提着一个皮箱,左手的衣袖却空空如野,不用说是因某些特殊的原因没了。
他的浑身都已湿透,可他那张英俊的脸上始终平静如水,看不出丝毫的情绪,但他那深黑色的眼睛里却好像有两团旺盛的仇恨火焰正在燃烧,发出灼人的光芒。
他也选择了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只不过似有意无意地离皮靴男和僧人近一些。
茶客并没有因雨大而消停,而是继续大声说笑着。
他自顾自地唑着茶,一口一口地送入嘴里,丝毫不理会周围人不时瞟着他那空缺的左臂的目光,就连茶客们的谈话,他也懒得去听,他就这样平静地喝着茶,目光也只是在他桌上的茶杯上,从他进来到如今从未多看过别人一眼。
也许是他的身影太过孤独,怕感染了别人;
也许是他目光里的仇恨太过灼热,怕烫了别人;
也许是他心里的痛苦太过浓郁,只有用平静才能消化,只有用冷酷才能不伤了别人。
他刚进来时,皮靴男和僧人瞳孔都缩了缩,散发出刺骨的寒芒,相互点了点头,便又归于寻常。皮靴男脸上依旧挂着温和的笑,僧人外表看起来依旧是一副悲天悯人的大慈悲。
此刻他依旧坐在那儿独自地品着茶,并未多看那两人一眼。
周围茶客对这三人之间发生的微妙事情并没有注意到,继续围绕着金瓶谈天谈地。
大约半柱香的时间过后,距离这座茶馆很远的一座大山的某个诡异的巨型山洞内,突然发出了一声惊天巨响,只听轰的一声,洞内火花四溅,泥土砂石飞扬,瞬间便把这巨大的山洞给填塞了一半,这巨型山洞的中央赫然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幽深大穴。
一座青铜棺从幽穴里飞速地冲了出来,直接撞上了巨型山洞的顶部,棺与壁剧烈地碰撞,发出的巨响传遍四方,惊得荒山中的野猿大哭大闹,猛虎四窜逃散,毒蛇毒虫害怕得直发抖。
就在青铜棺撞上顶部将要坠地之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幽穴里竟然闪电般伸出一只金黄色大手,将青铜棺托于半空之中使其没有坠落下来。
这时候,那原本飞悬在青铜棺四周与其一起冲出幽穴的九只金瓶,迅速飞到青铜棺的底部代替金黄色大手将它托住。
金黄色大手刚被金瓶替代,竟然嘭的一声,分解成无数的金色小蛇,这些金色小蛇竟能在半空飞跃,它们盘旋于山洞四周不断地撞击穴壁,坚硬的削壁上传来密密麻麻的钢铁撞击声,那撞击的火花此起彼伏,就如单红色的烟花在夜空中燃放。
不一会儿穴壁上就被撞出了密密麻麻的小洞,这些金线一般的小蛇迅速钻入洞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过了一会儿,一个巨型如海碗般粗的金蛇又从洞中飞了出来,它飞出来后,和其他金线小蛇一样,在穴壁上打了个洞,钻了进去,只不过它钻洞所用的时间只是一刹那。
紧接着巨蛇之后,幽穴中便喷出了无数的金砖,一直喷了一个时辰才喷完。
数不清的金砖占去了巨型山洞很大一部分的空间。
事情到此还没完。
这时候幽穴中又飞出了密密麻麻的丑陋虫子,这些虫子各个细齿如刀,所过之处,岩石立马变成碎泥,不用多大功夫,它们就冲开堵塞的洞口飞到了外面,飞绕盘旋在洞口前。
几乎就在这里发生异变的同时,远在荒山极远之处的茶馆里的皮靴男和僧人不声不响地走出了茶馆。
就在这两人离开不久,他放下了手中的茶杯也离开了茶馆。只不过方向却与那两人相反,那两人向西——恰是异变所起的方向,而他却向东。
他在雨中,右臂提着一只皮箱,始终未打伞,任寒冷的雨水淋湿衣衫,他那孤独却坚挺的背影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茫茫黑暗中。
就在他消失在茫茫黑暗中的同时,宇宙的另一片星空,一位十八岁的少年,穿着与中国古代衣着有些相似的青色长衫,长衫上绘有一个木字的标记,带着满腹的屈辱与不甘,在一片没有人迹的、散发着死亡气息的、绿色与灰色并存的大森林前犹豫了一下,摸了摸藏在胸口的那件东西,最终好像终于下定了重大决心,愤然地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