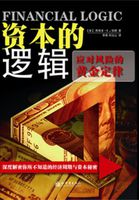张妗娘道:“那你为什么不拦住他?”
杨文广道:“当初原是我的错,当时栋梁在埤a城中栋梁过来找我,说闸河帮出重金替他们帮主报仇,他想要这一笔赏金,要我帮他打探情报,事后平分,我知道那杀了袁七手的杀手是江湖上有名的‘夺命无常’崔干,不仅武功高强,人也十分阴险狡诈,手段毒辣,非常不好惹,所以不曾答应,劝了他几句,栋梁负气自己一个人去了,我一连派出去的人俱都跟丢,没想到过了三天,栋梁就拿了崔干的人头回来,大闹闸河帮,强按着两个副帮主的头与他磕头,硬是坐了帮主之位,他上位的第一件事,便是将这两个副帮主逐出帮去,从他坐稳了闸河帮帮主的位置,争抢地盘,大肆扩张,竖了不少敌人,只因闸河是三州交界之地,向来官府都是半管不管的态度,只要交足了税银子,平常也不大来问,但栋梁如此行事,打破了往日闸河地区的势力平衡,闸河帮一帮独大,底下的人心思活动,教外围无赖挑起事端,杀了两个税吏,唆使帮众连合起来抗税,闸河的税官连着半年都是赔课,其害一半在民,还有一半在官,虽不知栋梁到底是如何管理闸河帮的,用人一定是出了大问题。”
张妗娘闻言,泪如雨下道:“你们哪一个去,把他给我揪回来?”
三人互望了几眼,张妗娘道:“张小枫,你做姐姐的人,领人去把你亲弟弟带回来。”
王菱道:“舅妈,这件事是一件家务事,表兄是张家的继承人,将来接掌张家,哪一个族人不要仰仗,就是请来的外姓教师,只可以与外人对敌,却未必会与表兄撕破脸,表姐去了也是劳而无功。”
张妗娘道:“那王菱你去。”
王菱道:“是。”
杨文广道:“母亲,表弟去也不中用,莫说硬碰硬不行,就用软话说得栋梁动心,他自己肯回来时,但那些手下的喽啰哪一个肯放,遑论栋梁此刻醉心权力,迷头认影,决不肯回,如今让小枫在这里照顾你,我与表弟两个人去闸河口上,先去探一探闸河帮的情况如何?”
张妗娘道:“你这样说时,是没得捉摸,不像个当姐夫的人了,难道就任他在外面作死?”
杨文广道:“母亲,此事不能着急,我有一条慢计,可以徐徐图之,只是有些儿逾矩,却要冒犯母亲。”
张妗娘道:“我恨不得此时就飞到那劳什子河口去,什么冒犯不冒犯的,还不快说。”
杨文广道:“我与王弟这一去,栋梁必定不会回来,我二人便称母亲受了一场惊吓,病重晕厥,用药无灵,等过半个月,再去送信称病危,等过半个月,再去假传死讯,栋梁闻讯必定回来奔丧,我们就在灵堂上埋伏将其拿下,装在棺材里运到别处,不拘囚禁在个什么地方,只是不让他外出,过个一年半载,等那闸河帮另扶了帮主,再放他出来,岂不是好。”
张妗娘道:“好是好,只是要等一个月,却不是让人心焦,就说我此刻就死了吧。”
杨文广道:“要诈栋梁回来不容易,闸河帮探子众多,族中子弟必然也常跟他通信,做戏要做全套,母亲怎样病重危急,我们怎样挂服举哀,一项不少,连族中人都瞒过去,方才能引得栋梁上当,只要他人回来了,在饮食里做些手脚,将他的手下隔在庭院中,我们在大堂上动手,不愁没有办法摆布他,今日我与王弟先去打探一番消息,也好回来准备。”
张妗娘想了一回,没有其他法子,道:“只能如此了,你们快去快回,左右先讨个信来。”
当时王菱与杨文广出来,在家中安排了两匹快马,立时上路,在路上跑了半日,至晚歇在一个客栈,次早又动身,日行晚宿,这一日来到闸河岸边,正在一个路边茶铺歇息,忽见一队人马匆忙路过,也进茶棚里来坐下。
杨文广道:“王弟,你看这不是那个严队长,他是个与闸河帮对敌的人,我们讨讨他的口气如何?”
王菱道:“他怕是不会理我们,你上去试试?”
原来严队长当日回去见上司,当时上司正为闸河帮的事情忙的焦头烂额,听说拿了一个头目吴老三回来,大喜道:“连日抓人,都只抓了些普通帮众,不见一个要紧些儿的,你今番出马,功劳不小,却是怎生拿来的?”
严队长将事情经过禀告了一遍,道:“还请相公再下一道令,让我去剿收财物了来。”
那上司官闻言,却不愿得罪十乡宗族,道:“你怎地不当场拿住,常言道,拿贼拿赃,捉奸捉双,这贼人与赃物,跟奸夫与淫a妇一样,终不然拿了一个,再拿一个,硬打成奸。”
严队长道:“有礼单证物在此。”
上司官看了道:“便有证物,如今事已迟了,只得作罢。”
严队长道:“这张家倚仗地方上的势力,胆敢阻挠,不把官府放在眼里,正该拿他来开刀。”
上司官道:“严拥军,我知你人执法不阿,甚是能干,但十乡的宗族不是一日养成的,此时还动他不得,我派你去闸河口,对付闸河帮只是其一,不日还有一件大事将要发生,你严密监视闸河地方,休要节外生枝。”
严队长见上司如此说,只得强忍怒气,领了军命出营,不想带兵刚到闸河,却又跟王菱,杨文广撞在了一起。
当时杨文广上去道:“严队长,前日一别,今天我们又见面了,真是有缘啊有缘。”
那严队长见了二人,大怒之下,茶也不喝了,喝道:“你们这两个嫌犯还敢来这里晃悠,好大的胆子。”
杨文广道:“长官,你休疑心,我们两个是来劝我弟弟脱离闸河帮,改邪归正的。”
那严队长厉声道:“不仅人要自首,侵吞的不法财物一发要交出来,他是他,你是你,你们两个的事,也还没完。”
杨文广道:“是是。”向他打听张栋梁的情况,那严队长喝了一碗茶道:“我自没空理你。”
那杨文广碰了个钉子回来,王菱道:“再找别人打听打听。”出了茶馆上路,走了半日,路过一个牌坊。
二人见那牌坊上写的‘闸河口镇’,当时进去,向人问闸河帮的情况,原来那闸河帮总坛在镇外十里的北临山上,山下密林环绕,二人问了路径,出镇又找了半日,到了山前,果见三面环水,只有北边一面接着陆地,是天生的要害之处,王菱道:“我们进他的山寨去,先礼后兵,一时我下了手,姐夫接应着些,带了表哥下山回去。”
杨文广望着那山,吃了一惊道:“我看着这山上的旗号,喽啰上上下下,关隘也有三重,我们只有两个人,如何弄得过他。”
王菱看了看,道:“终不然教表哥陷在这泥潭里,我们上去再说。”
杨文广道:“贤弟你不知道,栋梁一向与我不大对头,他见了我,多半没有好言语,不如你去的好,我在山下看守马匹,等你下来。”
王菱道:“既如此说,我一个人去吧。”当时上山,那山路甚是狭窄,到得寨门前时,只见那两边立着数座箭楼,堆着许多擂木炮石,中间走过来一队巡哨的。
那哨头儿迎面喊道:“你是何人,在这里乱走,要来投奔入伙的,谈生意的,都先去闸河口镇上的堂口排号。”
王菱上前道:“我不来入伙,也不来谈生意,只求见张栋梁一面。”
那哨头儿道:“大胆,我们帮主的名号,岂是你这黄毛小子能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