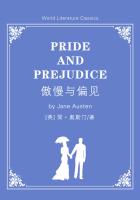唐淑贞的人材,原本不算怎么错,当其刚嫁与高局长之时,曾经有过一枝花的绰号。如今自然不同啦,肩头微微有点耸,项脖微微有点勾,在二十年前,谁看了都会吐泡口水的。然而现在作兴了方肩头,并作兴高跟鞋,穿上高跟鞋走路,必须腿子打伸,脚尖用力,踏八字脚不行,踱方步更不行。当其脚一点地之时,自然而然就有个前脚才伸出去,后脚就追了上来之势。于是这么一追一赶,而再注意把脚尖踏在一条直线上,不必摩仿而电影之步自成,而婀娜之姿自生。如其身体健康的,不妨尽量昂起项脖,挺出胸膛,自然就成功了气昂昂雄赳赳的美国女性。设若身体不行,又瘦又小,则不妨老实把肩头耸起,脑袋低垂,在摇曳之中,也自然有一种娉婷之美,据说三十年代巴黎拉丁区的一般格里色法文GRISETTE的译音,即轻佻的女人。——原编者注便这么样的引诱了不少的青年。
以此,唐淑贞的肩头微微有点耸,项脖微微有点勾,并不足说是她的瑕疵;且皮肤相当白,肌理相当细,以年龄言,也并不大,然而够不上再称一枝花者,她妈看不出来,向嫂却偏能说出原由,由于以前一对极呼灵,像走盘珠样的眼睛,而今已失了活力,也失了光彩,不但眼膛下有了眼泡,就上眼皮也微微有点浮肿;其次,额脑起了皱痕,眼角也生了鱼尾;还有,嘴角也有点朝下挂,显得上嘴唇更其翘了起来,从前那嘴唇多么鲜红,而今哩,不搽唇膏,简直就是乌的;从前笑起来多么迷人,牙齿白得像一排珍珠,牙龈红得像珊瑚做的,而今哩,不笑还好点,免得露出那怪难看的又黑又黄的烂牙齿。据向嫂说,这些都还罢了,因为一枝花的残痕犹可强勉找得出来,而变得连痕迹都没有了的,更是那张寡骨子脸,不但既不丰腴,又不红润,在早起不打扮不搽粉时,几乎是一张戏台上青蛇的脸;颧骨高起来,眉骨凸起来,都不说了,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地方,就是以前虽然发了气,咬牙切齿的骂人,也武辣得好看,巴不得多看她几眼,而今哩,发气也是那样,不发气也是那样,总之凶狠狠的,活像借了她的谷子还了她的糠。
一句话,一枝花已被鸦片烟毁了!
不管一枝花是否蔫了,萎了,甚至残谢了,到底其名为花,其实也是花。结婚之后,男的和女的毕竟不免有一段昏沉沉的时间,这在西洋叫作蜜月,在中国则叫作迷月。
唐淑贞是光明正大的早晨总要高卧到十一点钟才起床。慢慢地过瘾,慢慢地喝泡得极酽的普洱茶,慢慢地抽纸烟,慢慢地洗脸、梳头、搽粉、画眉、涂口红;然后才慢慢地吃一碗煨得极溶的银耳或哈士蟆当早饭;完了,是下午三点了,才慢慢地换衣裳,谈谈闲话,再随意烧几口消闲遣日;再过一会,便吃午饭,一顿菜肴精美的午饭,慢慢地嚼,慢慢地咽,总要费上三刻钟,才吃得完两个小半汤碗的米饭;然后再漱口,再打扮,再烧几口,精神蓬勃了,便邀着白知时一同出门,逛逛街,看一场电影,或是看几折川戏;然后买点小东西,或是糖果啦,水果啦,下酒的干菜啦,急急忙忙回来,一脱衣裳,便开灯过瘾;这是一天里头顶重要的一次瘾,五七口之后,已是二更,才又吃晚饭;这顿饭需要吃酒了,黄的也好,白的也好,吃不多,黄的三茶盅,白的三小杯,只白知时一个人陪着喝;喝完下来,老寡妇、向嫂、高白继祖先睡,两夫妇还要靠着烟灯烧几口耍,总在三更后了,才打睡觉的主意。
安乐寺的大门、安乐寺的茶铺、安乐寺的正殿、以及其中挤得像蛆样的人,吵得像海涛样的声音,已经钻不进她的脑际。她妈在她吃午饭时,偶尔提说一两句,她一定蹙起眉毛,哆起嘴巴,撒着娇,活像一个才懂事的小女郎似的,咬着竹筷说道:“妈也是哟!人家才办了喜事,也让人家安安逸逸的过几天不好?说真话,安乐寺我也赶伤了!热天热死你,冬天冷死你,遇着下雨,上头倒不怕淋,脚下可湿死你。你还能穿好衣裳,好鞋子吗?挤过去,攘过来,不放点泼,你硬挤不进去。还有那些嘴脸,你才看不得哩!个个都像狐狸样,又像狼样,又像蛇样,胆小一点,你硬不敢去同他们打交道。稍为不当心,包你栽筋斗,那是个无底洞,要是一个筋斗栽下去,能够好好生生翻爬起来,除非有通天本事。我每天赶了安乐寺回来,说真话,硬是人要柔柔读让字的阳平声,形容累得全身无力,系四川人的方言。——原编者注半天,才缓得过气来。哼!你们光默到赚钱,好松活么!第一个就是妈,一点也不体贴人,才办了喜事,就要催人家去拼命!我硬不!”
老寡妇都挨了训,自然没有第二个人敢开口了。
所谓第二个人,谁也明白绝不是向嫂,绝不是高白继祖,自然只有我们的白先生。白先生不是不敢开口,因为白先生自从办了喜事以来,也和唐姑奶奶的心思一样,想安安逸逸的过一些时日。他也累够了啊!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六七点钟的功课,星期六还好,只四点钟,若果光教一个中学又好啦,但是教的乃是三个中学,都是老主顾,和他已发生了除非死、除非自己告退是绝不会有六腊之战一九一五年,袁逆世凯叛国,蔡松波率领滇军伐叛入川,与袁逆悍卒战于泸县与纳溪之间,当时称为泸纳之战。其后,川局不宁,学校校长几乎每学期必有更动,校长更动,连及教师,每年六月、腊月为解聘、续聘之关头,竞争激烈,故世人谐音称为泸纳之战。——作者注的恐惧的历史。自疏散以来,三个中学恰好散在老东门、新西门、老南门三门之外各十余里地方,而且都不通大道,都相当偏僻,现代的交通工具不能去,就能去,也没有这种工具的。
别人教的学校,或许有两个三个邻在十里之内,别人可能同一天到三个学校上课,看来辛苦极了,刚在这学校下了课,又须急急忙忙步行到那学校;其实,倒并不怎么辛苦,多走几里,权当散步,权当休息,因为在甲校的两小时连上的功课,可以只教四十五分而早退,而乙校的连上两小时的功课,也一样的只教得四十五分,而迟到;这不是教习先生的过失呀,学校得原谅,学生更加欢然。但是白知时却捡不着这种魌头,他的功课,大抵每个学校占两天整的,说起来,每天只走一处,少辛苦,可是既不能早退,又不能迟到,而且他的老实教学法又习惯了,号音一响,便上讲堂,不点名,不说空话,打开书本就认真的讲,偶尔写写黑板,也很快,因为太熟了的原故;又不肯借故缺课,除非害病,害得支持不住了,然而几年当中身体偏又很结实。以前尚觉得高兴,他对得住学校,学校也对得住他,不管专聘或是以钟点计,每月得来的薪水,总用不完,除了存一笔在一个极稳妥的私家银行外,还可时时兑一些给居孀的妹妹,或者帮助几个同乡学生;就是在民国二十七八年时,还捐献过好多次给国家去买飞机,和做慰劳之用。——当然也同一般捐款的人一样,捐了就是,从没有问过后果,而偶尔发表一张捐款人名单,也从不过目,就听人说及没有自己的姓名,也只笑一笑而已。——学生们也对得住自己,亲切、尊敬、听话。然而自三十年以来,这兴致就一学期不如一学期,自然,报酬太菲薄了,物价每月跳一丈,而教习的薪水却每学期只增加一寸。
那时的教育厅长又是一个对哪都不含胡的时新的所谓三干人物,只管自己住洋房、坐汽车,但是一开口便说:“譬如我堂堂厅长,每月也才四百元的薪水,各位一个中学教师,每月拿到一二百元,也够啦!要说不够穿吃,目前抗战紧急,救亡且不暇,哪能顾到个人的饱暖?教育本是清苦而高尚的职业,我们既高尚了,精神方面多得一点安慰也罢咧,为何还要论及物质?像这样只在报酬上斤斤用心的人,怎配说是为人师表!不如老老实实去当黄包车夫,不如老老实实改行做生意!我竭诚奉告各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要各位冷得、饿得,国家自然得救,只要国家得救,各位就牺牲了也值得呀!如其一定在这困苦时节,要求增加薪水,甚至强迫学生格外出钱、出米来尊师,那,兄弟不客气,决定奉行委员长的手谕,宁可封闭学校,也不许可开此恶例的!”这种不顾事实的官话,也实在令人灰心。因为白知时既不能丢下课本去摸车杠,如教育厅长所指示,又不能去摸算盘,如好些校长们之已为,而自己又习与性成,到时候必上课,一上课必认真,上课时倒不觉得什么,但下课回来,把车钱一出,算一算,真禁不住就颓然了。兴致不佳,以前心安理得认为乐事的,今日出于勉强,差不多就甚感其疲,何况菲衣俭食,营养不足,身体也受了不少的恶影响。多劳一点神,多讲一点书,就感到头昏,感到不能支持。
幸而白知时还算有打算的教书匠,一看法币在贬值了,便赶忙将存款提出,交与一个做生药材生意的同乡去合伙。因为相信人,他是从不看帐的。那同乡——他和唐淑贞举行典礼那一天,这人还来参加过,吃过喜酒。——也真好,只要他用钱,从未拒绝,而且每年赚来的红息都给他转到本上。几年来,他算略略有了点经济基础。可是一星期仍然要教三十六、七点钟的功课,还要为同乡、为自己的外甥,为学生们,劳神费力的帮忙使钱,甚至还要为抗战胜利、为爱国热情而兴奋,而嚣嚣然地批评议论,他确实也累够了!
光是教书之累,还则罢了。为了黄敬旃要从军,差不多劳敝了八、九天的唇舌,以及三、四夜苦思焦虑,谁知刚刚着手挽救,便生波折,这个打击是何等的严重!然而致此严重之打击的,乃由于想不到的无妄之灾。这在精神与心情上,岂只是打击,剋实说来,简直是斩杀,简直是残酷的活刮,简直是最残酷的车裂啊!
当他那天匆匆出门,正要去找负责检验从军青年体格的霍大夫时,才不过走到街口,就遇见一个穿中山服而面貌好像在哪里会见过的壮年男子,笑容可掬的走来招呼他道:“白先生到哪儿去?”
不等他答言,接着又说:“有一桩要紧事,得请你到一个地方去走一趟!”
也是不等答言,便走来把他肩头抓住,很严厉的只“莫问!走!”同时,街边又过来一个短小精悍的小伙子,一只手抓住他右膀,一只手在他腰眼上一顶。他感觉到顶住腰眼的,不是手,而是一件小而硬的家伙。
他登时明白,他一定被匪人绑票了。这是成都以往常有的事。他早已听见过,曾经有个汉州粮户,为了避兵、避匪,躲来成都,不上半个月,一天,到春熙舞台看午台戏,到戏散出门,正拥挤当儿,忽觉背心上有件东西顶得生疼,忙抄过手去一摸,啊!一件冷而圆硬的家伙!同时,左右耳朵边都有很小的声音在打招呼,叫识相点,跟着走。
自然他也识相点,跟着走到街口,便被拥上一辆小汽车。而且两手立刻就着一个铁铐铐上,两眼立刻就着一片黑布扎得无一丝缝,汽车也立刻开走,起初还算感觉得出这是南门大街。
不准说话,他就不开口,心里倒觉坦然,“一定是弄错了,姓白的多啦!断不会是我这个穷教书匠!可惜没把书包带上,有书包,更可证明一定是匪人们弄错了。”他又微微有点诧异,今日的票匪们也真进步了,穿中山服不计外,还玩的是汽车,在十几年前,汽油像冷水样,倒还不算什么,可今日正是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时代啊!从前,倒也作兴绑手绑脚,用的大抵是温江麻绳,听说也有用湖绉腰带的,却哪能及今日的洋派,玩手铐,似乎还是美国货哩。
汽车不晓得走到什么地方,地面那样不平,想来绝不是城里的繁华街道。车子外,没一点闹声,只听见马达响,好久好久连喇叭都没有按过。
白知时脑经一闪,忽然记起二十八、九年几个跟他喊抗战到底,和在会场中痛骂汉奸汪精卫,并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青年的自行失踪的故事。据好些学生的传言,统是用汽车载走,一走之后,永无信息。有说送进集中营改造脑经去了,也有说简直就变了骨灰的。他于是才省悟了:“唔!我着了!我着了!这不是要我自行失踪吗?绝对是的!”
他全身都随汽车的颠簸而震颤起来。他本不要这样害怕,想穿了,也不过要命罢咧!何用怕?但是却没方法止住牙齿不哆嗦,止住两腿不像在秋风里的衰草样的抖。同时,口也干了,很想得点水来润一润。
“怪哩,我又不是生事的青年!”他这么想:“两三年来,本本分分的,并没有参加过啥子集会,也没在外头发表过啥子不满的议论。唔!也说过些牢骚话,那不过为了生活程度愈来愈高,谁不受着生活的威胁?谁又不对抗战前途表示悲观?这是事实呀!在教习预备室,个个见了面,谁不说‘这日子怎们过得下去呀?’连校长们都这样的在叫唤!唔!在讲堂上?倒说过一些题外话,那又算啥呢?还不是报纸杂志上全有过的!唔!难道学生中有啥子不满意我的人,在使我的坏?故意添盐搭醋的密告我?哎!多半是的。现在的学生,不比以前纯洁了。听说已有了什么三青团小组织,大多数都学会了当侦探的本领。中学生为了好升学,大学生为了有出路。哎,哎!坏透了!坏透了!”
但他毕竟是学科学的,还不敢不待证实就相信自己的假设。直到汽车又走上了较为平坦的道路,喇叭接连响了几次,转了几个弯,骤然停下,有人把他拉下车,装进一间上有楼板下是土地的小房间,而开去手铐,揭去蒙眼黑布时,他犹在从脑里追寻致其至此的其他原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以他这样一个人,而居然也受了几天意想不到的“优待”?这时虽听见了嗡嗡的警报声,大家不注意,他也没注意。直到第五天上,自己已经是在绝望当中,刚把一碗盐水饭吃完,突又被另两个不认识的人抓出,依然蒙了一块黑布在眼睛上,并被塞进另一辆汽车,又不知弯来弯去走了多久,猛的汽车停下,有人将他抓下来,只在耳边说一句“等五分钟!”人与汽车好像都走了,他还是莫名其所以。
他是最驯良的国民,而且是受过高等教育,又正在以教育为职业的人,果然非常守信的竟老老实实呆在被人安顿的那地方,静等了一准不止五分钟。听一听,四下静极了,只有远远的几声鸟叫,和草里的几处不大起劲的虫鸣。
他被抓上汽车和抓下汽车的一段时间,他简直记不清楚自己的心情如何,似乎已麻木了。只记得同房间的那几个难友曾经悄悄告诉过他:“要是有人提去审问,还好,到底算打响了,哪怕受些奇怪刑法,到底耍通了天;若能报了上去,更好,是政治犯就是政治犯,是思想犯就是思想犯,顶多枪毙,痛痛快快的,少受一些零星罪;不就送到集中营,管他妈的,受训练就受训练,作苦工就作苦工,到底见得到一点阳光,四体百骸也还多得一点活动的空间!顶可怕,就是这等不生不死的拘留着。再不然,就是胡里胡涂的弄出去黑办了,上头不晓得有这回事,家属亲友还在设法找人。真是,即有孝子贤孙要出个讣闻也无从叙起!”以及他被喊出去时,那几个难友的木然而又恐怖的惨白脸色。他早已料到,算了,这也是人生。“唉,就要光明正大,学元元,学刘文玉,高唱一节《柴市节》,也不可能哟!”他作了安排,等枪响时他一定破口大骂一场,以表示他的正气,他的不屈。——很久以后,他才想到,枪响时他还能不能骂?而且黑办的方法多啦,也不会等他有开口骂人的时间啊!
等啦,等啦,大约绝不止五分钟。没有人的声息,也没有枪和其他致人于死的什么东西的声息,“咦!怪啦!”两手一举,才发觉手并未被铐上。这才连忙把蒙眼的黑布取下,虽没有太阳,而从薄薄白云漏下的日光,到底是实质的光明,而久为黑暗所蔽的眼睛,到底一时还不甚睁得开。不过,他已是中年以上的人,人生的路程已经熟悉,并不必怎么留神,仅只一瞥,——实实在在仅只一瞥。——他登时就发现自己恰站立在成嘉公路武侯祠西过去数里,白贞女坊左近一丛灌木之后的野田埂上,脸朝着一道小沟。如其向前两步,包会栽在沟里。是泥沟,已经半涸,倒无死的危险,不过十冬寒月,鞋袜夹裤打湿,终不会令人高兴哩!
再一看,正是下午不久,路断人稀之际。“咳!他们倒选中了时候!”而白贞女坊,“噫!是有心开玩笑吗,抑是巧合?一定用过心的,叫人家明白,就一点儿小节目,他们也不含胡。何苦哩,人的脑经想不到是这们用的!”
大约一分钟罢?一辆盟军的吉普车飞驰的向城那方开去,接着成群结队的行人,成群结队的长途黄包车,成群结队的载重板车,成群结队的挑担、抬杠,成群结队的叽咕车,马路的灵魂复活了。但是早十分钟如此呢?时间算得也真准,“人的脑经想不到是这们用的!”
到这时,他也才恍然大悟:“把我放在这里做啥?哦!我一准被释放了!被释放了,我?但又为的啥?到底是误会了呢?还是”
他来不及再思索,真像被猎狗追急的兔子似的,三脚两步就迈过白贞女坊的已被拆了一半的石坊。——以前是巍巍峨峨,横跨大路,叫千千万万过路的男女们来瞻仰,来景慕,而其实并无一人要瞅睬这古董,也没人要知道白贞女到底是什么样人?是何时人闹到称为贞女而又能建牌坊的故事,到底是如何一段动人故事?想来,这贞女的一生,准是可歌可泣,说不定比哭长城的孟姜女的遭遇还为复杂,还为热烈!但是今日之间,并无一语传说,没一个人把她当龙门阵摆,那吗,这石坊真也立得没多少用!一自改修马路,这石坊还更委之丛莽,以前的巍巍峨峨,今日已残缺得快完了,“千秋万世名”吗?还不是“寂寞身后事!”白知时在迈过贞女坊、奔上马路时,是这样为他同姓的古女叹息,把自己的命运倒暂时的忘怀了。
跑回一巷子寓所,满认为唐家必然要大吃一惊。然而却不,吃惊的倒是他。
刚进大门,一般正在阶沿上努力洗衣的大嫂大娘们,便都丢下活路,伸起腰,个个笑得脸上发花似的,一齐叫道,“啊!白先生回来啦!啊,啊!快放火炮!快放火炮!”
果然,大门外霹雳叭喇铳!一串相当长而响的爆竹遂从大门外,一直燃放着进来。他就这样被人众们,被人众们的闹声和爆竹的霹雳叭喇铳,围绕着,直送进侧门。唐太婆三代人也已经个个笑得脸上发花似的,从堂屋里迎出来,还有向嫂,还有那个前任街正纪万钟。
爆竹才完,耳朵犹是嗡嗡的,纪老头子已一揖到地,一面说:“恭喜!恭喜!从此清吉平安,也从此安家立业。真是双喜呀!双喜呀!哈哈!白先生,想不到吃了场冤枉官司,反而红鸾照命。哈哈!我们倒联起姻亲来了”
接着,两厢里一般老年太婆、中年大娘,以及年岁参差的掌柜们,也都冲着他打拱的打拱,作揖的作揖,满口道喜,道贺。
贺他离开了班房,——管你正式的牢狱也罢,非正式的拘留所集中营也罢,他们总还沿着前清时代县官衙门里的名词,叫班房。皂班办公室,临时拘留人犯的私监,又名卡房,比正式牢狱还黑暗还糟的地方。——他懂得;用爆竹祓除他身上带回来的瘟气厉气,他也懂得;一群人如此像亲人样的欢迎他,他更懂得;但向他道喜这一层,却把他弄糊涂了。
向嫂端了盆洗脸水来,向他说:“把背时霉衣裳脱了。洗了脸,洗了脚,再进房里去!姑老爷!”
他急忙拿眼去看唐淑贞。她只是笑,眼睛眯成了线,上唇几乎贴拢鼻子,右手指头正拈了支纸烟。
还是纪万钟懂事,一面咂着根挺长挺大的叶子烟杆,一面慢慢向他说明,唐姑奶奶已把他们订婚的事,宣了布了。并且说,得力是亲戚关系,所以才没费多大的事,仅由姑奶奶花了几万元,凭两个表叔的力量,他才出来了,“不然的话,班房是容易出来的么?我当过多年的公事,别的人不懂,我是懂的。”
他还是呆眉呆眼的把唐淑贞瞅着。脸上没一点表情,好像才从噩梦中惊觉了,还未十分清醒的样子。
唐太婆诧异道:“这个人咋个了?是不是着了啥子迷蒙药,把心窍迷住了?”
纪万钟摇摇头道:“不是的。大概受了啥子非刑,伤着哪里了。不打紧,让他静静的养一下。姑奶奶,你同他进去,最好把你那安神的仙丹烧一口给他。”
他刚才走进唐淑贞的房门,便一把握住她的双手。握得那么重,她竟蹙起眉头,叫了起来:“哎呀!你做啥子?我的手!你看,几乎没有把箍子给人家嵌进指头去了!显你的气力大吗?呸!”
“唉!你是我的恩人!设若不是你,我一直是昏天黑地的,从没有想到你救了我!”
“这些空话留到以后说罢。我只一句,你得答应我。”
“绝对答应,你说。”
“也没啥子。我的话不要当成耳边风。从此以后,一切事情都得和我商量,并且要听我吩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