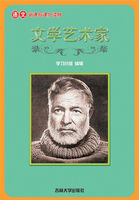[印度]泰戈尔
我们像是诗篇里散佚的一行诗句,永远感到它和其他诗行是押韵的,必须找到它们,否则它就完不成它自己的使命。这种对尚未达到的境界的追求,便是人心里最伟大的冲动,它促成了人的一切最佳创作。人似乎深切地感觉到在其生存的根子上有一层隔阂,他呐喊着要求引导他越过隔阂、走向融洽团结;而不知怎么的,人也明白,能把他引导到一种究极之爱的,无非是爱。
昨夜北风锋利如钢刀之刃,摊贩们用树枝枝叶临时搭了些栖身的棚子。尽管棚子简陋,当其时也,却是他们的最重要的必需品。然而,今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听见他们吆喝他们的公牛,从树底下拉出他们吱吱嘎嘎作响的车子。现在,对他们说来,紧迫而重要的是离开这些棚子了。
“我要”,自有它经常的平衡砝码——“我不要”。不然的话,“必需”这个怪物,就会以其不可改变的重量压垮一切生存。我们暂时会慨叹无物永久长存的事实,然而我们却永远免除了为万物均不变动的灾难而失望。万物留存和万物变动——在这两个恰巧相反的激流之间,我们找到了我们的栖身之所和自由自在。
我们的意志与爱情合为一体的时候便臻于完美的境界,因为只有爱情才是真正的自由。这自由不在于否定拘束。它自动接受约束,因为约束并不捆绑自由,只不过衡量自由的实际情况。不赞成奴役,而要停止服其劳。然而自由就存在于劳动服务之中。
一位孟加拉乡村诗人说:
在爱情里,结局既非痛苦,
又非快乐,却只有爱情,
爱情在约束你时给你自由,
因为爱情便是有所结合。
真正理解一首诗所需要的良好的审美趣味,来自按照想象力所见到的统一体的幻象。在我们对人生的领会方面,信念也有同样的功能。它是视觉的精神器官,它使我们在其实只见到部分时得以本能地认识到整体的幻象。怀疑论者也许嘲笑这种幻象是精神错乱所产生的一种幻觉,他们也许挑选些事实,把它们罗列出来,用以非难这种幻觉;然而信念却从来不怀疑它自己对内在真理的直接的心领神会。内在真理约束人、造就人、治愈人,引导人走向圆满的理想。信念便是存在于我们身心之中的、对于传遍一切的“是”的声音的自然而然的响应,因而它是人的生活里一切创造性力量中最伟大的。它不仅是被动地认可真理,而且一直积极努力,以达到同和平、善、爱的团结等互相和谐的境界。和平存在于宇宙中真理的节奏里;善存在于社会中结合的节奏里;而爱的团结,存在于灵魂中自我实现的节奏里。仅仅是这样一种节奏里的无数破绽,尽管是事实,在一个有信念的人看来,却不足以证明这种节奏是不现实的;正如在音乐家看来,刺耳的曲调和声音等普遍存在的事实,不足以否定音乐的真理。这等事只不过召唤他鼓足干劲去修补破绽,建立起同真理相和谐的境界。
东方破晓,白昼像个蓓蕾突破花苞、发为花朵。然而,如果这个事实只属于事物的外在世界,我们又怎么能找到门户进入这种境界呢?这是我们意识的天空里的一次日出,这是我们生活里一个新的创造,鲜花初放。
张开你的眼睛瞧瞧吧。就像一支活的长笛感受音乐的气息吹彻它的全身那样,感受领略这个世界吧。在你的生存的壮丽中与晨光相会吧,你在那儿是同它合为一体的。然而,如果你坐在那儿把脸转了过去,你就是在造化的并不分割的领域里设置了分隔的栅栏,而那个领域本是事物与创造性的意识相会的地方。
有的人对生命所抱的观念是静止的,他们盼望死后继续存在下去,只不过因为他们祈求的是永生而不是完美,他们喜欢想像他们所习惯的事物会永远持久不衰。他们在心灵里,把他们自己,跟他们固定不变的环境,跟他们攒积起来的任何东西,完全打成一片了,要他们丢下这些东西,就是要他们的命。他们忘记了生存的真正意义就是超生,这就是永远生长得超越它本身,更上一层楼。果实依附着茎,果皮依附着果肉,果肉依附着种子,是因为果实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准备好进一步的生长过程。果实的外层和内核还没有区分开来。它只是以其坚韧性证明其生命。然而,种子成熟的时候,它对周围环境的依附便放松了,果肉香了,甜了,超脱了,奉献给需要它的众鸟了。鸟儿啄它,损害不了它;风暴把它刮下来,甩在尘土里,也毁灭不了它。它以它的舍弃,证实了它的不朽。
一个真正的富翁和一个穷汉的区别是:前者财大气粗,能使家里有广大开阔的空间。一个富翁,他那塞满房屋的家俱也许是贵重的,然而,他用以使他的庭院开阔、花园广大的空间,其价值之高是无限的。商人做生意的地方堆满了货物,他无法确保空间不存放东西,他在那儿是吝啬小气的,尽管他也许是个百万富翁,他在那儿却是一贫如洗。然而,在家里,有些商人藐视只讲居室长、宽、高的实用性,——更不必提花园广大的实用性了——他把空间推上荣誉的宝座。这商人之富有,就富在这儿。
不仅未被占据的空间具有最高的价值,而且未被占用的时间也具有最高的价值。富翁财源茂盛,他能够购买闲暇。事实上,这是对他的财富的一种检验,看他有无力量留下大片时间的休闲地,哪怕“需要”也不可能逼他耕耘。
还有另一个领域,那儿开阔的空间是最最重要的——那是在人的心灵里。必须思考的、无可逃避的思虑,不过是烦恼而已。贫穷和悲惨的人们的千思万虑,缠绕着他们的心灵,仿佛常春藤缠绕着一座倾圮的寺庙。
痛苦关闭了心灵的一切门户。所以健康也许可以界定为一种状态,生理意识在其中休闲,仿佛一片空旷的荒原。只要在最外边的脚趾上患了一点儿痛风,整个意识里便充满疼痛,哪一个角落也无法幸免。
正如一个人没有未被占用的空间就不能豪华地生活一样,心灵没有未被占用的闲暇就不能高瞻远瞩地思考。——不然的话,对这样的心灵,真理就变成浅薄不足取的道理了。像昏暗的灯光一样,浅薄不足取的道理会歪曲视觉,引起恐惧,使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的交流的领域始终狭窄。
老人谨慎而并不明智。智慧在于心灵的清新,清新的心灵使人认识到真理并不藏在格言盒子里,真理是自由而活跃的。巨大的苦难把我们引向智慧,因为这些苦难是分娩的阵痛,我们的心灵由此从习惯了的环境中解脱出来,赤裸裸地投入现实的怀抱。智慧具有儿童的特性,随着知识和感情的积累而臻于完善。
教条和礼仪是一些渠道。根据其固定性或开放性,可能对我们的精神生活有所阻碍或有所推动。精神观念的一个象征,当其结构精细复杂得僵硬刻板之时,它就排挤取代了原来它应该支持的观念。在艺术和文学里,比喻是我们的情绪熏陶的象征,它们激起我们的想像,却并不拘禁我们的想像。因为它们从来不要求独占我们的注意力,它们为其他比喻的无穷可能性敞开着道路。如果它们堕落成为固定不变的表现习惯,它们就丧失了艺术价值。雪莱在他的《云雀》诗里倾泻出的形象,我们对之评价甚高,是因为它们不过是对我们无法计量的美学享受作些启发罢了。然而,如果由于这些形象恰当而又美丽,便通过一条法律,规定凡想到云雀时这些形象应该作为终极的定型对待,不允许作其他设想,那么,雪莱的诗篇就会立刻变成虚假荒谬的了,因为这诗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的流动有致,在于它的虚怀若谷,这诗默默地承认:它并没有用最终定局的词儿把意境说尽。
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仿佛是在听一支歌,我们欣赏这歌,并不等待,一直欣赏到歌儿唱完。歌声在哪儿,唱出第一个声音时就在哪儿了。歌的和谐统一,渗透及于歌的各个部分,因此我们并不急不可耐地寻求结尾,却随着它的发展欣赏下去。同样,因为这世界确实是个统一体,它的任何一部分并不使我们感到厌倦——只不过我们对世界的和谐统一理解愈深,我们的喜悦也随之愈有深度。我们各种不同的精力,用之于人和自然的世界里的各种不同的事物,当其时也,我们心中的一便逐渐形成,向往着万物中的一。如果众多与一,无穷无尽的运动与永远够得着的目标,在我们的人生里并不是和谐统一的,那么,对我们说来,我们的生存就像是永远在学习语法,却永远不能进而懂得任何语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