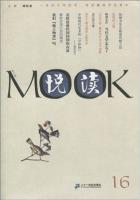张拓芜
他常搜索枯肠地写些故土风物的小文,别人或许觉得无甚足观,而他却慎重将事,摊开稿纸之前,几乎有沐浴斋戒、焚香顶礼的虔敬,一如抄经;他把平日的朝思暮想、感恋怀念发展成一种感恩的反刍。那宛如一坛陈年老酒,愈久愈甘冽香醇,愈久愈平和醪厚。其实家山对他来说应是模糊的,自十二岁那年离开故乡,就再没有机会踏进斯土半步。十二岁只是个少不更事的小不点,因为身在此山中,也不曾对山川草石多作深入的了解,而且足迹所及也只是附近几个村庄,离家二十五里的县城,总共只去过一回,但他对故乡似乎比他住了三十多年的台湾还清晰、熟稔。此所以第一眼看到那幅照片,就认出了是黄山。
那幅图的取景只是黄山一个小角落,不是名气响亮的天都峰、始信峰、蓬莱三岛、飞来石等等的名胜,但他竟一眼认出,好似老朋友久别重逢。他自己也感到有些奇怪、突兀,这究竟是佛家所说的缘分,还是故国家园给予他的精神感召!
他没有跟家人联络过,看到别人接读家书的欣喜和悲愁,他的心头更是酸潮翻搅。主要原因是他这四十年来一直坎坷蹭蹬,一事无成,乏善可陈,没脸向家人报告近况,二则故乡亲人都已年迈凋逝。
新近从同乡处辗转得悉,他的老父业已作古,由于消息来源九转十八弯,又欠详尽,强迫着自己不去相信。父亲应已有八十好几的高龄了(提起这件事,他就心痛如绞,罪愧交加,不知道老人家的忌日也就罢了,竟连父亲的年龄生辰也不记得,这样的人子不是真如畜牲吗!),这样的年龄逝世,也算享了高寿。得噩耗之夜,他去市场面摊上喝了两瓶小高粱。自从中风残废后,十多年来他已滴酒不沾,而今天非喝不可!一口一个干见杯底!通过喉咙时居然不辣不烧,从容而过!
回到家立即摊开一叠纸,恭恭正正地写下:“父亲大人膝下……”
离开父亲膝下已达四十四个年头,一万六十多个日子离乱分别,有多少话语、多少思念要倾吐诉说?但父亲业已作古,这封和着血泪的家书竟是欲寄无从寄了。也罢,我就用依稀的、不标准的,几乎遗失了的泾县土话读给壁上的黄山听,山山相连,血脉相通,请你转达给四顾山听,父亲的坟墓一定葬在四顾山脉的某个小丘的山麓。父亲啊,你听得到不肖游子遥远的呼唤吗?
晨起读报,迎眼便是洛夫兄的《寄鞋》,稍早,洛夫诗成付邮前曾在电话中念给我听,不待放下话筒便已老泪纵横,今天再详读全诗及后记,则更禁不住涕泗滂沱起来,一以悲恸,一以感恩,心中波涛起伏不能自己!
读诗竟读成这个样子,记忆中从未有过,大概这首诗与我有切肤之痛,大概洛夫下笔之时也是鼻子酸酸的,因他是我的好友,因他是位至性的有情人。
这双鞋我穿不下,我并未量脚给她。正如诗中所说:“鞋子也许嫌小些/我是以心裁量/以童年/以五更的梦裁量”的,我别她时均是十二岁的少年,虽然近半个世纪的漫漫岁月,但她记得的仍旧是分别时才十二岁的表兄(那是1940年的春天)。
莲子是大舅舅的长女,母亲怀着我时回南陵县娘家,舅母则刚好怀着她,姑嫂们谈着谈着就谈到肚子里的小生命,舅母提议指腹为婚,不管谁生女娃儿,一定嫁给对方的男囝子,当然,若是生的全是小壮丁或全是“赔钱货”那就不算。
在半个世纪之前,表兄妹结婚是理所当然的,是最亲密的亲上加亲。以前的人重信约,重然诺,说了就算,绝不反悔。上一代的一句话往往决定了下一代的一整生,对女人尤然。
听说她到了三十岁才被我父亲强迫出嫁,舅舅去世得早,舅母早已认定她女儿是张家的人,所以她出嫁我父亲便做了主婚人。
父亲只在1948年和我通过一封信,知道我那时在高雄当兵(他以为我当官,其实我只是个上等兵,但不好意思说实话,含含糊糊的让父亲去猜),三十余年生死茫茫无音讯,父亲想他这个不成材的儿子多半不在人世了,兵荒马乱,烽火硝烟的,一个随时要调上火线打仗的军人,生命犹如疯汉手中的玻璃灯——哪有不随时随地砸碎完蛋的!同时看到莲子年华老大,觉得我们张家对她大有愧疚,就强迫逼她嫁了出去。
前年夏天,一位同乡长辈寄来一张照片,一见这照片,始而悲恸莫名,嚎啕大哭,继之全身发冷,心头茫然!我正在烧开水泡茶,那一壶刚滚的开水竟然大半浇在下腿及脚背,因是大理石地板,积满了水之后我寸步不敢离,滑一交我便整个完蛋。伤到的部位热辣辣作痛,我知道若不早做处理治疗,这条腿会溃烂、发炎,而这条腿正是我赖以行动的唯一的一条健康的腿!
但电话离我尚有二三尺,我又不敢移动,痛就让它痛下去,烂也只好让它烂下去吧,这光景,我心中想的只是那张照片,其他全不存在!
照片是父亲的坟墓,其实只是一抔黄土,别说碑石,连小草也没一根,是真正的一抔黄土!
自从接到这张照片,心情丕变,在此之前从未想到要与海峡那边的家人联络,从此之后就积极地寻找管道,要问清楚:父亲是哪年哪月哪日过世的?享年多少?同时我要设法托人寄一点钱去,为父亲修个稍微像样的水泥坟,立块碑,碑的左下方刻上我们诸兄弟姐妹的名字以及我们的下一代以及莲子的姓名。她在父亲膝下算不得媳妇,也算不得女儿,那就老老实实地称姨侄女或表侄女吧。
三位弟弟我都不认识,连名字也不知;他们不是我的同胞弟,是我在1940年离家后,继母陆续生的。
看到照片,我知道他们实在没有力量为父亲筑一座稍微像样的水泥坟,这个担子应由我这个不肖的长子来挑。诸弟虽然穷困,但都在父亲膝前尽了菽水之欢,而我这个当长子的,不但未能在膝前承欢,甚或数十年不通音讯,生死茫茫!这样的人子真正不肖不孝至极,真乃牲畜不如!
然则,我能尽的儿子的责任,也只有这些了。
莲子早就知道我已残废,离了婚,目前与唯一的儿子相依为命,便一再表示要来我这里,照顾我父子。我想她没有这责任,而且分别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她如何能来?又怎样来得了!
她不但是个大字不识半个的“睁眼瞎子”,并且是个十足的没见过世面的乡下老妪,别说出“国”,离家才二十五华里的县城有没有到过都成问题!她不会说普通话,广东话、闽南语更是闻所未闻,不会看路标、路牌,她怎能出得来,又怎能入得了境!
莲子六七岁时即来我家,一直职司婢女使唤工作,母亲在世时只担任洒扫庭院,尚无人轻视她的地位(她是母亲的亲侄女),但母亲去世继母进门之后,她的地位就一落千丈,砍柴挑水照顾弟妹,种田烧饭洗衣等等粗重分内工作之外,尚得忍受父亲和继母的詈骂叱责及掐、打!
我离家出走,逃到孙家埠油坊当学徒之后,姑母和姐姐都与父亲和继母决裂。在我未成年成亲之前,她们绝不回娘家,莲子挨了揍、受了气,连个哭诉吐冤的对象都没有了。舅舅曾想接她回去,等我们长大了再接过来,但舅母认为她已是张家的人,不让接回家,而继母是因为憎恨我而祸延及她,我不在家中碍继母的眼,久而久之她的处境会好转些。如此,她只得认命了。
她受的这些罪,我全然不知,我也不怎么关心她,因为我在店里当学徒的苦日子并不亚于她,我是泥菩萨过河啊!
这些,都是姐姐亲自踅着小脚走了三天来孙家埠探望姐夫和我时,亲口对我说的,但我也只听听而已。那年是我学徒的第三年(1943年春天)。老实说,那光景我还不把她当回事,我根本没想到将来要和她拜堂成亲,因为我自己还养不活自己,我只是对舅父舅母有一点点抱歉而已,对她还不曾想到!
3月27日洛夫的《寄鞋》刊出后,接到好几通友人的电话,对我表示慰问之意。洛夫诗的魔力真大矣哉!
我和表妹都已是花甲之人,还能活几天?见面的机会,此生恐怕是没有了。唉!我比莲子幸运,至少我还能捧着一双布鞋仔细研读,她呢,她有什么!
纸雁儿
苏叶
我父亲去世,整整十个年头了。
那天,他和平日一样早早起来,母亲给他打好洗脸水,父亲平静地说:“我蛮累。”母亲就搬了一张椅子让父亲坐着,然后绞了热毛巾替他老人家揩面。忽然,父亲头一歪,就这样去了。
人们说,父亲高寿,又是无疾而终,是福人了。
火化那天,一切仪式完毕,我们绕过挂着他老人家遗像的屏风,向躺在灵床上的父亲告别。我双膝一软,就地跪下,搂住他恸哭。那一瞬间,我感觉到我的血肉之躯和他联系紧密,而我什么都还没有来得及替他做,他就这样平静淡泊地去了!我多希望他还能活着,还能看到我!
其实,父亲不能看见我已有多年。他双目有疾,白内障,渐渐地终至失明,连光感都没有了。我不知道我留在他脑子里的最后的形象是什么模样,而我对他的最早的记忆,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他总穿一身青布长袍,头发有点花白了。每次他从离家几十里外的学校回来,总是双手背在后面,让我猜他给我的礼物——一个金红的柑子,或一个银黄的柚子。我有些陌生,有些好奇,有些娇憨地仰望他,然后看他手执毛笔,在薄薄的纸上竖着写了一行又一行。他的字十分清秀,像他的手,超凡脱俗,修长修长。他的眼睛很慈和,但是有一颗很小的白点。我不知那白点是何时开始逐渐胀大,终于使一双眼球布满了云翳。父亲闲居之后,先还拄手杖出去看戏,后来就不出家门了。先还看书,书和眼睛的距离愈来愈近,后来贴近面孔看,简直像闻书一样。再后来,眼镜也废了,他再不能看什么了。
我时常痛悔,二十年前,我的心长到哪里去了?我为什么不曾体会父亲双目失明后的忧乐与心境?
我给父亲念过书报,讲过外面的事,给他老人家沏过茶,端过饭,牵他在院子里晒过太阳……但做这一切时,我都没有用心。我在父亲渐渐失明的过程中,渐渐习惯了他的状况。母亲学会了理发,她让父亲坐在藤椅上,胸前背后围上一块布,父亲微笑着,顺从地低着脑袋。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满头银丝,显得超逸和清淡,使我察觉不到他的痛苦。有时,需要剪指甲了,他叫我。我,多半在忙自己的事,常常“嗐”叹一声,嫌烦,然后拿了剪子,坐到他身边去,剪得很快。父亲便默默地用指头互相搓磨着不匀的地方,我心一愧,再细细给他修一回。
他听广播,听新闻,听京戏。八个“样板戏”的时候,父亲实在嫌它们闹,不听,每天只听天气预报。常常下午5点钟一敲,他就喊我开收音机。天天如此。我有时说:“您老人家听么子天气预报罗!”言下之意是您又不出门,何必如此关心呢?那是黄昏时节,多半是天空云蒸霞蔚的时候。树叶儿映着夕晖,沙沙翻卷,有如奔马的铃响。归鸟啾啾,来回飞翔。燕子衔泥,轻轻剪开芬芳的草地……这一切父亲都看不到了,可他是否借助于季节的更替和天气的变化,在脑海里描画着什么呢?我那样忤逆地回答他,无异于打趣他,堵他,他为什么不训斥我,不责备我呢?
父亲是个细心、慈爱的人。那年“大跃进”,母亲被拉去修京广铁路,不能回来。父亲每天给我梳辫子,梳两条柳瓣儿一样匀整秀气的拖肩辫子,引得同学们都羡慕。那是父亲在我能力稚弱时给我的帮助爱护,而我,当父亲能力衰颓之后,在他视界黑黑的天地里,我给予过他什么温暖,什么安慰,什么帮助吗?
父亲眼睛失明了,可父亲一直在看着我。记得那天夜晚,我回家迟了,远远看见路口立着一个人,是母亲。“你到哪里去了?”母亲说,“玩到这时候回来!把你爹爹急死了!”
我惭愧地跑进房去,看见父亲坐在床上急扇扇子,一脸焦躁,纺绸褂子早褪在一边,身上仍是汗流如雨。我内疚加感动,几乎要哭出来。他听见响动,向我仰起脸,张大了眼,那灰色发亮的眼睛似乎明澈了,似乎要洞穿我的心腑,透着那么重的爱,惜,忧,叹……使我不敢对视。
父亲没有说我什么,他一生从不对人讲重话。他自尊,又尊重别人。他好像很怕打搅了世界,很怕烦扰了家人。他的饭菜是母亲单做,端到书桌前,让他单吃。他总是倚着椅、柜、桌,很从容准确地摸过去,坐下,就餐,不肯让人扶。他很少迟滞懵懂的样子。他是暗里用了努力,不使自己成为家人的负担吧?也许,他就是要掩饰自己的困难,以此麻痹我们对他的关注,来减少由这关注而带来的所谓“拖累”,以防止由“拖累”而引起的厌烦吧?啊,父亲,我真不敢深想,细想。
给老年人摘除白内障,是近十年来愈臻成熟的一项医术。十多年前,国内也有一两处地方可以开刀。可是父亲执意不肯,大约也是怕麻烦人。而我们觉得父亲年事已高,加上路途不便,有风险,便没有坚持去做手术,也没有另想一些更积极的法子。
父亲时常一个人坐着,恬淡的微笑中略有沉思,不知在想些什么。他的生活越来越寂寞了,他把这种寂寞深埋着,留给自己一个人吞咽,有时,父亲要求帮母亲剥豆,或是绕绒线,都做得井然有序,干净利落。临终的前一年,父亲忽然多了一种兴致——折纸。
他要我找一些用不着的书给他,他一张一张将书页拆散,然后摸索着,折呀折。对角折,对边折,翻角折,翻边折。我背地里和母亲说,这有什么意思?母亲却说:“你们都只顾忙自己的事,哪里晓得一个闲人的苦恼!何况他两眼又盲了,时间是难熬的!”
我怏怏地听着母亲这些话,心里觉得有些难过,可是过后,我还是只顾忙自己的,并没有设法帮他排遣什么。等到父亲去世,我收拾他的床铺,一掀褥子,我发现棕绷上有一扎一扎用细绳子捆起来的纸工制品!有雁儿,鸟儿,猴儿,兔儿,鱼儿……折得精巧细致,形态玲珑!这些能飞能走能游能跳的活物儿,都是出自父亲之手吗?父亲,您是用一种什么心情,在孤寂的黑暗中,制造了这么多活泼的生命!您是带着怎样的企盼和心愿,活在它们的色彩与声响之中?我痛哭着。
父亲故去有十年了,他偶尔会走进我的梦里来,不说话,安静地笑,眼睛明亮。午夜梦醒,我听着窗外如雨水般的树叶的嘈切之声,心上似有一个深深的空洞。我没有父亲了,我这一辈子已无法补赎我对他的歉疚了!我常常感觉到我心上这一道深渊,它提醒着我,对人,尤其是对残疾人,少一些冷漠,多一些关切,少一些自私,多一些爱护,让人类在扶危互济中,奋发向前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