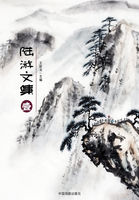古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地方一种物产,有出金丝枣的,有产枸杞子的;有的地方出蟒蛇,有的地方产熊猫。人群也不例外,一方水土出一方人。过去人们常说:浙江的绍兴府出师爷,直隶的河间府出太监天津卫的三河县出“老妈子”。那么,我们关外有什么“特产”呢?特产很多很多要说“两条腿的”,那就非“胡三太爷”莫属了。
在“东三省”六十年前,外面的世界有日本关东军和伪满的宪兵队“守候”着,什么“营造日满亲善的王道乐土”的鼓噪,甚嚣尘上;可是,我们所在的那个角落,却好似被人遗忘了一般,“膏药旗”从来也没有插过。当局说它是“兵荒马乱”、“土匪如毛”之地。这里也确是一向都“不服天朝管”,每当青纱帐起,那些手持各种兵器的“顽民”便四出活动,闹得个云低日暗,沸反盈天。
这种人,在我们那一带通称“土匪”,或者调侃地称为“胡三太爷”,也有叫他们红胡子、棒子手、马贼的。这是一种以抢劫为职业的武装暴力集团,有别于砸门撬锁的流贼、小偷小摸的络窃,突出的特点是武装化、集团化。成分十分复杂,成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家贫如洗,衣食无着,为着混口饭吃的;有的是抗租、逃税,或者逃避抓壮丁、下煤坑、当炮灰,溜到里边“暂栖身”的;有的由于命案、奸案、盗案或民事纠纷遭到缉捕、追杀,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也有的因为输钱、欠款,无力偿还为逃债而出走的;还有一些市井无赖之徒和个人野心家,为了求个一官半职、发家致富,或者威镇一方、称王立“棍”,结伙搭帮,铤而走险,正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当地的土匪头子、后来成了奉系军阀首领的张作霖,便是最典型的一个。
我的一个舅爷和表姑父,早年都曾吃过这碗饭。他们究竟是何因由,其说不一。据我祖母说,这个舅爷原是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一次嫖娼中争风吃醋,失手打死了衙门里的什么人,就落草为寇了。到了晚年,好像他也没有攒下多少钱,却落下了残疾一瘸了一只腿,右手少了两个指头。小时候我见过他,高高的个头,挺大的脑袋坐在炕上腰板标直,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见着酒就馋得流涎水,左手端着酒碗,拇指和无名指翘成一朵兰花,不管碗里面酒多酒少,总是一饮而尽。
每逢来到我们家,特别是三杯老酒下肚之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当日匪帮内部的情况。原来,土匪里面多数都是本地人,绝大部分不识字,粗野、暴戾、凶狠是他们的特性。内部虽然不如帮会那样组织严密,但是,也都具有松散的指挥系统和应该遵守的不成文的“帮规”。比如,遇到送亲的喜车和送葬的丧车一般的不劫不抢,主要是图个吉利。摆渡的、行医的,一般也不抢,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金银细软,主要是土匪渡河离不开“船老大”;经常出现伤号,总要找医生治疗。耍钱、赌博的不抢,有歌谣在:“西北连天一片云,耍钱劫道一家人:清钱耍的赵匡胤,混钱耍的十七尊。”传说,赌钱的祖师爷是宋太祖;而胡匪的开宗初祖是“布袋和尚”——他是“十八罗汉”里的第十七尊。所以,许多土匪的胸前要挂一个小铜佛。另外,他们出于生存的考虑,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打扰当地的父老乡亲(实力雄厚的大财主除外),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
土匪都特别迷信,他们嘴边不离八个字:“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匪帮头目往往都把烧杀劫掠等各种活动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以便于笼络徒众的情绪,鼓励他们在绝望中挣扎。记得一本书上记载过这样一件趣事:有个老汉在大风雪天撞上了土匪。一个新入伙的“崽子”见老汉胡子上冻了一层冰溜子,顺口说出崎,这天头真冷,冰把胡子围住了。”其他人一听,愣神儿了。为了除掉晦气,他们想要拿老汉开刀。老汉反应很快,忙着用手一抹胡子上的冰,说:“没关系,围不住。冰是临时的,胡子是长久的。”匪徒听了,高兴地说这话中听。放他走吧!’,
书上还说,土匪都有三样必备的东西:一件是后面带有长毛的狗皮帽子,因为他们常把短枪藏在脖梗子后面;一件是“护屁子”——一块绑在屁股上的毛皮,便于随地而坐防凉防潮;一件是腰带子,一般都是十二尺六寸长,遇有紧急情况,一头拴在楼房里的凳子上,一头攥在手中,然后纵身跳下,有时候上树、爬房,长长的腰带子也能提供方便。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倒没有问过那个土匪舅爷,因为他早已死去了。
我那个表姑父寿命倒很长七十年代初还在世。他在匪窝里面混了三个年头,后来改邪归正,逃到大兴安岭当了伐木工人。每到旧历年根,他都休假探家,有关土匪的许多知识,我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他说,当土匪有两个门径:一种是自起炉灶,占山为王,内部黑话叫“起局”;另一种叫“挂柱”,就是搭帮入伙他自己就属于这种情况。
那年秋天,县公署抓壮丁去给“皇军”修炮垒,轮到了我这个表姑父头上。走在路上,他听人说,为了怕走漏风声,炮垒修完了,鬼子要把民工统统活埋。表姑父心想,左右都是一个“死”,干脆跑它个“狗日的”,有幸逃出虎口,还能捡一条小命。于是,在一个夜黑天里,趁着“解手”,一溜烟似地钻进了高粱地里。尔后,转游了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四海”绺子,入了伙。
原来,土匪把队伍拉出之后,都要报个“字号”。这种“字号”,一般的既是匪帮的名头,也是它的大头目的代称。除了这个“四海”,那个时期横行在我们那一带的,还有“青山”、“老二哥”、“四虎”、“大海”、“大老挖瘩”等十几伙。
表姑父开始“入围”时,不懂得匪帮内部的专用语言(通称“黑话”),一张嘴就遭人嗤笑。以后听人说惯了,逐渐地也学会了把推牌九叫“搬砖”,把银子叫“老串”,把信件叫“海叶子”;懂得了“眼线”就是通风报信,“插千的”是密探,“拉线”是给匪帮带路,“打闷棍”是劫道。这些黑话据说共有五百多种,三年过后他也说不完全。
土匪的活动天地,一般都是晡聚山林,而在我们那一带主要是占据苇塘。每到苇叶齐腰时节,便进入了活动旺季。大帮的土匪主要是“砸窑”(即攻打大户人家的宅院),人数不太多的往往把重点放在“绑票”(掠劫活人为质,借以勒索钱财)上。
听父亲讲过,早年他给“何百万”家扛活。这是辽西一户有名的大财主。家里有枪支、炮手,防守严密,“砸窑”是很困难的。可他又是一块“肥肉”,不叼进嘴里,匪徒岂能甘心。于是,他们便通过智取,把“大掌柜的”抓走了。
本来,为了防备“绑票”,“何百万”一年到头蹲在家里,不走出大门一步。这天,他正躺在炕上,和小老婆面对面地抽鸦片烟,突然,有人进来报告:房后祖坟上有人祭祖,大队人马,穿袍结带,吹吹打打,闹得不亦乐乎。“何百万”说不管他!”过了一会儿,来人再次禀报:这伙人点名骂他“是姑娘养的’,说他吃喝嫖赌,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把祖上的阴德全败坏了。“何百万”感到蹊跷,他也弄不清楚这是族中的哪一支人,究竟来自何方,到底有什么来头。盛怒之下,抛下了烟枪,走出大门,后面紧跟着四个“打手”。那伙“祭祖”的人像是没看见一样,根本不和他打招呼,照样地焚香磕头,照样地骂骂咧咧。他气得大吼一声:“还不给我打!”可是,没等“打手”上前,已经有两个被那边的“神枪手”掲开了脑壳。然后,三拳两脚,就把“何百万”干倒,捆起来,带走了。
匪帮给他蒙上双眼,带到一处匪窑里,一张口,“票价”就是五千块大洋。“何百万”岂肯答应,又羞又怒,愤然绝食。第二天早晨,匪徒割下了他的一个耳朵,让“花舌子”(说客)给送回家去。这下可吓蒙了他的一妻二妾和大少爷。他们满口应承,两天之内,就把这笔天大的款项如数凑齐交上,才算保住了一条老命。
地了场光、庄稼进院之后,土匪便转入了“猫冬”期,分红,结账有家的回家,没有家的投亲靠友,或者带上银两和姘头远走他乡。这时,正是他们挥霍资财、寻欢作乐的时刻,有的吸大烟、听小戏,有的耍钱弄鬼、设局抽红,有的去找过去相好的女人鬼混。待到第二年春夏之交,青纱帐起,他们又都回到事先约定的固定地点集结,继续劫掠一些殷实富户。
这一带尽管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但就民风来说,还是质朴憨厚,豪爽好客的。过往行人随便走进哪一家,只要赶上开饭时刻,都会被让到炕桌前,有干的吃干饭,没干的喝稀粥,吃完了任你抹干嘴巴走开,分文不取。人们进了西瓜园子,口渴了可以摘瓜吃,但是不能带走,而且,要把瓜籽留下。听说,医巫闾山的梨园也是这样,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可以伸手摘梨,放开肚皮吃,只要不揣走就行。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这一带的人,说是愚憨可以,说是强焊、粗鲁也无不可。人们说话声高,即使随便闲谈也像吵架似的,动辄满嘴喷吐沫,脸红脖子粗。有人形容:一句话不投合就瞪眼睛,两句话不中听就伸拳头,三句话不顺心就动刀子。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了。但就那些“耍光棍儿”的刺头来讲,还是恰如其分的。赌钱输了,掏不出票子来下注,他就回身扯出一把杀猪刀,从自己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块肉来,抛到牌桌上,吓得赌徒们“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吭声,这样,就算立下了“光棍儿”,以后见面就要以“爷”相称。
当地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特别要“面子”。有的明明只喝了一碗稀粥,在人前也要装出一副吃过了鸡鸭鱼肉的样子,不停地打饱嗝,还要半天半天地剔牙缝儿。打架时一看要吃亏了,赶紧往回跑,还要高声叫着:“你等着,不要动,我先解个手,回来狠狠地收拾你!”
还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屯子里有个赵书阁,逢人就讲他的“优胜纪略”:有一次,他在西河沿推牌九,一个通宵赢了四十根金条,往哪里放呢?情急智生,就把一根根金条并排缝在一块厚布上然后往腰上一缠——,说到这里,他眉飞色舞、神气活现地问周围的听众你们知道什么叫“腰缠满贯’吗?就是像我这样!”他接上说:“可是,没有料到,一出大门就被“胡三太爷’盯上了,走出二里地外,“啪、啪、啪甩过来一梭子,冲着我的腰身打过来。你猜怎么样?安然无事,——一个个弹头都被金条挡回去了,只是马褂上落下了几个小窟窿。我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枪来,瞄准他的后脑勺,“机’地一声就撂倒了。”
土改时搞清算,划成分,明知道他是一个穷光蛋,一双肩膀支着个嘴,三天两头揭不开锅,可是,有人仍然检举了这件事。工作队长带着记录员,郑重其事地找他谈话,交代了政策,指明了出路,要他打消顾虑,把金条如数交出。赵书阁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架势,一时哭笑不得,只好彻底“坦白”——那些话全是自己瞎编的,一边说,一边打自己的嘴巴。逗得小记录员笑痛了肚皮,笑出了眼泪。
在我们村子东面,影影绰绰看得见一点轮廓的是高升镇。这是周围几十里粮菜、柴草、畜禽的集散地和交易场。我五岁那年,第一次跟随父亲去赶集,觉得除了天大地大,就是高升街最大了。说是只有八里地,可是,我却觉得很远很远,那段路老半天也走不完。高升镇的东北方,三十里外有个张家堡子。本来没有什么出奇的,只因为这里是少帅张学良的出生地,远近就闻了名。五里八村的人提起这个“小六子”,个个眉飞色舞。有的说,这个人厉害得很,眉毛一耸,连小鬼子也惧怕三分。也有的说,他喜欢跳舞,身旁有两个能干的女人。在我的想象中,这个人一定是个挎双枪、骑大马、脚登高腰皮靴、身长八尺、一跳一丈高的武把式。不然,怎么会那么出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