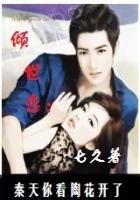马枫VS易安
时间:2005年4月25日
地点:绍兴亚都大酒店
马枫:以前只在网上对话,没想到这次在绍兴能与你相见。
易安:是的,世界如此之小。
马枫:这次访谈,我想从你童年的生活经历开始。
易安:好的。在这里,我要先说到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是一个叫禾青的小镇,几乎位于湖南的几何中心,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那里河水湍急,山也很高,老家的屋前是一条叫龙溪的小河,屋后的高山是雪峰山的支脉。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去河边和山上,捉鱼、游泳、放牛、摘野草莓、种豆、挖薯、割麦……这些都成了我童年生活中最难忘的经历。我一直庆幸自己生长在农村,一出生就和泥土、庄稼、蓝天、白云、青草、野花、溪水、动物、昆虫等大自然的事物发生了最亲密的联系。
马枫:看来,这种对家乡的热爱无疑影响到了你后来的写作。你是如何开始你的诗歌写作的?
易安:其实我最先的兴趣是绘画。在我刚上学的时候,我就喜欢用铅笔在白纸上勾画下一些眼前的事物。记得八岁那年,我常趴在二楼窗前母亲的缝纫机上,画下对面的山岚、树、房屋和远处飞过的鸟影。因为入神,有一个下午,母亲拿着一件破了的衣衫在我身后站立了半个小时我才发觉。没想到母亲不但没责怪我弄脏了她的缝纫机,反而夸我画得像。从此开始我就有了用笔去捕捉这个世界的兴趣。我最先的写作是在父亲的指导下进行的,那是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平生第一篇看图作文就得到了老师的表扬,从此埋下了兴趣的种子。那时我的作文总是好过同龄人。在初中的时候我开始学会了用诗的形式写赠言,真正的诗歌写作是在15岁的时候,是在我第一次完整地读完汪静之的《惠的风》和洛夫的《诗魔之歌》之后。
马枫:除了写诗,还进行其它的文体写作吗?
易安:还有散文、歌词、小说、纪实作品,但以诗为主。其实我最先变成铅字的是一篇《雨季-误区》的校园小说,用笔名雾迪发在一本叫《长岭人》的杂志上。但后来我更喜欢写诗,是因为发现了诗歌语言的魅力,往往一篇较长的散文可以浓缩到诗中。打个比方,散文还在写“冬天去了,春天来了……”的时候,诗歌已经直接发现了“雨燕振动的翅翼”。
马枫:我最早注意到你的诗歌是在1997年,那时候我正就读在北方的一所大学,喜欢泡在学校的阅览室里,那一年,我从《诗歌报》月刊上读到你的《城市舞女》等三组诗作,感觉到你是一个充满忧患、失落、又满怀激情的人。后来从《北方文学》上读到你的《父亲在春天里打井》,又发现了蕴藏在你内心深处的苦难。印象中,易建东三个字便突然从报刊上消失了。
易安:我从1992年开始正式发表诗歌,到1996年是我的诗歌写作中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一有时间,便自觉地读书写作。然后投稿,那时我的家庭生活很幸福。父母身体不错,兄妹相继毕业工作,初恋也很甜蜜。当时没有什么不良习惯的我,读书写作成了我业余生活中常受亲人和朋友夸赞的一部分。那时我的爱好就是到处捕捉诗意,一棵树的蓑老、一个女孩迷离的眼神、一个劳动的场面、一处被冷落的风景……常常令我心有所触,再慢慢写到纸上。这种状态在1996年下半年开始改变:母亲突然病重、父亲离职、五年的初恋告终、单位发不出工资,所有这一切如此突然地降临到我身上,让我无所适从。常常一个人愣坐着发呆。至1997年底,断断续续大概就只写了20来首诗,后来陆续发了一些,其中就有你所看到的那几首。此后,我基本中断了写作。
1998年下半年,我在母亲病逝不久后也厌倦了单位的机关生活,便主动申请下岗,离开了家乡,去省城打工。
马枫:但后来,又陆续看到你的很多新作。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再次提笔写诗的呢?
易安:我去长沙后,便在一家杂志社应聘做编辑、记者。同事中有几个写诗的,于是我也不断认识了居住在长沙的远人、韦白、易清华、唐兴铃、谢宗玉等一些诗人和作家朋友,时常和他们在一起聚会,并再次产生写诗的冲动。其实严格点讲,从1998年至2000年间我并没有完全停止写诗,偶尔会在笔记本中写一两首,但写了便丢在抽屉里,不再投稿。2001年,那时我学会了上网,将两组新写的诗歌贴在了《诗生活》、《天涯社区》、《尚书屋》等网站上,一组是城市题材的,一组是乡村题材的,当时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喜爱。后来一些文学期刊、民刊和网刊选发了其中的部分作品。
马枫:2003年,我先是在《人民文学》和《诗潮》读到你的《1997年的一次乡间晨跑》、《为母亲梳头》、《河边的打铁铺》,紧接着又在《诗选刊》读到你的《世界的两面》等作品,这是两种不同语言风格的写作。说真的,我很难把它们看成是一个人的作品。
易安:这和我的生存状态有关。经过多年的读书、工作,时间已把我变成一个城市人。但城市无疑是令我失望的,虚伪、隔核、势利、冷漠、贪欲和各种生存压力,正渐渐同化着城市中每一个人,包括我。因此我在涉及城市题材的写作中,心态也是充满嘲讽和无奈的,表达的角度和语言较之乡村题材写作时的宁静心态有所不同。我喜欢在夜里让自己安静下来,复活从前的乡村记忆。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在白天穿过城市,夜晚回到村庄的漂泊者。
马枫:许多人认为你的《我想对每一个女孩说》超越了舒婷当年广为传诵的《致橡树》,认为舒婷只是简单地模仿了裴多斐,而你的《我想对每一个女孩说》却几乎呐喊出了这一代男青年发自内心的原始的失落和伤感。
易安:怎么说呢?那个年代我还在读初中,从后来的阅读中知道那只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之所以朦胧诗风靡一时,我想肯定和那时的娱乐休闲方式缺泛有关,读书是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因而一首适于朗诵的诗很快就可流行,一夜之间成名。就像现在的明星一样,成为公众人物。那个时代诗的功能是被扭曲和夸大了的,并且官方主流媒体也在其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现在的人都在忙于物欲的满足,媒体也只关注政治、经济和娱乐,文学(尤其是诗歌)受到冷遇。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在目前才回归到了它的本真,不再被政治利用,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内心对于世界的真实感受。但是一首让人喜欢的诗歌,肯定也有被人记住并流传下去的可能。我在写《我想对每一个女孩说》的时候,并没有想着去超越什么《致橡树》,我只是目睹着现在的女孩被金钱和物欲不断俘获后有点感伤。这种感伤在读到《中国青年》杂志曾经为“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爱情”展开讨论的一系列文章后更加强烈,于是带着一种呼喊、无奈、企盼的心情写下了这首诗。
我为这首诗能够打动一些人感到满足,并没想着它能产生多么大的影响,给自己带来多么大的名声。
马枫:你怎么看待诗人身处在常人间的身份问题?
易安:我一直以为,我们对“诗人”身份有误解的地方,包括写诗的人自己。其实“诗人”的身份并不存在,只是存在于他写诗的过程中,一首诗写完了,“诗人”的身份就结束了。这句话,我曾经在2002年冬天在桂林和哑石的一次相遇中提到过。我现在的另一种富有意味的解释是:这就好比一个“妓女”,她只有在卖淫的过程中你才能说她是“妓女”,如果她卖过淫后又和自己喜欢的男人一起做爱,你说她还是卖淫这就对她不公平。写诗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细节,卖淫只是做爱的一种异态,都不是全部。
马枫:哈哈,高见!说到写诗和做爱,我就想起了你的《楼下》和《女演员和她的影子》。我记得这是你在网上反响比较大的两首诗,曾在诗生活和天涯社区等着名网站引发争论。我发现其中一个有趣的地方,即“河蚌”和“深渊”都是表述女人的阴部。
易安:是的,但两者表达的内容是不同的。《楼下》描述的是一个生活在颓废和无聊中的人,在无意间看到楼下一个穿超短裙的女子撅起的臀部时,那种沉闷突然被打破后的兴奋、意淫及后来的怅然若失。无意表达什么,象征什么,只是描述现实中确实存在的一种生活状态。《女演员和她的影子》则是对当前演艺界的虚妄生活的一种厌恶、批判。“河蚌”是灵动的,而“深渊”是黑暗的。
马枫:现在,我想谈谈你的乡村题材的诗歌。无疑这也是你的诗歌写作中最重要的部分。
易安:我一直有个愿望,要把我在乡村生活中的经历、经验和乡村中的俗事风物尽可能的记录下来,用一种自己的诗歌语言,写下自己的乡村传。但我的写作状态常常停顿了下来,我为此苦恼,甚至感到力不从心。
马枫:是否想到要放弃?
易安:这应该不会吧,但需要努力。
马枫:我记得初读到你的《盖屋顶》《河边的打铁铺》《一个冒雪锯木的清晨》等诗作时,只感觉到你在叙事和抒情时的漫不经心。但再细读时却发现了你在平淡叙述中隐藏的突兀和不断深入下去的力量,字里行间陡然生出一种气韵,形象点说,这种气韵就像冰层下河水的流动。我想这是在我静下心来阅读你的诗歌后,找到了你的诗歌中的语感,或者说,真正进入了你的诗歌中的秘道?
易安:先抛开我的诗。谈到读诗,肯定得戒除浮躁。我想,阅读好的散文和小说也同样如此。汉语是鲜活的,文字本身深藏着内蕴,我们只有在细腻的阅读中才能感受到它的奇妙。
马枫:你是否在意别人对你作品的评论?
易安:我认为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别人关注并不是一件坏事,不管这种评论是批评还是赞誉。
马枫:2001年,着名诗人刘洁岷在诗生活网站论及你的诗时有这样一段话:“易安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自不待言,他在他的诗中较生动、妥善地化用了这些经验,以与其质朴、明快的诗风相谐和。易安的突出点是其控制力,他对情感抒发和理念呈现都相当谨慎与节制——这是因为他对‘诗意’有较清晰的把握。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与国内其他写乡村题材的诗人有了明显区别。”你是怎样看待这段文字的,对你的评介是不是很准确?
易安:应该说,刘洁岷是那个一语将我击中的人。我们至今未曾谋面,但我觉得他对我似乎很熟悉。他说到我的诗中“语言的本真”时,说“这是一个还原了的乡村孩子的想法”,并问我“是自发的抑或有几分自觉?”我无言以对。什么都被他洞见了。我一直想用自己的方式写下自己的乡村,描写出乡村生活中的那种原始、在场、温暖和巨大的人情味,并且把自己的炽热情感掩藏在平静的叙述之下。我仍然做的不够好。
马枫:但是这两年又很少看到你的新作了。是陷入了创作的低潮还是又一次远离了诗歌?
易安: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对我提到过。确实如此,我从长沙返回原来的单位后,一时无法静下心来写作,找不到当初的那种状态。当然,对诗歌界的一些炒作和话语霸权的不满也从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我的心态。我确实又一次冷落了诗歌写作。现在想来,我很怀念在长沙和诗友们在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
马枫:在《湖南六诗人集》中,我注意到你有一首比较独特的诗,就是《工厂职代会》。这种题材的诗歌我是第一次读到。
易安:这可能和很少有人去涉及这方面的题材写作有关。这首诗写于1997年初冬,那时我上班的工厂因为管理不善而呈现出一片萧条之色(几乎大部分的国有企业都是这样)。我每次从威严的办公楼和灰暗的厂房下经过,都感受到了一种从内心深处涌起的不满和苦涩。在一个独自深坐的雨夜这种情绪最终不可抑制,似乎是一口气就写下了这首充满怀疑和讽喻的60多行的长诗(相对于我的诗作而言)。
马枫:说到雨夜,我忽然想起了你诗作后面的日期,好像大多是“深夜”和“清晨”,这是否是你在创作习惯上的黄金时间?
易安:是的。我喜欢深夜的那种静谧,几乎听得见呼吸。我的许多话语这个时候就会汩汩涌出。有意思的是,因为这种习惯,我发现许多的雨和雪都是从深夜开始下起的。而别人要等到天亮以后,才明白这个世界在昨天夜里又发生了什么。这时我才发现,一个人对世界的触摸有多深!
马枫:这句话很精彩!
易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