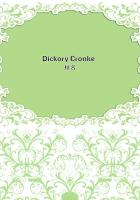走进报社后,我的心突然痛了一下。我马上想到,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因为我做了愧对自己的事。
不行,我不能原谅自己,我不能纵容自己的堕落。
现在回去,我可能什么也得不到。不合时宜。
走进办公室,我将资料交给了管丽芳。由她来写,刊登时附上我的名姓。她明白我的心情,没有推辞。这个方法是报社内不成文的‘规矩’,你不开心写这篇稿子,由别人替你执笔,下次他不开心了,你在帮他。这个方法不错,至少大大减少了写手被气死的人数。
下了前,管丽芳拿了稿子给我‘过目’,我看了几眼,相当的满意。
下班后,几人约我去聚餐。
我说,家中美女有旨,需准时回家。
他们催促我赶紧回家享温柔去吧。
远离报社后,我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探头问司机,知道胡楼镇吗?
司机说,去过一两次。
我又问,去过胡楼村吗?
司机说,到了胡楼镇,就能找到胡楼村。
我上车。
他开车。
如司机所说,到了胡楼镇,就找到了胡楼村。
我给钱。
他收钱。
我向前走。
他扭转车头,开车向后飞驰而去。
天色渐黑,家家户户亮着灯。冬天的晚上,很少有人走出房屋,在街上聊天。虽然白天他们被强行窝在屋里不许出来,但也没有出来透透气的意思。他们已经习惯被压制了。
我绕到村的后头,避免走大路,免得遇到我不想见到的人。附近住的都是老人。我决定选最边上的一家。
走到门外,院子里传来了狗的叫声。
“谁啊?”一个苍老的声音传了出来。
“是我!”我尽量小声的做出来回答。
“你是?”一个高大的老人走到了我的面前。说是院子,其实与正房的距离只有四五米。
“我是白天过来的那个记者。”我将声音压到了最低。
“原来真是你。”老人确定了我的身份。
“您认识我。”我很清楚白天没有见过他。
“您有事?”老人不愿回答,有些冷漠的说。
“我想找您聊聊天。”我说。
“您不是已经回L城了吗?”老人说。
“是回去了,可又回来了,回来就是想找个人聊聊天。”我说。
“聊什么?”老人不耐烦的说。
“聊今天我不知道的事。”我说。
“无可奉告。”老人说着扭头走进了房内。
我跟着走了进去。房内的陈旧布置跟这精美房子的外表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让我一下子燃起了咒骂那些做了坏事又将嘴巴擦的干干净净的东西们。
老人正在吃饭。一瓶劣质白酒,一盘辣椒拌咸菜,冷馍,稀汤。
这撕开了我的咒骂,让那些音符飘上了天际。
“您要不要一起吃。”老人准备继续吃饭。
“不用了。”我调理好情绪,让自己保持冷静。
“忘了,你们这些人大鱼大肉吃惯了,怎能看上这个。”老人说。
我默默接受了老人热讽。心里想到了上午的那桌丰盛的酒宴。
老人喝了一口酒,用筷子夹了两根咸菜,放进嘴里,咯嘣咯嘣咀嚼起来。
“我可以坐下吗?”我请求道。
“随便,不过我家的凳子可没有沙发舒服。”老人说。
我在一个低矮且四条腿长短不一的木凳上坐下,看着老人,低叹了一口气,说:“我了解官场,知道跟着他们是瞎转悠,得不到什么,就像一群驴在沙漠里找嫩草吃,找到累死饿死也找不到一棵嫩草。”
“你这话说的挺有意思。”老人一听我将自己跟领导们都比划成了驴,有些乐了。
“大爷,您祖祖辈辈都是生活在这个村子里的吗?”我说。
“农民?谁祖祖辈辈不是扎在一块土地上?”老人说着朝我面前丢了一个酒盅子。酒盅子在桌子上打了几个转,最后站立了。
看样子,我不得不接受他的邀请了。
老人要给我倒酒,被我给抢了过去。我自己给自己斟的满满的。
“大爷,您今年贵庚?”我喝了一口酒,问道。这酒真烈,辣喉咙辣的要命。
“六十有八。”老人左手比划了一个六,右手比划了一个八。
“看不出来,您都这岁数了。”我说。
“再活上几年,死也值了。”老人说。
“您何必如此悲观。”我说。
“我这辈子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想想人这一辈子都是在折磨中过来的,各种各样的折磨,别人折磨你,自己折磨自己,你折磨别人的过程也折磨了自己。总之没有消停的时候。”老人伤感的说。
“是啊。”我对老人的话深表认可,我时常不是在折磨自己啊。
“你为什么选择做记者?”老人突然好奇的问。
“做记者之前我靠写蝇头小说赚些生活费。最近没灵感了就一直闲着,父亲看不下去,通过关系让我进了报社。”我长话短说,来此不是炫耀家庭财富的。
老人摇着头长叹了一口气。
“做了这行,我体会到了很多的人生。”我马上做了纠正,表明我不是游手好闲吊儿郎当之徒。
“你走了又来,是个人的意思吧?”老人问。他已经看透了所谓的相护与做样子。
“是的,我憋得慌,就是想知道他们不让我知道的事。”我说。
“你知道了又能如何?”他深意的问。
“我如实写,稿子很有可能会被毙掉。”我说。
“可能性有多大?”老人问。
“通过,仅存理念上的希望。”我说。
“那我说了又有何用?”老人问。
“我很想听,不然憋得难受。”我说。
老人沉思了许久,说出了关于胡楼村规划的往事。胡楼村是镇里数一数二的富村子。人怕壮猪怕肥,试点村也就轮到了胡楼村。规划开始时,社员们住的都是瓦房。好就好在我们有个好支书。村支书是个既有钱上面又有人的好人。他一生令下,为倡导国家发布的关于缩减房屋用地增加农田的政策,全村规划。这个决议有一成村民响应,有八成村民激烈反对,剩下一成被直接剥夺了说话的权利。一成村民中大部分是靠运输开手工作坊养殖发家的富裕户,小部分是宅基地地势不好,挪挪好换‘风水’的人。
国家的法规就是圣旨,村支书就是钦差大臣,服的是良民大大有赏,不服者是扰乱社会秩序的不良分子,拳打脚踢那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直至你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后,再从新给你贴上良民的标签。这期间,数十名村民遭到了毒打,严重者骨折多处。
全民同意后,村支书开始了跑上跑下耗时一年筹集了六十万补助的壮举。补助到位后,轰轰烈烈的拆房盖楼的运动开始了。房子拆了,没地儿住了,村民们只得搬到亲戚家去。
一年半载后,崭新的村子闪亮眼前了。每栋楼房高五层,每套毛坯房子的造价应地势楼层而从十四万到十八万不等。旧房子的估价也不等,算下来没有一家不需交差额金。差额金从五万到九万之间。五万啊!九万啊!一个靠种地为生的农民谁能掏出这笔钱。有钱的先把好地势好楼层的买了,中等的被东凑西凑亲戚家借个遍的拿下了,剩下差的部分社员也望而生畏。
好支书就是好支书,他说通了银行,帮社员贷了部分款,又牵线让社员贷了黑市上的高利贷,这又让村子的空房少了一部分,让建筑公司临时不上门讨钱了。剩下的实在没钱的,只得在亲戚家常住或一家老小道外地打工去了。到现在,村里还是四十多间房子空着。
这一系列折腾下来,胡楼村得社员都穷了。耕地没有增加,反而搭进去十余亩良田。
那六十万补助,算下来,一分没有补助到社员手里,全进了领导们的钱包。就是补给社员,这区区六十万才够补六套中等房啊。
村书记在领导面前扬了名,在社员心里却臭到了家。其实这种事,市里的领导都知道。知道了又能如何,总不能抽自己耳光子吧。上级领导安排你们这些小兵来,也只是找给他们脸上贴贴金说说好话,哄哄他们的领导。
好一个抽自己耳光子。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
老人没有出门送我,因为我太渺小了。
在外面,风儿一吹,我切实的感觉自己太渺小了。
这个时间段,很难打到车。
我在公路上步行穿梭着,以这个速度,走回L城,恐怕要见到第二天的太阳了。
我的心没有空间去计数逝去的时间,只在一味的穿梭众多房屋的倒下,众多房屋的崛起,众多人脸上的痛苦,众多压在人民背上的钞票。
有一天,旧的房屋倒下了,没有新的再崛起,众多人怀着痛苦死去,人民身上的钞票变成了五台山压住了‘猴子“,而世上却再无唐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