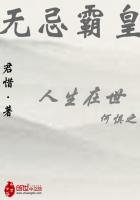朱胜文虽然可怜他的身世,也对那个叫徐一杰的坏人深表愤恨,但却不知道怎么安慰刘占山,只得任他宣泄胸中忿懑不平之气。心中想到两月前在日和茶行里曾清平说过的话,就开解道:“其实,听我们茶行的总办说,也有个车夫的儿子和你差不多惨的,一般的家道中落,一般的扔给奶奶不管。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也别太伤心了,以后找机会报仇就好!”
刘占山奇道:“车夫?”
朱胜文点头应道:“嗯!”
刘占山更奇道:“叫什么名字?”
朱胜文无辜地答道:“叫刘三。”
刘占山一听又哭得以泪洗面,伤心道:“他就是我那个不争气的老爹啊!我就是你说的那个车夫之子啊!”
朱胜文满脸惊讶,问道:“你们家以前是开牙行的?”
刘占山一抹泪水,点头应道:“是的。不过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你说报仇?哼,谈何容易!他每次出门都是武师护卫前呼后拥,我一个毛小孩,又不会少林功夫,不被武师打死就算幸运了,怎么报仇?初时那人还假惺惺地时常送点米粮肉油到我奶奶家来讨好我,倒也相安无事。后来我大些懂事了,了解事情原委之后,气愤不过,不时扔石头砸破他家新装的昂贵彩色玻璃,气得他吹胡子瞪眼心痛不已,于是再也没有人来送肉粮,但还没有为难我。可我始终愤愤不平,不是偷他家养的老母鸡,就是卷他家挂在墙边的腊肉腊鱼,但哪怕是我乘他刚出门未提防用石头砸伤他的腿,他都是息事宁人了事。直到去年的秋天,得寸进尺的我,用弹弓将他最疼爱的小儿子头上射出个大包,震怒的他终于大发雷霆,派武师四处抓我,扬言要将我送官法办。不得已,我再也不敢在新店待着,只得跑到羊楼峒附近四处游荡,隔三岔五再乘着夜色偷偷溜回新店看看奶奶。如今,漂泊了一年,仇也不得报,命也不易保,这样的生活我都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我真没用!”说完又惭愧又恼怒地将耷拉的头埋进双手中长吁短叹起来。
朱胜文也深深地叹了口气,以前他一直觉得自己家徒四壁,自惭形秽,不时埋怨一没肉吃,二没新衣穿,如今,比之刘占山,自己竟是何等幸福!有完整的家,温暖的床,还算正常的生活,还算快乐的童年,不必餐风露宿,忧心追捕,苦思报仇,思而不得!
正在朱胜文感叹之时,刘占山不知道想到什么事,忽然从沮丧中回神过来,蜕变成另一个人,歇斯底里地叫道:“不如我们来结义!来!”说完找了三支短棍给朱胜文当香,要朱胜文举着。朱胜文还没会过意来,就被刘占山领到土坡之下跪着,自己则一屁股坐到土坡上。这一下朱胜文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奇道:“呃,不是要结义吗?好象说书先生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焚香为盟时,三人可是并排一起对天盟誓不求什么什么生但求什么什么死的,现在你怎么在上,而我在下?”
刘占山瞪他道:“谁说要和你桃园结义?我说的结义就是你拜我做大哥,仅此而已!而且,我救过你的命,现在又是你大哥,所以你要拿钱给我花,拿好吃的给我吃,不然老天爷就要惩罚你!”
朱胜文满脑一团乱麻,如云里雾里,不知所处。先不说拿不拿钱给你花,给不给好吃的给你吃,这还没拜不是吗?而且,突然这么伸手要钱,这还是那个辞谢总办银票的刘占山吗?按理,他于己有救命之恩,无论给多少钱给多少吃的都无所谓都应该,可他以结义以神佛来约束自己,多少有些蛮横强迫之嫌。朱胜文虽然心中别扭纠结,但想想如果不是他拼死一救,自己现在只怕已然身在阎王处遭受死后清算地狱酷刑。于是端正态度,敛容举“香”,说道:“大哥在上,请受小弟三拜!”说完认认真真地向“大哥”磕了三个响头。
刘占山志得意满,伸手扶起朱胜文,说道:“嗯!兄弟请起!”朱胜文将香棍扔在地上,往怀袋中一摸,触手之处是那张十两银票。可能是刚才心中那一点点不满之心作祟,又或是他那黄陂人固有的小气作风驱使,犹豫一瞬间,他的手终于划过那张银票,伸向更下面的几颗散碎银豆子,拿出来献上道:“这是我这月的工食银,寄了点给我妈,就只剩下这三两钱散银子,你先用着,我下月再给你拿点。”
这三两钱银子虽说按当时物价也只值个四百文钱,对大户人家来说不值一提,但对居无定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刘占山来讲,都够买两百多个鲜肉包子,可算有雪中送炭之功效。刘占山拿了银子收入束带中,非常感激地拍了拍朱胜文的肩膀,说道:“谢谢了!兄弟!我先走了,再见!”说完,抄起地上的米,沿着七里冲往新店方向而去。
朱胜文望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关切地喊道:“你有地方住吗?要不要去我们茶行的茶园里和游老爹同住?”
刘占山回头摆了摆手,潇洒地远去。午后的阳光明亮地投在他的背上,一闪一闪,如星光反射入朱胜文眼中。真希望,这阳光能够时刻照亮他前行道路,照暖他的心内的阴霾与黑暗,照耀他生存和抗争之意义与目标之所在!
午饭后一大部分人稍息片刻即赶去戏台看戏,另一少部分人干脆躺在床上睡大觉,朱胜文正是后者。一则,追赶刘占山消耗了他太多体力;二则,假使是先生说书,可能他去观摩的劲头会更足。
这昏天黑地的,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猛然鼻尖嗅到一股异香。紧接着,嘴中轻轻塞进一物,甜软可口,奶香花生香四溢。他立即坐了起来,眼睛还未睁开,倒听见女孩子的咯咯笑声。睡眼惺忪中,嘟咙道:“黄逦,你没去看戏么?”却不见有人回答。他倍感怪异,心中暗想:难道见鬼了不成!等他拼命把眼睛揉醒,仔细看来,眼前一张圆嘟嘟白净净的粉脸,噘着嘴巴瞪着自己,手上还拿着一块已然剥开一半,前段还带着湿润口水的花生牛轧糖。
朱胜文大惊,知道讲错话了,立刻摆手解释道:“对……对不起,师傅!我……没听出来你的声音,以为是黄逦呢!”原来来人正是马蔓丽。
马蔓丽醋劲大发,说道:“人家本来觉得你今天早上做得很棒很棒,大伙都认为你虽败犹荣,很替师傅我挣面子。为此中午特意去给你买的牛轧糖,没想到你却这样不留情面!”
朱胜文这会只想找个地洞自己钻进去,羞愧不已,只得再次道歉道:“对不起了,师傅!”
马蔓丽见他也确属无心,便不再纠缠,假装生气道:“好!我接受道歉!不过,要罚你!”
朱胜文见她还要罚,苦道:“啊!罚?罚什么?”
马蔓丽仍然板着脸,敛容道:“罚!罚你把这块牛轧糖给我吃下去!”说完破怒为笑。
朱胜文只要她不再生气就好,而且这要求还挺不赖,于是从她手上拿过那块口水牛轧糖放入口中。细细品来,奶味适中,花生香浓可口,软硬适度,既不粘牙,亦有嚼劲,心下越吃越开心。马蔓丽见他面露满足之情,心中也暗自愉悦,可是却不能太过表露,不然既辱没了“师傅”美名,以后也不好意思在他面前再端起师尊架子。
朱胜文一边吃着,一边问道:“对了,你看,他们都去看戏了,你怎么不去,跑这儿来了?”
马蔓丽歪着头想想,答道:“嗯……一来给你送糖做奖品,总办不给,我给。二来嘛,那戏说的话唱的词我都是听不全懂,怎么,那么象你们黄陂话?”
朱胜文解释道:“你们随州那边可能还没有传过去,蒲圻也是近些年才开始流行的,大戏唱得机会不多。在我们黄陂还有孝感那边,那可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神仙菩萨寿诞都要唱的,大大小小戏台无处不搭,无人不看。因为发源于黄陂孝感,又采用黄陂孝感地方方言,因此这戏被称为黄孝花鼓,所以你听不全懂也挺正常。不过,我倒觉得咱们黄陂话又没有怪腔怪调,也很容易听懂啊!有些从JX、HN来的茶工还以为我说的是京片子呢!”
马蔓丽笑道:“就是说嘛,我还真的说对了,原来黄孝就是指黄陂孝感。不过,谁不说咱家乡好!谁还嫌自己家乡话难听?”
朱胜文想了想,说道:“不过我听茶工他们说话,HB这一块,英山话好象相对不好懂,只看他张嘴,只听见嗡声,不明白他讲什么。”
马蔓丽点头说道:“那是。不过,你要出了HB往南走,往北走,往东走,往西走,走很远很远,指不定还有说话更让你难懂得多的地方,谁叫咱们大清地大物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