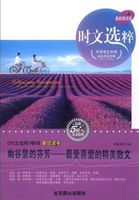第三十七章责难X数落X茶室
刘三对一胖一瘦两个车夫一使眼色,两人会意地走到堵塞道路的自己的马车旁,纵身上车,将马车开到官道前的空地上的大树下。刘三则来到自己的车前,东摸摸,西敲敲,趁大家不注意时,将故意错位出去的车轴归到原处,方才跃上马车,轻轻一拉缰绳,“驾”声一起,马儿缓缓起动,也朝马四二车之处得得而去。围观的人们见歉也道了,钱也赔了,纠纷已解,遂一哄而散,各回各屋,各办各事。曾清平从旁边唤来个茶行的伙计,耳语一番,伙计连连点头离去。朱胜文则站在曾清平旁边,好奇地看着面前的这几个洋人。
八字胡子对曾清平再次表示感谢,并将手掌一指假发洋人,向曾清平介绍说道:“这位先生是大英吉利帝国尊敬的威廉·克利弗·弗朗西斯·罗便臣爵士(SirWilliamCleaverFrancisRobinson),他受加拿大政府之委托考察了香港及贵国广州、SH、汉口和羊楼峒等地风土人情及所出特产,以图开展新商品贸易及开辟新航线,现在即将启程远涉重洋到加拿大就任大法官。”并靠近曾清平的耳朵,轻声说道:“告诉你,其兄夏乔士·乔治·罗伯特·罗便臣爵士(SirHerculesGeorgeRobertRobinson,KCMG、LordRosmead)便是香港第五任总督,治理了香港数年时间,颇有政迹。”随后又指着曾清平,用英语向罗便臣爵士引荐并介绍一番。
虽然自《穿鼻草约》及其后的《南京条约》大清割让香港和《BJ条约》割让九龙之后已历二十年之久,而且香港、九龙对自身而言只不过是个远在天边、不曾游过,曾经的大清地名如今的英国地名而已,但在曾清平听来,仍犹如针刺一般难受和不快,勉强才挤出一丝微笑。罗便臣爵士则非常礼貌地微微一笑,一倾上身,对曾清平说道:“Thankyouverymuch,sir.”金发洋人却心有不满,抱怨道:“明明是你们清国人的错,堵了路不让我们走,却还要我们道歉掏钱,难道他们是喝醉酒的疯子只会蛮横不知讲理?”
八字胡子一耸肩,笑道:“亨利,如果你没有骂人,或者假如他们听不懂英语的话,恐怕他们想赖也赖不到你们身上来,哈哈!”曾清平一竖大拇指,也哈哈大笑。罗便臣爵士听不懂大清官话,一脸木然,八字胡子便用英语转述给他听,他连声点头称是。
金发洋人亨利面有愧色,涨红了脸高声争辩道:“清国人常常莫名其妙自私自利,只顾自己舒服活着,哪管别人苦痛病死。象今天这样找一个小小理由就能敲诈勒索,他们可是从官到民,轻车熟路,运用自如得很!”
曾清平本来就心中暗生疙瘩,耳中更听得亨利攻击国人,心中更加不满,眉头一皱,不客气地问道:“此话怎讲?”
亨利也心中不快,平白无故损失了十几块钱,还耽误了不少时间,索性讲个清楚明白,不吐不快,意气风发毫不结巴地说道:“说民吧,今天发生这个事就莫再提,单就一件小事可见你们百姓内心的自私。你们清国人生病喜欢用小罐煎熬各种气味难闻的草药,疗效如何尚且不知,就说过滤出来的草药渣子,既不倒入垃圾堆或公厕,也不埋进农田作肥料,而是撒在马路上甚至邻居家门口,既影响道路美观卫生,又让踩到的行人讨厌。请问可有此事?”说完在地上捡起一根木棍,提起右脚,在皮鞋鞋底一番拨弄,刮下几片中药残渣来。围观群众听了,纷纷下意识地抬脚来看,自有不少人未能幸免。
朱胜文从小身体不好,感冒发烧那是经常的事,几乎算得上半个药罐子,对中药煎煮熬制一事并不陌生。每次母亲熬好了药,都要让朱胜文乘着天黑,或是自己众目睽睽之下,将药渣倒在大马路上。朱胜文多次询问母亲此举原因,母亲要么支支吾吾,要么讳莫如深。
曾清平一楞,有些难为情地点了点头,回答道:“确有此事。”
亨利见曾清平承认,一脸得意,继续追问道:“那,原因何在?”
曾清平一瞥八字胡子,见他也一脸好奇地看着自己,于是只得略加思索,说道:“原因嘛,说出来能让你们见笑,让我们羞耻。实实在在地讲,说得不好听点,就是‘转嫁于人’:百姓相信行人踩到了药渣,就能把病气和病根带走,而自己则药到病除。但是也有另一种说法,把药渣撒在路上是为了方便郎中,也就是贵国所说的doctor,检验药方是否开错,药材是否真材实料。不过不管什么原因,这毕竟是鄙国百姓的一种陋习,既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又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只会给行人带来诸多不便,更增加清扫人员的工作量,确实应该改善。”亨利得意地一耸肩膀,一摊双手,说道:“看吧!你们清国人确实没有什么公德心和道德底线!你们行事,一不讲规则,二爱破坏规则!No,No,No!不好!不好!”还轻蔑地伸出右手食指左右晃动,恶心得曾清平真想上去狠狠给他一耳刮子,让这恩将仇报的货满地找牙去。
亨利继续说道:“再说官吧。其实也不用我说,你们自己和当官的打交道,自己也最清楚。大多是些表里不合言行不一贪婪虚伪心狠手辣的家伙,只不过靠拍皇帝和上司马屁外加行贿送礼坐上高位而已,平日里没少干巧立名目敲榨勒索摊派捐厘鱼肉百姓的事。你们清国人真正交到国库的税金与你们交的税费摊派捐厘相比可当真少得不得了,Why?大多被你们的官老爷们给贪到自己口袋里了!别说你们清国小民,就连我们大英帝国商人在鸦片交易合法以前都没少被官府军营里的官爷军爷们敲竹板。”亨利这一段话当真是搜肠刮肚,把自己平生所学清国词汇一一使出,还不乏俗话成语。
听八字胡子传译完亨利的话,罗便臣爵士连连点头称是,但转念一想,似乎觉得亨利的话有些不留情面,颇觉愧疚,好歹人家刚刚解了自己的围,只不过碍于绅士风度,并没有呵斥亨利。八字胡子和曾清平相视一笑,看曾清平显得无言以对无可奈何,对亨利笑道:“这个不对,这个不叫敲竹板。呃,曾先生,叫什么来着?”
曾清平说道:“叫敲竹杠。”
亨利连连点头道:“对,对,对,是叫敲竹杠!你们两位绅士说说看,之前那三个车夫的行为叫不叫敲竹杠?”八字胡子听着亨利又把话题引向那些车夫,又眼看着曾清平脸色越来越难看,当下只得用英语和罗便臣爵士交流一番,示意他适时阻止亨利没完没了地继续纠缠,早些上车赶路。罗便臣爵士非常礼貌地向八字胡子致意示谢,见亨利还要继续责难,便叫开他,和他轻声说了一通。亨利从口袋中掏出怀表看了看,和车夫说了声,车夫便跳上车,赶好车,拉好马,等待两人上车。
罗便臣爵士感恩地伸出双手,同八字胡子和曾清平一一握手话别,对二人的努力再次弯腰致谢,并掏出一张洋文名刺递到曾清平手上,随后和亨利上了马车绝尘而去。曾清平把名刺收好,看到傻站一旁看热闹的朱胜文,便喊他过来,指着他向八字胡子介绍道:“这是我们同一个村子的小老乡,叫朱胜文,刚做茶行学徒不久。”见八字胡子笑容灿烂地伸右手过来停在眼前,朱胜文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曾清平笑道:“这个叫做握手,是西洋人见面礼节,就好比我们的鞠躬请安礼。回礼就是你也伸右手握住他的手,上下摇上几下即可,你试试看。”
曾清平指着八字胡子向朱胜文介绍道:“这位是隔壁‘日和’茶行的大班,也就是相当于总办。姓名嘛……反正姓你应该熟得很,让他自我介绍吧。”朱胜文高高地伸出单薄的右手,晃晃悠悠地伸进八字胡子的右手里。八字胡子敛容道:“我叫伊东佑和,大RB帝国九州岛南部萨摩藩鹿儿岛城之下的清水马场町人士,哦,也就是如今的鹿儿岛县鹿儿岛市。”两人握紧摇了三下,再松开双手,礼毕。
朱胜文瞪大眼睛惊道:“伊东?”指了指伊东佑和,又指了指自己的腰间,继而又指了宿舍方向,看着微笑的曾清平。伊东佑和奇道:“你认识我?”朱胜文连连摇头,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曾清平哈哈大笑,对伊东佑和说道:“他有一支箫,不巧正好取名为‘伊东’,正应你的姓氏。”伊东佑和展颜开怀大笑,拍了拍朱胜文的肩膀说道:“哦,哦,那我们还真是有缘分。来,来,来,一块到我办公室尝尝我们RB抹茶的滋味!”朱胜文有些尴尬地瞅了瞅眼前这位只比自己高出一头,却比曾清平还矮了一头,一脸认真的RB男人,又瞅了瞅曾清平,未置可否。曾清平微弯腰一摊手,笑道:“那恭敬不如从命,请!”
伊东祐和在清国待了十余年,深谙清国礼仪,不但并不挪步,而且更加恭敬地鞠躬平手,说道:“十分感谢今天阁下的出手,曾先生请!”曾清平见礼数已足,再不推辞,一拍朱胜文,示意他跟上。正待进去时,之前和曾清平耳语的伙计快步走了过来,又与曾清平一通耳语,曾清平连连点头。说完后曾清平一摆手,伙计快步返回长和川。随后曾、朱二人一前一后地走进“日和”茶行:前面的人气宇轩昂,步履轻快,后面的人则左顾右盼,缩头缩脑。伊东祐和殿后而随,一进门便招呼手下准备茶点,随后在门口鞋袜处脱下皮鞋进来,跪坐门口欢迎。
朱胜文进得门来,四处张望,发现RB茶行陈设的格局同清式茶行大同小异,但摆放得更加精细,饰物更加考究,一应乌亮黑漆镏金片饰的茶架、茶具、茶盒等物,更显富丽堂皇雍荣华贵。墙上还贴着夸张硕大的盘着高发髻赤身露体只有胯下白布条遮掩,张开着四肢欲搏的巨肥男人,或是冰洁雪山(其实就是富士山)之侧,云海般的粉红花树(其实就是樱花)中,油纸伞下,那高顶髻宽衣袖着木屐婀娜多姿顾盼生辉之盛装丽人的巨幅纸画(浮世绘),无论是人物神情举止还是屋中陈设皆维妙维肖。
进入内室,原来地上并不是象大清,富人家以方砖、条石铺地,穷人家就只能是原始土面,而是除了门口脱鞋放鞋的一小块地方外,其他的地方都要高出一尺左右,上面满铺了一层草席。中央位置是一张黑漆小案,案上一尘不染井井有条摆放着各种精雕细琢精美无比的茶具,有些在茶行的那尊黄花梨木根雕茶台上见过,有些则是平生仅见。案下四周放着数个象佛寺里供香客们礼佛用的灰色软布蒲团,案侧摆放着一只香炉,和一只花瓶,瓶中插着数支盛开的鲜花。还有一只精妙绝伦的黄铜小风炉,炉中木炭火刚起,炉旁搁着一只大号的紫砂陶釜,吸引着曾清平惊奇的目光。对朱胜文来说,只不过觉得好看而已,但曾清平是见过世面之人,自是知道这只小炭炉和炉上的紫砂壶不但大有来历,且价值不菲。
朱胜文跟着曾清平脱去布鞋走了上去,再往里看,只见一副红黄为主花里胡哨奇形怪状的盔甲挂在正中偏右的位置,其上是一把稍有弧度把手较长似剑似刀的带鞘武器架在黑漆镏金的木拱上,再上又是一把形制相同只是稍短的“剑”,都与中土物件形状不同,令他好生奇怪。正中更怪,挂了一副不大但装裱得非常精美的蓝绢,上面用金线绣着一个三寸见方样子奇怪的图形:上面是一个弦在下的三角形,象个茅草屋顶;屋顶之下,左右各一个上下窄左右宽的长方形,象是房柱;合起来看就象个屋子,而屋子里面则是朵看不出种属的四瓣花。这图也太奇怪太难看了,还挂起那么高,一点都不象大清的茶行,几乎家家都会挂上一副神龛,或祭祀关帝爷,或祭祀观音菩萨,或祭祀真武大帝等各路神仙,逢其生辰或吉时,焚香献祭,烟雾缭绕,虔诚而又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