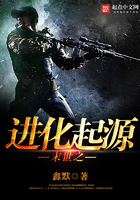来班级报道后我才知道,原来这边的学校初中是四年制,小学是五年,来到这边读初二等于是蹲了一年级,同学普遍逗比我小一岁...我的班级在年级组里算是还不错的班级,我坐在后排的座位,同桌是个胖子,两个人共用的课桌,胖子自己要占三分之二,这也就算了,还他娘的有狐臭,呛眼睛的那种,每天我都被熏的头晕目眩。
来到了这边,我想要开始新的生活,想要重生,上课的时候很是很认真的在学,可是我的底子差,成绩也是班里的吊车尾,老师先是找了我谈了谈然后安排了个女同学帮我补课,那个女生的眼睛很好看,虽然总是淡淡的看人,但眼睛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明澈。身上总是有一股淡淡的洗发水的香味。学校每天早上做广播体操的时候都是常丹在升旗台上领操。
除了在学校老师安排同学帮我补课外,母亲也帮我报了补习班,每天晚上都要去补课,我们补习班教室的旁边就是画室,每天晚上,上补习班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个同班的同学在隔壁画室,戴着眼镜,长得特别中性又特别白的一个人,我一直以为他是女生,后来有一次在学校上厕所的时候在厕所里碰见了他。
我笑着问他“原来你是男的啊?”我问
“对啊,不然呢?”他笑着答
“我还以为你是女的呢!嘿嘿”
从那天起每天去晚上放学我们两个都是一起走,张郝嘉每天晚上放学会去练琴,和我们不在一个地方。我们往十字路口的左边走,她走右边。有时我还会去江东他们画室里看他们画画,在学校也会经常和他一起画画,美术课的时候我们俩老是要坐在一桌,还经常和同班的同学显摆俩人我们画的画。
除了补课外,没事的时候我会在操场上踢球,周末会去公园练武,我们班的学生都是一些老实的学生,没有什么人打架。
全年级就七班的学生最刺头,刺头的学生自然身体素质也不差,学校里每个体育社里都有七班的身影。那天在操场上踢球,七班有一个和我前后没差多少天转过的学生与他们班的头头球场上打起来,那个头头很高比我们都要高出半头,我本以为这货肯定会被打的很惨,可另我没想到的是竟然是那个胖子被打,刚转学过来的那人一拳一拳的招呼在了胖子的鼻子,下巴上,胖子当场就被打蒙了,麻杆的手上全是胖子的血。最后被路过操场的老师拉开了...从那天后我认识了这个同乡的转校生,叫张松,老家离我们那里不太远。在漠河。
来到威海有了一段时间,和赵叔也混熟了,这人的经历丰富,而且情商很高。
听赵叔说,他们家哥两个,他排行老大,本来学习成绩很好,可上初中的时候他老是被欺负,后来就学坏了,去欺负别人,当时年轻,很喜欢那种感觉,特别是从被欺负转变成欺负别人的那种反差。
赵叔说他们那时念到初三快毕业的时候,已经是学校没人能管的地步了,学校在开大会,教导处的一位老师在升旗台上演讲,几个不读书整天瞎混的同学事先商量好跑到升旗台上拽住他就是一顿打,当时下面跟炸开了锅一样,学校的男老师们上前拉架,几个人打完了,就从学校的围墙翻墙跑了。毕业证也不要了。那时候什么都不为,就是感觉这么做很解气很威风。现在一看太傻了。
后来几个人就一直在社会上游荡,赵叔被家里人送到了DXAL当兵,打靶的时候新兵们嫌打枪后坐力震的难受,每回打靶都把子弹埋在了靶场下面的土堆里。赵叔说当兵那年赶上了发洪水,DXAL着大火,好多的天灾人祸。赵叔说有好几个战友在那两年死了。赵叔说当年当兵的时候,腿都能抬到自己脑袋上。三五个人根本弄不了我。其实看着赵叔的模样,我真的很怀疑他是在吹牛。。
赵叔退伍后回到威海就和以前的朋友一起混社会,刚开始的时候在洗浴中心里看场,后来帮人收账,收保护费,到最后起承包工程,越做越大。
赵叔说年轻的时候我们去收账,十几个人就往他家商铺一座,他去哪我们去哪,他吃什么我们吃什么,也不打人,,每天就是不停的烦你,你也不敢动手。你要动手打我们的话,我们就有理由惹事了。报警的话也是欠债还钱。这种狗皮膏药的做法看着不怎么样,效果却是很好。
赵叔说我们承包工程的时候在威海都是数得上号的人了,一提我们几个,没有不认识的,那时候房子才七八万,我每个月就能挣两三万,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才三四百块钱....我问赵叔那后来呢?赵叔告诉我后来有天晚上出去喝酒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个仇人,就和手下兄弟上去打,那天都喝多了,有个人上去把那人的手脚筋都挑断了,在外面躲了一个星期,后来被抓住,判了十年,十年,我这秃顶就是在里面愁出来的,人生能有几个十年?现在在威海说起我赵老三,有谁会认识?有谁会买账?赵叔问我。我没说话。
赵叔的弟弟和赵叔初中的时候在一个学校念书,赵叔学坏了,弟弟却很用功的读书,有了个混混哥哥,弟弟也不用担心在学校受欺负了,安心学习考上了重点高中,大学又考上了BJ大学,毕业后又留在了BJ当了记着,每回回威海的时候,市长都要约他一起吃饭。说起弟弟,赵叔脸上掩饰不住的骄傲。赵叔出狱后,也是他弟弟帮他在这市政府附近找的地方开的超市,刚出狱一年不到,认识的妈妈,俩人又谈了一年,最后俩人结了婚。
那天赵叔领我去理发店理发,一个很老的理发店,理发师是一个老头,给我剪了一个方形的头,整个就一方形,那根本就不是平头了,回到家照着镜子怎么看怎么别扭,就拿着剪子自己剪了下,结果剪的更像是狗啃的一样,去理发店里干脆刮光了。去了学校简直心态爆炸,升旗的时候也是戴着帽子,老师说让我摘下来的时候,起初我还在坚持,后来也不得不摘下来了,下午的时候年级里三个班一起去音乐室里上课,那个音乐室就像电影院里的布置一样,老师在扇形的教室下面讲课,梯形的教室有三排座位,两排靠在两边的墙上,中间一排,左右两个过道把三排座位隔开,一个班一排,我们班坐在中间的一排,上音乐课的时候我坐在后排,在那里趴着,听见隔壁班的几个学生在他们那边议论我——
“看到那个光头了吗?好像刚转来不久”一个人说道。
“跟他妈个****是的,前两天还戴个帽子,长着一个欠揍的脑袋。”另一个不削的声音。
“哈哈他好像是劳改犯。”
“好想打他一顿,看见这种人就不爽。”
“¥%&*。”
我一直趴在桌子上在听着,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反击的事,如果这次不反击,以后他们会更加的变本加利的欺负到我头上,就像小学的时候在东北一样,人都有恐惧心里,而且这一次反击必须把对方震慑住,要有视觉冲击的效果。
亚索一直在等下课铃声想起的那一刻,等了好久,下课铃声终于响了,亚索把音乐书交给了旁边的同学,一步步的走到隔壁班骂自己的那些人的那排,低头看着坐在边上的人说“听说你找我有事?”那人转头看向我,还没等他回答,我运住全身的劲用右手猛的把他的头按在了前方的桌子上,“嘭”的一声,紧接着左手跟上,两只手一起用力的把他的头砸向桌子,就像在砸一个西瓜。少年人打架都是那么率性而为,不计后果。
那人瞬间被砸的七荤八素,第三下砸下去的时候,木板样的桌子已经裂开了,然后我又朝着他的太阳穴打了一拳,看着他当时就要躺在地上,他后面的一个高个子扶住了他,把他放在了椅子上,向我冲来,就那么径直的用身子撞我,我被撞了一个跟头,起身站到桌子上,助跑跳起一个飞踹把他踹倒,我用膝盖顶着他,又朝着他鼻子打了两拳,起身应付冲过来的第三个人,那个人和我差不多高,我冲过去左手掐住他的喉骨,人在喉骨被掐到了时候,浑身的力气都提不起来,我右手又是两拳打在了他的眼眶上,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了一瞬间,三个班级将近二百人都在看着这边,他们班的其余的人只是看着我却不敢动手了,站在那里愣着,老是也跑了过来大喊道“亚索,你给我住手。”
那个音乐老师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人,长得很漂亮,人也特别温柔,我从小有个毛病,就是特别听这类女生的话,我还美其名曰——骑士精神,就像海贼王里的香吉士一样,我松开了那人,老师皱眉看着我“亚索你下手怎么这么黑啊?”“是他们先挑衅我的,他们在上课的时候骂我,要不是看老师在讲课我当时就起身打他们了。”
三个人,一个昏了,一个鼻子在流血,一个眼眶打青了,他们班的老师把我和他们班挨打的学生叫出来,我说是他们先骂我的,而我事先根本不认识他们,班主任也很护着我,同学也站出来帮我作证,他们理亏在先这事最后不了了之,体育老师路过时说三个人打不过人一个?是不是五班的学生,真完蛋。
班主任事后单独把我叫到了办公室,说平时看着你挺老实的,怎么打起架来这么狠?我没说话,班主任告诉我以后不许打架,有什么事可以和老师说,老师替你出头。来到威海后,老师对我很是照顾,我要是不听老师的话自己也感觉有点说不过去。就答应了老师。
那件事过后,同年级的同学基本上都认识了我,高年级也有很多人听说过,二年三班的亚索一挑三,把三个人都打了,自己一点事没有。我突然发现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渐渐好了,在学校,在上学的路上看见我,会和我打招呼了。晚上在操场踢球的时候,还会有同学在球场边上看我踢球。有时候还能看见常丹,刚接触足球没多久的我虽然球技差了点,但是耐力惊人,也许是和每天坚持的跑步有关,在球场上来回飞奔,十分扎眼。每回看见常丹在球场边上的时候,我都像是浑身打了鸡血似得玩命的跑,我带着球一直老是在常丹那边晃悠,张松在旁边喊:“传球!传球!你他吗在那晃悠个几把毛呢?”我根本不理他,张松大怒,冲过来一个扫堂腿。我摔了个狗啃屎,大怒的跳起来想打人,后来起身看见常丹站在那对着我笑,突然间的就什么气都消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