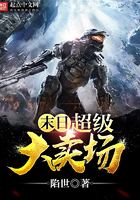“话说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明天还要上班。”
桌面上摆满了两打的空啤酒瓶,咣当咣当的在面上滚着。马皇天依然喊着不够,摇晃着脑袋又叫着一打啤酒。
我已经记不得我到底喝了多少,是七瓶还是八瓶。原本还担忧着明天上班该怎么办。但酒精逐渐的上脑,混乱了所有的时间观,完全不知道现在是多少点,明天是什么时候。
“明天星期五……”周麟打着酒嗝,身子晃个不停,最后栽在沈安驿的肩膀上,还不停的用手胡乱指着天空,傻笑咧咧的说道:“管他呢,反正那些关系户,基本上是九点半到十点半才班的……不管我去的多晚,我都是最早的……最早的一个。反正局长也去了其他地方考察,明天不在……”
“你那随便,我们明天还得起早呢。”我摆摆手,真心喝不下了。脑袋时而沉时而重时而轻,晕晕乎乎的,可是肚子又是一片翻江倒海,一股股酒劲直冲喉咙,如果不是一直顶着酒劲,一定吐个精光。
“明天早上我得和一个同事开大门,就不喝了……”沈安驿低着头,面色潮红,时不时的打着嗝儿。
马皇天退了最后一打的酒,带着不屑的眼神骂咧咧的说道:“你们一个个的……怂样。我都有数着,安驿最少,才四瓶……你们两个不过是六瓶,也别笑得太早……”
“六瓶……我这起码是……”我恼火劲头上来,一瓶瓶的数给马皇天看,“五瓶,六瓶……咦,奇怪,我第七瓶在哪里?”我晃了晃脑袋,眼睛看哪都是重影,看到有一瓶貌似是我的,就抓了过来,“我的第七瓶在……在这里呵呵。”
沈安驿却一言道破,淡淡的说道:“那是我刚喝过的。”
“就是就是,你什么时候喝过第七瓶。”马皇天洋洋得意的笑道。
“我也不记得了,管他呢……”我掏了钱,“今天晚上太感谢你们,这一顿——说什么都是我来请你们。”
付完了钱,我们摇晃的沿着珠江江滨,模模糊糊东倒西歪,犹如走在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还好江滨有栏杆,不然真会摔进珠江。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些什么?”不知谁起了头,唱了几句的周华健的《朋友》,我们几人也跟着唱了起来,“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终有梦终有你在心中。”
走路都走不稳,我们偏偏肩并着肩,又笑又闹着唱着这首歌的主旋律部分,“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滨江道上早已经没了人,空荡荡的大道就我们几个疯子,疯疯癫癫摇摇晃晃。如果有人,肯定躲都来不及。
“实在走不动……头好晕,晕得要死……”周麟叫喊着,踉踉跄跄的走了几步,就身子一歪,跌坐在地上,靠着栏杆。
我们其他人依着铁栏杆,吹着晚风,望着对江的广州塔,吵闹终于稍微歇息。
“我跟你们说……我特别羡慕你们,这真是实话啊。”马皇天笑呵呵的转过身,背后靠着栏杆,仿佛转了一个腔调,笑声之中夹杂了其他不可言状的味道。
“我们有什么可羡慕的……”周麟坐在地上,擂起拳头打了一顿旁边的马皇天,“你有百万还是千万富翁的老爸,在广州还拥有——多少套来着?然后还没数有多少公司和分公司呢。”
马皇天摇摇晃晃的蹲下身子,试了几次才揪住周麟的衣领,一把拉起来,先是重重的呸了一口,“你知道个屁!我爸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混蛋,我妈死了,我爸过不了几年就娶了一个。但没到两年就离婚,离婚不久我爸又和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人结婚。结果前段时间又离婚。我跟我爸基本形同陌路,他还声明遗产宁愿烧光都不会给我。这样的生活给你,你还要不要?”
马皇天松开了手,转身靠着栏杆,低头看着江水。
酒劲稍微降了些许,却换来了沉沉的惆怅。往日受到的委屈、不公混杂着酒精,酿出了种种苦涩的回忆,造出了种种无以言状的幻想。受到马皇天的影响,我那沉沉的脑子再次高速造势。
来到广州第一天,我感到万分的新鲜。快速便捷的地铁、摩登时尚的建筑、摩肩接踵的街道,这些是家乡没有办法比拟的。来自小地方的我就如同进了大观园,被繁华迷昏了眼睛。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做着地铁上班,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劲儿。
新鲜感过了,我也才渐渐发觉,我们这些来自外乡的人很难融入到当地生活。不仅仅是语言不通遭到当地人有色眼镜的鄙夷,还有更多的是在当地没有房没有车,居无定所搬家频繁,归属感是什么至今依然在个位数徘徊。
“要比惨,应该都没有我厉害。”周麟凝望着远处的广州塔。广州塔那绚丽的霓虹灯早就熄灭,还剩下灰溜溜的钢筋外壳,与远边的低矮楼群浑为一团,黯淡无光。
周麟换了一个口气,对着珠江大大咧咧的骂着:“我们部门的那些关系户才真是什么都不做,就我一个临时工在做事。但是局长又没办法说他们,最后就是老怪我——对,没有错,看到我,不管什么时候就是一顿臭骂。报告写不好就说我怎么学语文的,联系不了商家就指责我怠职混饭吃。看看那些个关系户,上班聊天串门什么都有,就是不做事。”
马皇天将手搭在他肩膀上,“不就是个关系户嘛。我帮你说说,你也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
周麟甩开他的手,脸转过一边,沉沉的叹道:“算了,说了也不顶用。”
“想想看,我们当时怀揣着五光十色的梦想来到广州,想着凭借自己的双手就能开创自己的未来。”我手靠着栏杆,撑着头看着他们,明明是笑着说,但说的内容就是酸溜溜。“就像我现在的公司,虽然工资基本接近广州人均工资,但是要处理许多的账目数字。可是这些——都不算个事情,处理那些同事的关系才是一道坎,你们看,就我一个光杆司令在调账,明明是团队却没有一个来帮忙。幸好有你们这些兄弟,不然我都不知该怎么活下去。”
“习惯这样就好。”沈安驿不冷不淡的说道。
“是呀,我们出了大学,用了三四年的时间还没完全习惯。”我直觉得一阵鼻子微酸,“还是学校的时候好,只用想好学习怎么样就可以,剩下的时候可以不断的梦想,不论是白日梦还是天方夜谭,我们可以有想的自由。”
“说的也是,不用像现在为各种人和事而狗一样的活着。”周麟应和说道。
“安驿,你那单位不错,不仅钱多,而且又不用那么辛苦。”我笑呵呵的看着旁边的沈安驿。
“我也面临压力,只是你们没体会过。”沈安驿撇过头,故意用着云淡风轻的话语浅谈自己的高压力,“每天在银行柜台坐上十个小时,面对几十个人,给他们办理所有银行业务。”
“不谈工作了,都是一把泪。”马皇天大大咧咧的做出总结。“抱怨也没用,还是得生活。我们这些兄弟从高中到现在,一直都在一起,就差穿一个裤裆……”
“滚你的蛋去。”周麟用膝盖狠狠的顶住他那大肥屁股,挺不满他那粗俗的言论。
“就像今天你们都来帮我。”我笑嘻嘻的说道:“你们以后有需要我的,尽管说,我肯定会帮!”
“真有义气。”马皇天搂着我的肩膀,偏偏甜腻的说道:“这才是好兄弟嘛!”
我一把嫌弃的推开他,“真重的口臭啊,你也滚一边玩去。”
“那是——流星么?”沈安驿指着天空,让我们赶紧抬头。
我揉揉眼睛,仔细的盯着黑色的苍穹。还真的是流星,我没有眼花。那颗星星半明半昏,拖拉着又细又长的尾巴,剪破了夜空,缓缓的从广州塔一侧滑过。
“流星划过,赶快许愿呀你们这群白痴们!”马皇天急吼吼的骂道。
真是一语惊醒醉中人。我喝得迷迷糊糊,脑子迟钝,早忘记了这个对流星许愿的习俗。我双手合十,浆糊一般的脑子还在天旋地转,要许的愿望一个接着一个蹦了出来,却又描述不出个大概。流行快要驶离天空,我赶紧扒拉最后一个跳出来的愿望,“干脆就希望我们友谊万岁,兄弟情谊地久天长!”
马皇天笑嘻嘻的对着那流星许愿道:“希望我们顺顺利利,万事大吉哈哈。”
沈安驿的愿望很有特点,“今年找到女朋友,明年结婚。”
“蠢货,怎么许的跟新年愿望一样。”周麟吐槽了所有人的愿望,拽紧双手的拳头做努力拼搏的样子,大声的喊道:“我要赚大把大把的钱,享受公平的待遇,争取做个人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