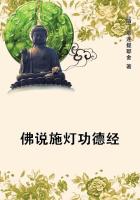她刻意在“两年前”这些字眼上加重语气,然而眼波流转间,却只见纯净笑意。
这妮子好生可恶,竟在讥讽我是昨日黄花吗?
瑗夫人目光一凝,心下已是大怒。她微微咬唇,却是隐而不发,笑容丝毫不减,亲热地挽了燕姬,一起向前漫行。
二人步伐轻盈,瑗夫人又是刻意,几步之后,便领先众人几丈,遥遥在前。
“我本就是蒲柳之姿,年岁既长,和妹妹站在一起,倒越发显得可笑可叹了。”
叹息声中,瑗夫人仿佛是在哀叹韶华易逝,岁月无情。随即,她压低了声音,仿佛漫不经心地道:“妹妹不仅貌美,还甚是贤淑体贴,看着君侯忙于公务,就日日亲手熬汤奉入书房,单这份温存,就让我等望尘莫及。”
燕姬目光闪烁,下一瞬,却听到瑗夫人的声音,竟是含笑低沉,近乎诡谲,“妹妹日日去书房,想必连那些文书密函的位置,都要熟记于心了!”
燕姬只觉得脑中轰隆一声巨响,顿时面色苍白,咬紧了银牙,冷笑道:“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竟是听不懂了!”
瑗夫人笑容更盛,越发亲密地挨近了她,吐气如兰:“妹妹这么聪慧,又哪会不懂我的意思——你才初来乍到,就这么急着登堂入室,太过张扬了些吧!”
她一手扶了下香肩上的银貂斗篷,一手却顺势将燕姬鬓边的金钗轻轻拔下:“妹妹这只钗头怪利的,要是扎中了人,那可怎么得了,可要好好保管呢!”
燕姬双目冷瞪,眼睁睁地看着她拿走自己的随身利器,却很快恢复了冷静:“只是个凡物,不值当什么,姐姐若是中意,送你也无妨。”
“看妹妹说的,我倒成了个剪径强人不成?”瑗夫人笑得越发妩媚,手掌一用力,那只凤钗竟在她的柔荑双指中逐渐弯曲,最后成了一块金饼。
金质偏软,可若要凭两个指头拗成这般,也颇需些不凡功夫。燕姬眼看着这一幕,心中惊疑不定,压低了声音,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想要怎样?”
“看妹妹说的,只是姐妹间戏耍,难道我还会去告诉君侯不成?只是你我姐妹间情比金兰,妹妹在书房里找着了什么有趣的,也该让姐姐我开一开眼界才是。至于我的来历,妹妹不是早就知道了?”
瑗夫人微笑着,将金饼还入燕姬掌中,气定神闲道:“妾身乃是奉王上亲命,从宫掖中仔细挑选,特地赐予君侯的良家子。”
燕姬看着对方意味深长的眼神,心中有所明悟,她扯了扯唇角,悄声道:“原来你和我也是一路,只是主人不同……”
“妹妹真是兰质蕙心。”瑗夫人笑得雍容大度,朝后微微颔首,便带了自己的从人扬长而去,只剩下燕姬站在原地,却是因为不甘和躁怒,连脸颊都滚烫得绯红起来。
燕姬僵立原地,半晌才回过神来,她猛地甩袖回头,低喝道:“还愣着做什么,回宫!”
下一刻,她的左肘撞到了一件坚硬之物,随即,烟水弥漫,庭院中央一片忙乱。
燕姬抱着手肘忍痛,定睛一看,却是气不打一处来——原来是跟在她背后伺候茶盒的小侍女躲闪不及,竟一头撞上了她!
金黄的蜜柑茶在她的碧罗锦裳上漾出片片污痕,两种色彩混合之下,近乎五色斑斓。
燕姬怒极反笑:“宫里出息的奴才这么多,就配给我这般不中用的。”她提了裙裾,甩开了侍女的扶持,转身道,“快把这个不长眼睛的东西给我拖回去!”
她余怒未消,恨恨道:“丢人现眼还嫌不够吗!”
燕姬回到自己宫中,看也不看一旁瑟瑟跪地的小侍女,她换了衣裳,兀自烦躁道:“这身云锦可是君侯亲赐的,乃中原世家所制,宫中统共也只有一匹,就这么糟践了!”
一旁的女官见她意兴阑珊,于是上前细声道:“主子您且不用着急,及时浆洗也许还有救。”
燕姬瞥了她一眼,不耐道:“色贯其中,便是彻底废弃了,还能有什么救?”
女官略微想了一会,眼前一亮,道:“有了!”
对着燕姬不解的目光,她道:“先前君侯从外面掠回了一批苦奴,奴婢听说其中有个女子,一手绣工甚好,说不定,可以让她以绣纹补救。”
“绣工甚好……”
燕姬一听,面上便有了喜色——燮国地处西北,珠宝尽有,好的绣匠却嫌弃此地苦寒,不愿在此扎根停留,是以宫中虽然华服甚多,却无甚绣彩,着实有些单调。
“既然来了个有手艺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女官面对燕姬的嗔怪,有些犹豫道:“她……她面上刻了黥纹,甚是丑怪,怕惊了主子。”
燕姬闻言皱眉,不以为然道:“朝廷的罪奴,脸上有刺青黥记是免不了的,哪来诸多废话——还不快给我把人唤来。”
一声令下,早有人依言而行。一刻之后,便有人轻揭鲛纱帘幕,珠光闪动之下,一道轻盈身影站在下首,躬身示意。
燕姬抬眼打量,却也禁不住轻噫一声,心下一震。
那女子着一袭布衣,长发垂髻,右半边脸被乌发遮住,看不真切,左半边却是肌肤胜雪,只是,青黑黥纹在其上繁密连贯,显得狰狞可怖。
燕姬也吓了一大跳,她定了定神,有些厌恶地瞥了一眼,曼声道:“听说你绣工不错,是真的吗?”
“不敢说好,只是略懂一二。”
那女子低声应道,声音也有些嘶哑,随即抚着胸低咳起来。
“罢了,罢了!”
燕姬见她咳得难受,倒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缓和了一下声调,继续道:“你且看看这云锦……”
悉悉索索的衫衣抖动声响起,早有侍女抬了杌子来,将染了色的衣裳展开放平。
那女子细细看了,伸出手来抚摩,窗外天光映得她皓腕似雪,竟仿佛通身剔透一般。
嘶哑的声音响起,因这满殿里的熏香,漾出空寂沉闷的回声——“色入已深,又染得四溢横流,再好的刺绣也遮不了满幅,请恕奴婢无能为力。”
燕姬一听,柳眉一挑,看着阶下之人那骨瘦嶙峋的丑怪模样,连斥骂的兴致都没有了。
她一回头,看见先前那个小侍女,正跪在一旁默默啜泣,禁不住一腔怒气涌上喉咙,连声音也变得尖利起来——
“你这小贱婢还敢哭!坏了我这匹云锦,做出这个样子来给谁看!”
说罢纤长玉指已伸出,尖利的指甲几乎要生生戳入对方的眼中——
“把她给我拖出去……”
未尽的言语,带着凛冽的杀意,蔻丹的鲜红映着她的雪白十指,仿佛宣昭了这微贱生命的终结。
这时早有健妇上前,七手八脚将人拖下。
哭喊声中,小侍女被生生从地上拖行,经过那黥面女子身边时,她正垂首敛目,仿佛是泥塑木雕一般。
小侍女被拖得衣衫凌乱,汗巾腰带都散了一地,她哭昏了头,栽倒在地,开裂的衣领口跳出了一枚香榧小扣,雕得很是精致。
那物件跳跃着,映入黥面女子的眼中,她寂若死水的眼中,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
怎有可能……竟会是……
燕姬冷哼了一声,心下懊恼不已——几日后,便是闻侯的生辰,这件衣裳正要派上大用场。
她的沉思被一句突兀的话打断。
“燕夫人请息怒,这件衣裳修补起来虽然棘手,却不是无法可想。”
燕姬一愣,看到那黥面女子正抬起头,直视自己。
那目光幽然深邃,微一触及,竟连周身肌肤都为之刺痛。
蓦然被人插言,燕姬本该发怒,却不知怎的,只觉得那目光凝然,自己竟讷不成言。
那一瞬间,这个黥面女子带给她很奇异的错觉。她身上的那种清静尊贵,连先前自己觐见的燮王也难与比拟。
她呆了一呆,暗骂自己胡思乱想,随后皱眉道:“你方才可是说无能为力!”
“光凭奴婢一人,当然不能——我需要她的协助。”
那女子手一伸,指向了被拖在地上狼狈不堪的小侍女。
燕姬回过神来,冷冷打量着她:“哼,你是想救这个小丫头?”
“不敢有瞒夫人,奴婢确实如此作想。”
迎着燕姬微愕的目光,她咳嗽着,苦涩笑道:“奴婢刚刚从此物上认出,她是奴婢少时失散的亲妹妹。”
她举高了手,掌心赫然是那枚香榧小扣。
这一下大出众人意外,却听她继续道:“先前奴婢一人,确实无能为力,现下有妹妹在此,她学过拆丝之法,拆开之后分别洗净,不足之处再由奴婢以刺绣补之,定然天衣无缝。”
燕姬听了,半信半疑:“你该不会是来诓骗本宫吧?”
“如若有假,夫人再治我姐妹二人重罪不迟。”
燕姬闻言一笑,指间的蔻丹闪烁生辉:“好,若是你们姐妹真能挽回,本宫就饶过你们这一遭。”
言下之意自明,那女子满口答应,拉了妹妹正要退下,却被燕姬唤住了。
“本宫差点忘记问了,你叫什么?”
那女子闻言,目光幽深,抬起头时,笑容里带了一丝不易捉摸的意味。
“疏真……我的名字,叫作疏真。”
白雪皑皑中,早已由宫人们开出一条曲折小道,越往偏僻处,越是崎岖难行。
疏真拉着小丫头,一步一顿朝前走去,雪没过她的膝盖,寒意沁入,引得她又是一阵咳嗽。
“你真是我姐姐吗?”
尤带稚气的声音响起。疏真勉强止了咳,看向身畔之人,抚胸喘息着苦笑道:“你已经忘记我了吗,虹儿?”
她伸出手,掌心伤痕累累,她有些费力地从怀中掏出一物——竟是另一枚一模一样的香榧扣。
“真是姐姐!”虹菱又惊又喜,眼中流下不敢置信的泪水,深深抱紧了朝思暮想的胞姐,“姐姐,真是你!”
她激动得语无伦次:“那年北狄人打进来,又逢上八府之乱,舅妈她们说把姐姐你卖给了京城的官人,没想到你我还会再见面!”
疏真将她揽在怀里,温柔地抚着她的头发,眼中带着深邃难懂的悲喜之意。
“是啊,十年了……”她叹息着,双眼望向无边无尽的苍茫天宇。
已经十年了。
可霓,十年前你来到我的身边,一直服侍我、陪伴我,不离不弃,直到我穷途末路的最后……如今,难道真是你在冥冥之中有灵,让我遇到了你的亲生妹妹?
北风呜咽,雪屑纷飞,天光渐暗,淡淡余辉照在紧紧相拥的姐妹身上,仿佛是幽冥中那飒爽英魂的欣慰轻笑。
可霓啊,你还是不愿我萌发死志,所以才将妹妹送至我身边,让我好好活下去吗?
疏真的眼中闪过难解的悲怆怅然。她静静含着笑,轻抚着虹菱的头:“虹儿,姐姐现在改名了,叫疏真,你可记住了。”
虹菱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可是姐姐还是姐姐,不是吗?”
“你说得对!”
疏真的声音温软轻柔,随着两人的脚步,逐渐消失在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