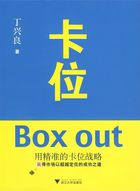黄国华和李国生要离开面粉厂了,厂长尤得柱要为黄国华、李国生举办送别宴(其实就是在食堂一起吃顿饭),黄国华婉拒,他不想惊动厂里其他人,交接了工作,收拾好行李。尤得住表达了对黄国华的感谢,说:“老厂长,你和国生的离开是我们厂的一大损失啊”,黄国华淡淡一笑,说:“得柱,你过谦了啊,损失谈不上,有了新陈代谢,才有动力,你的能力有目共睹啊,相信面粉厂在你的带领下,会发展的更好,我啊老了,思想僵化,视野有限,跟不上时代了”,尤得住说:“老厂长哪里话,你就是我的主心骨啊,你这一走,心里空落落的”,李国生也交接完了工作,推开厂长尤得柱的门走了进来,“国生,坐”尤得柱将凳子递给国生,黄国华问国生说:“工作都交接完了?”,“交接完了”李国生回答说,尤得柱对国生说:“国生,全县在年轻干部里面,你是很出色的一位,县委、县政府领导对你都有很公正、客观的评价,在交通局大你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都看好你”,“谢谢尤厂长”李国生浅浅一笑,黄国华在李国生肩膀轻轻拍了拍,表示鼓励。
天空中,云层似画笔扫过,在高远的晴空里淡淡晕染,凄冷的风摇曳干枯的树枝,几片残叶簌簌的掉落下来,几只白色的家鸽在房顶“咕咕”叫着,勿的飞起,留下悠扬的哨声在天空回响。要离开了,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全是感情,初建厂时战斗的身影历历在目,仿佛昨日。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也都过来了,司机已将黄国华和李国生的行李搬上车,二人一一和送行的几位同志握手道别,汽车驶出了县面粉厂大门。
农历十二月,俗称腊月,是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月份。进入腊月,春节就越来越近了,过年的气氛渐渐浓郁,置办年货,洒扫庭厨,都是要在腊月提前做好的事情。进入腊月,大人们就开始盘算着该怎样度过这个春节,心头的忧虑如同这光秃秃的冬日景象,靠天吃饭,锄头底下刨吃食,李家庄的人们辛劳一年,也落不下几个钱。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年货大多都是一些土特产,或是到集市上用粮食换取过来的“稀罕”物件,过年最高兴的要算孩子们了,新衣服、好吃食、压岁钱、鞭炮,糖衣等等,始终是他们的最爱。
李贤老人算计着需要准备的年货,面类、肉食、糖瓜;红色纸、绿色纸、黄色纸;香炮、灶糖、神仙树……在腊月二十三小年之前,这些货物必须要准备好的,再挑选个黄道吉日,彻彻底底将家里卫生清扫干净,之后,全家人就高高兴兴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腊月初十,天一亮,婆婆张慧开始张罗着做小馒头,这拳头般大小的白面馒头,也称“蒸馍馍”,通常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等重要时刻摆上桌面,成为餐桌上世俗而温暖的美食,也是一种最为隆重礼仪的标志。
晓佳放了寒假,在厨房帮忙,张慧将面团做成小馒头状,均匀的把手中的玉米面粉手轻轻撒在面团上,预防成型的面团黏贴到案板上。晓佳坐在灶台前一把一把的添着柴火,水滚了,她站起来揭开锅盖,白色的水蒸汽魔鬼般的充斥在眼前,遮住了她全部视线,担心柴火掉下来,她赶忙蹲下准备往里塞,但是柴火终究还是掉了下来,奶奶张慧埋怨说:“这么大的娃了,笨手笨脚,火都烧不好”,晓佳脸微微一红,顾不及火烧的疼痛,裹紧地上燃烧着的柴火一把塞进灶腔,柴禾燃烧发出的浓烟熏了眼睛,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张慧瞥了一眼,放下手中的玉米面粉,厌恶的说:“你说上辈子我造了什么孽,你遭了什么灾,竟然进了一家门,骂不得,说不得,就知道哭,什么活儿都干不好”,“我刚揭锅盖,一不小心柴禾溜了下来”晓佳怯怯的回答说,张慧的语气中夹杂着严厉,说“别辩解,赶快把蒸笼支在锅上”。晓佳起身,使足全身力气,抱起蒸笼支在锅上面,蒸笼由木板和竹篾制成,分三层,足有半人高,面团混合水汽形成的污垢黏贴在表面,常年累积,增加了蒸笼的重量,晓佳力气弱,抱起蒸笼已是趔趔趄趄,所以,在支往锅台上面的时候用力过猛,“哐当”一声脆响,晓佳心中一惊,迅速检查了灶台一周,确认无任何损坏,悬着的一颗心随之落定,这一声响还是招来了奶奶的一阵责骂,晓佳没有吭声,蹲在灶台前烧着柴火。张慧嘴里没完没了的责怪,一边将成型的面团放到蒸笼中,解下粗布围裙,仍在灶前的草堆上,语气生硬的说:“馍馍熟了之后,把厨房打扫干净”,之后走出了厨房,晓佳回应了一声,畏缩在灶台前,添柴烧火。
街巷中,几个邻家小孩已穿上缝洗干净的衣服,嬉笑着,打闹着,如欢跳的小鹿,似欢快的小溪,手牵手奔走在街巷里,似乎在提前迎接春节的到来,一会高歌,一会低语,仔细听听,孩子们是在唱腊月歌:“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小孩子们的合音天籁般回荡在村子上空,和着家鸽的哨声一起,在天高云淡的苍穹中,奏响着一曲意境悠扬的冬日赞歌,给这肃萧的冬日些许温馨的点缀。晓佳坐在昏暗的厨房里,灶台洞燃烧这的柴火光照亮了她俊俏的脸,小手扶着长长的玉米秸秆,机械的往灶洞中一寸一寸递着,头转向窗外,目光里满是渴望和羡慕,她渴望鸟儿的自由自在,她羡慕邻家小孩们的欢乐无邪,她希望和“上学四人帮”伙伴们一起快乐的玩耍,她想和村里女孩子们一起跳皮筋……晓佳脸上益出了笑容,似乎她正在伙伴们撑开的皮筋上,蹁跹起舞,“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马莲开花二十一……”,她就是一朵含苞待放的马莲花,和温室中的蓓蕾相比,只不过成长之路多了些羁绊与岔路,风雨无阻,但这朵马莲花,必将璀璨夺目的盛开。
“馍馍熟没有?饿死了”小姑彩娥扯着大嗓子奔了进来,晓佳被小姑的高嗓门惊吓到,柴火撒了一地,晓佳不顾直窜的火苗,迅速将柴火塞进了灶洞,火星还是溅到了手上,晓佳疼的直呲牙,彩娥在一旁哈哈大笑,大摇大摆走了出去。王婉芬已接近生产期,全身难受,炕上躺会、坐会、站会,都不舒服,她知道晓佳在烧火蒸馍馍,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挺着大肚子来到厨房,给晓佳说不要添加柴火,让余温催熟,晓佳断了柴火,将妈妈扶进偏房,上了炕,王婉芬注意到了晓佳手上柴火烧过的痕迹,拉着晓佳的手,抚摸着柴火烧过的地方,手背青紫色,隆起发肿,这是天冷生成的冻疮,柴火烧过之处变成了黑色小窝。看着晓佳的手,泪花在王婉芬眼眶中转动,心疼的问:“疼不疼?”,“不疼,妈妈”晓佳伸手擦掉王婉芬脸上的泪水,王婉芬艰难的挪动身子,拿出在箱底存放的凡士林膏,挤出一节,均匀的涂抹在晓佳手背柴火烧过的地方。
馍馍蒸好了,晓佳踩在板凳上将蒸笼一层一层摘下来,白色的是白面馍,黄色的是玉米面馍,紫色的是荞麦面馍,一出笼,面香味扑鼻而来,晓佳选了两碟子形状好看的馍馍,一碟子给爷爷奶奶他们吃,一碟子给妈妈吃。上房内,乔乔在胡言乱语的说些听不懂的话,见晓佳端馍馍进来,将盘子夺了过去,拿起馍馍使劲往嘴里塞,馒头散落地上,晓佳一个个捡了起来,放到桌子上,李贤老人对晓佳说:“娃儿,给你妈端点白面馍”,晓佳应了一声,回厨房端另一碟子馍馍和妈妈吃。张慧拿起馍吃的一瞬间,狠狠白了李贤老人一眼,她不愿听到丈夫关心儿媳的任何话语。
李贤老人没有去吃刚出锅的热馍馍,吸了几口旱烟,去厨房精心挑选了几个大的、笑的开的(李家庄的人们将馒头蒸熟时裂开的纹路称做笑纹,如何人的笑脸。纹谷越大表示笑的越灿烂,是吉祥的象征,也是对生活美好的一种寄托)、形状完好的馍馍乘在几个盘子中,垒成金字塔状,一盘白面馍,一盘玉米面馍,一盘荞麦面馍,一字排开,分别摆放在上房祖先牌位和院子正中央的小方桌上面的天神排位前,分别焚上香,烧了黄纸,磕了头,作了揖,李贤老人、裹着厚厚的破旧羊皮大衫,愈加使他行动不便,满是老茧的双手支撑着小方桌艰难的站立起来,回了上房,拿起一个荞面馍吃。李贤老人举行的是一种祭祖祭天仪式,简单而庄重,在李家庄人们眼中,粮食,一年幸苦所得,是大自然的恩赐,是受到上天诸神的庇佑的,祭天,是五谷丰登后或重要节日里必须要做的一件重大事情,以谷物反哺敬祭诸神,表达着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对神明的虔诚和对祖先的感恩,而食物,永远是凡尘众生与天地神灵沟通的最朴素、最直接的通道,这些食物带着手的温度、承载着勤劳和智慧,也带着劳动人民对时光流转的感知,这种传统,从农耕岁月一路走来,也终将在我们的视野里渐行渐远。
李铁匠拾粪回来了,佝偻着身子,头缩在衣领里,头发长时间未清洗,毡片一样扣在头顶,肩头棉花红杏般从棉袄的破洞中露出,在风中凌乱着,他一手提着竹笼,一手拿着铁锹,竹笼里稀稀拉拉的散落着几块动物粪便,僵尸般走在冰冻的土地上。在经过李贤老人家门口的时候,李铁匠看到院子里摆放的馒头,知道李贤老人家有热馍馍出锅,他将粪笼和铁锹放在大门拐角处,直了直腰,大步走了进去,“四叔,四叔”李铁匠一边喊叫一边朝上房走去,李贤老人坐在火炉边抽着旱烟,听到有人喊,缓缓起身,张慧从窗户中看到是铁匠进来,对丈夫说:“铁匠咋来了?”,李贤老人揭起厚重的门帘,对院子里的铁匠说:“铁匠来了啊,赶快屋里坐”,李贤老人将铁匠迎进屋,李铁匠坐在火炉边的木板凳上,张慧下了炕,递给铁匠一个白面馒头,笑着说:“铁匠吃馒头,刚出锅的”,李铁匠没有说话,拿起馒头大口吃了起来,患病的乔乔看见铁匠吃着馒头,坐在炕上嚷嚷着要吃馒头,乔乔已吃过几个馒头了,这是在闹腾,张慧塞馒头到乔乔手中,乔乔嘿嘿一笑,口水顺着嘴角流了出来,张慧用手拭去乔乔嘴边的口水。“铁匠,饿了就多吃几个”李贤老人对狼吞虎咽的铁匠说,“铁匠啊,等会走的时候给惠英(铁匠老婆)带几个吧”,李铁匠专心吃馒头,嗯了一声,没有多余的言语,李贤老人和妻子张慧对视了一眼,两人眼中全是无奈,看样子李铁匠是要撒泼了,在一连吃了几个馒头后,李铁匠打了几个饱嗝,用手擦了擦嘴,黑黑的脸上闪过一丝诡异的笑容,对李贤老人说:“四哥,馒头我带回去些,让惠英尝尝,嘿嘿,啊四哥,我家里好长时间没吃过白面了,你再给我点白面吧”,听到铁匠这话,张慧立马变了脸色,欲出口说话,李贤老人眼神示意妻子不要说话,答应了铁匠的要求,张慧不再作声,李贤老人起身找来编织袋,分别装了馒头、白面,李铁匠拿了东西,出门拿了粪笼和铁锹,心满意足,瘸着腿朝家中走去。
李铁匠走后,张慧责怪丈夫说:“你个老东西,给这无赖拿走这么多五谷”,李贤老人坐下叹气说:“铁匠是和我们家较上劲了,你看不出来啊?小匠的死他是赖再国生头上了,今天若是不打点,他会撒泼闹个没完没了,这只是个开始,哎,老天爷啊”,李贤老人依炕沿蹲下,“丝丝”的吸起了旱烟,张慧弯腰捡起乔乔吃剩仍在地上的半拉馒头,责怪丈夫说:“我们都没有多余的白面吃,你大方,送给他那么多?”
“不给点他是不会走的”李贤老人说,
“他不走?反了天了,看我不用棍棒赶走他”,
“这个国生啊,当初招惹他们干啥?现在人没了,凭铁匠两口子那修为,是要记恨国生一辈子的”,
“国生也是可怜他们,那‘短命’不争气,不死才怪”,
“人都死了,留点口德吧”,
“口德?哼,那‘短命’害国生不浅,在面粉厂吃国生的、喝国生的不说,要不是他,国生现在能受处分?”。
“降职了,工作干好了可以往上升,人没了就永远没了,哎,老天爷,一颗嫩苗啊,偏偏不学好”,
“我去他家把馒头和白面要回来”张慧越想越气愤,放下手中的麦辫正要走出房间。
“你站住,送给别人的东西哪有要回来的道理?”李贤老人厉声喝住走出房门的妻子。
“你个老东西,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对付这种无赖,就得以其道还其身”张慧止住脚步,走了回来。
李贤老人舒了一口长气,继续吸着烟斗,张慧上了炕,哄乔乔睡觉去了。
偏房里,王婉芬吃过几个热馒头,有点困,躺炕上休息了,晓佳替妈妈盖好被子,去了厨房,清洗了蒸笼,倒掉锅里的热水,息掉灶坑中燃烧着的柴火,回了偏房,到炕上编织麦辫去了。
李铁匠老婆惠英还未从失去儿子的无限悲痛中走出来,面容枯槁,披头散发,见丈夫回来,挣扎着从一推破旧的被褥中爬起来,看到两半袋子的馒头和白面粉,沙哑着嗓子说:“你哪里弄来?”,“从四叔家拿的”李铁匠稍稍有点得意。
惠英揉了揉眼睛,眼神缓缓放出几许光芒,铁匠拿出几个馒头递到老婆惠英手中,馒头散发出浓浓的麦芽香气严重挑逗起着惠英干涩的味蕾,惠英一把抓了几个馒头,塞进嘴里,疯狂的咀嚼着,好久没有吃到如此香甜的白面馒头了,看着老婆乞丐般的疯狂模样,李铁匠心中仇恨的火焰熊熊燃起,对蓬头垢面的老婆说:“他娘,从今以后想吃什么,想穿什么,你尽管告诉我,我去四叔那里拿,小匠走了,他国生要负起这个责任,小匠该尽的义务现在必须由国生来尽,就是我死了,也得他国生披麻戴孝”,李铁匠坐在炕沿,目露凶光,直勾勾的盯着凸凹不平的地面,这目光,放佛要翻过重重山道道岭狠狠的将国生吞噬。惠英听到小匠二字,母爱的堤坝再次汹涌决堤,哇的一声,号恸崩摧,又哭倒在一堆破旧的被褥里。妻子的伤心欲绝,断肠的哭声,藤条般狠狠抽打在铁匠的心上,他的内心迅速决堤,千沟万壑的黑脸上,浑浊的泪水一行行的滚落下来。他没有去安慰老婆,就让她哭吧,怀胎九月,拉扯二十几年,命途阴罗,怎能不断肠?李铁匠擦掉脸上的泪水,挽上竹笼,扛着铁锹,耷拉着脑袋,出了院门,又到后山转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