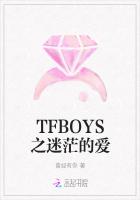在临分别前,空林终于劝服了杜眉,心下十分开心。
一直在底层颠沛流离两年多的生活,使他明白普通人为了一日三餐的温饱,要费了多少心血。
但是这一切,在战争来临之下,或者是时局动荡之时,一切都如薄纸般脆弱,不足凭侍,一戳便破,世上也不知何处,可再次寻得宁静平和的港湾。
家是人心港,国是家之湾!
离开了稳定的外部大环境,除却个别优异者,能够趁势而起,多数人只能随波逐流,难以自己。
所以空林对于自己的判断,不敢说分外精准,但以他一惯从大面分析势,小处着眼一个人的判断方法,相信局势该与自己所想相差不远。
晨光中,看着来往于身边,需要通过双手忙碌,来赚得温饱的普通人,又渐渐汇聚于长安城的大街小巷。
空林的嘴角勾起一屡欣慰笑意,人却不断的逢屋越屋,尽力避开人流视线,偶尔不得已疾行几步复又转向挪开,一路上体内真气保持自然流转,仿佛不假他求。
很快跃马桥已然在望,此时那片附近已是人来人往,舟来车往,热闹的一塌糊涂,空林接近后放慢脚步,游目四顾并未发现有何碍眼之人,于是一把钻进福聚楼,旋又整日整夜的隐伏不出。
将东西悄悄转手之事,他并不急于一时,许多事欲速则不达,不然只会坏事。
这连续两三日,他都是呆在书房中苦读,除了偶尔下楼用膳,或者在跃马桥一带,徐步而行流连风光,便无其他任何异常行止。
老实的出乎所有暗中监视之人的意料之外,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两三日时间,他完全不似表面般悠闲自若、无所事事,实际上他几乎步步算计。
书房苦读是为了必会遭遇一场的诗会,或许明日、或许后天,不管哪一日,它都会不请自来,所以他选择主动出击,至少自己可做足准备;
下楼用膳则是为了掩饰,学习模仿由杜眉特意安排来,与他对话的伙计口音,他们有的是带有西域胡音,有的带有梁州口音。
通过数次交流,很快他便掌握了其中的发声技巧,想要完全学会也许还不可能,但是让自己的话音中夹杂着这两地的口音,却是不难。
而在跃马桥一带四处信步而走,偶尔还会与贩夫走卒,不时的拉几句家常,看似随意的听些小故事,实则是从这些朴素的话语中,掌握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
居于这一带商贾巨富的身份背景,为人处世的口牌,从情报中得来,总会失之于片面,但是从口口相传中知晓,往往在某些方面显得更为精准。
另一方面,从一些小故事中,还能了解当今天下,兴盛的行业是哪几处,败落的又有哪些,某个家族因何而起,某个又是因何而衰;
只要结合朝中历史,与之略一应证,事情便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以有心算无心,猜出背后得利者。
而有些却是尘封往事,貌似已经时过境迁,好像与今日无关,但是凡事皆有因才有果,从头理出一条线,从古延伸至今,许多事便自然有了眉目。
而结合这些线索,再来印证杜眉处所得的情报,便能将有些盲无头绪的事情,理出一丝脉络。
而当前的局势正因不明朗,才会多了许多别有用心,希望能混水摸鱼的杂鱼角色,而从之前民间得来有用线索,便能派上用场。
许多消息于下人之间口口相传,往往未必无因,而且由小见大,从这方面听到的为人口碑,更能有效的凸显某些人真正的为人之道。
免至为一些表面消息误导,例如,那本《长生密录》所撰写的名单里,有几位便居于附近,在下人中风评不算太差,亦不见得有多少奢侈枉枞行为。
那么他们贪墨收受的银两,又为的什么,这些便有文章可做。
当然许多事,前世在此盘恒两年多,早就有所耳闻,但是以前着眼点不同,许多消息听过便忘,并未多想,眼下有心计较,一路走来当然是受益菲浅。
有些事旁人听来无头无尾,但是在他听来却是字字珠玑。
只因他多出两年多的前世阅历,许多事开个头便能闻弦歌而知雅意,立时骚到他人痒处,人们总乐意与他多聊几句,有时不经意间又有收获。
不动声色间,他通过不时与二女或明或暗的会面,渐渐的拟出部分行事的步骤计划。
如此,当他通过杜眉之手,经过两三日的挑选,终于雇足了那间大宅所需的卑仆下人,才选择搬了进去,离开了蜗居了好几日的福聚楼。
而随着踏进这间大宅那天开始,标志着拟好的步骤计划业已准确就绪,可以伺机而动了。
或许有些人业已等的不耐烦了,正等着他露出破绽呢!
不过空林仍是耐着性子,装做熟悉环境似的,留在大宅中足不出户一整日,方才手书一封拜贴,在第二日早间,登门造访白江原的居所。
当他从下人口中得知,此人昨夜留宿春江苑彻夜未归时,轻哦一声留下拜帖便走,表现的毫不拖泥带水,下人惊愕的片刻才发现,却已追之不及只能留待家主回来方好回凛。
空林早就得知此子,有露夜留宿花丛的风流习性,故特意选个早间递上拜帖,便是希望暂不与此人见面。
免致交流下突然发现自己口音有变的事实,而若到了明日晚间,那时人多眼杂,哪怕他听出其中异样,亦无法多问,如此便可避过砌词狡辨的后患,空林实在头痛了圆谎这门技术活。
只能选择能避则避,实在避不开硬着头皮也只能上了。
距离自己定下的诗会尚余足近两日,准确的时间是明日戌时初,地点便是前次失约的上林苑,此举是为表示诚意。
不过现下这段时间又该何去何从呢?
信步四处的空林,正沿街游览清幽河畔风景。
此时阳光辉洒下的路旁春芽吐蕊,万物枯逢新春,道旁槐榆林立,似岗如哨,河中商旅不绝,吆喝难歇,瞧的空林亦是心情舒畅。
及至不远处一块匾额上书‘法华寺’三字落入眼中,方又忆起实有必要逛逛这长安城中,几乎随处可见的道观寺庙。
随即信步前往,于是只见一位身背长剑的青年儒生,四处流连于长安城的名刹道冠,或是偶有不阻男子的庵堂,他也饶有兴致的前去转转。
遇着住持有兴,顺带用上刚刚能通读过的经策文章,若不能引经据典便顺口胡诌几句,随即逃之夭夭。
如此下来,不管他人是如何看法,有时他也感觉受益菲浅,增长了不少见识。
直到日落时分,方才拖着有些疲倦的步子,慢慢信步朝家中回赶。
蓦然印有‘三合庵’三个字的匾额,落入空林眼中,方才想起这间一开始,带给自己些许独特意味的庵堂,都还未进去瞧过。
不由信步转向,距大门尚余六七步时,便给列在门外的两组护卫合兵阻住通道,口中劝戒道:
“来人止步”!
空林不由好奇停步道:“劳驾,两位军爷,请问此地是何要地,在下为何不能进去?”
其中一人解释道:
“此地因与宫中有旧,太后懿旨为免闲杂人等擅闯,打扰此地清静,男子一概止步,就连皇上都不例外,女子则需及弟以后方可随意出入。”
此人大约是看空林样貌谈吐不俗,似个读书人,故解释的特别详细。
空林赧然一笑,抱歉道:
“那在下打扰了,告辞!”
仍是那人回礼一笑道:“无妨,请回!”
说罢便不再理会对方。
空林徐步离开,绕着此间庵堂几乎大半个圈,才发现还有一间后门可以出入,然此刻却闭的严严实实,除非强闯否则别无办法,由于院墙高足有两丈,想要随意翻越实在不便。
空林自家知自家事,以他还未练成的鸟渡术想要轻松翻越,还是力有未逮,只能打消此念。
正要离开此地返回家中,突然心中一动,只听一道‘吱呀’启门声传来,那间后门蓦然开启一条小缝,一道苗条纤细的身影忽然闪了出来,光凭身材便知这是一妙龄女子。
这道身影刚一印入眼帘,空林只觉一阵熟悉感传来,还未待他想出此人是谁。
两人已经彼此打了个照面,虽然天色刚刚入黑,但是这条小巷中尚余些许月色洒落,足够二人瞧清彼此样貌。
下一刻二人口中几乎同时惊忽一声,‘啊’!
女子是震惊于以自己的耳目,居然不能发现门外如此之近的距离,还有人驻足。
直到彼此突然打个照面,方才发现面前居然有人,忍不住芳心一乱,暗忖之人究竟是何方高手,为何跟踪自己至此,又突然现身,心中立即提起十二分精神,凝神戒备。
空林则是无论如何也未想到,居然能于此处碰见她,这位令她几乎一度魂牵梦引的女子,刻下怀中尚遗留她所赠之物,立时心中剧震,口中惊呼出声!
直到听到对方亦惊呼失声,立时明白她如此小心,来此定是秘而不宣,不欲旁人知晓,与自己突然打个照面,方才有些措手不及。
又见到她眼中浓浓的警惕戒备之意,立时醒悟自己这个样貌,对方从未见过。
为免误会,立时取下脸上面具,在她还未明白为何出现这一幕,空林口中已经以本来声间惊喜道:
“幕姑娘,是我啊!”
听到似曾相识的声音,再加上空林曾经相似的动作,当面解下面具塞入怀中,露出本来略显青涩的俊脸,脸上浮现恍然的微笑,吐气如兰道:
“原来是你啊!”
上下打量了几眼他此时装扮,旋又忍不住问道:“你怎会突然出现在此?”
空林不由挠头一笑道:
“此事说来话长,一时半会说不清!”
复又澄清道:
“不过,事先声明,在下之前可半点没有跟踪幕姑娘的意思!纯属巧遇,巧遇……呵”
幕姑娘不由面露莞尔之色,娇笑道:
“你上次说你叫什么,抱歉我没记住,可否重新介绍一遍!”
望着她犹如百花盛开般的灿烂笑颜,空林定了定神不由心道,你哪里是没记住,而是根本都未问过小弟名字,何来记住一说?
嘴里厚着脸笑道:
“那是在下名字不易记,怨不得幕姑娘,嘿,在下名叫‘空林’,不知姑娘可曾听过?”
在他想来,她在皇城当差没理由未听过自己本名,但是相当意外的,可能她是四大侍卫中唯一一个不关心身外事的人,故而只听她疑惑道:
“咦,难道你的名字很有名,我应该听说过?”
空林哪敢说出实情,忙伸手取出一物,递上扯远道:
“没有的事。对了,这块令牌我一直不知如何还给幕姑娘,今日如此凑巧遇上,正好不若一并还给幕姑娘!
而且上次援手之德,在下一直不知如何报答幕姑娘,在下郑重声明,若是日后有用得着某之处,幕姑娘旦说无妨在下无不从命!”
可奇怪的是,对方并未立时接话,只是双眼望着自己手中令牌怔怔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