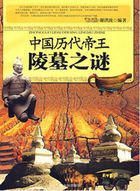惆怅
先在上帝面前,忏悔这如焚的惆怅!
朋友!我就这样称呼你吧。当我第一次在酒楼上逢见你时,我便埋怨命运的欺弄我了。我虽不认识你是谁?我也不要知道你是谁?但我们偶然的遇合,使我在你清澈聪慧的眼里,发现了我久隐胸头的幻影,在你炯炯目光中重新看见了那个捣碎我一切的故人。自从那天你由我身畔经过,自从你一度惊异的注视我之后,我平静冷寂的心波为你汹涌了。朋友!愿你慈悲点远离开我,愿你允许我不再见你,为了你的丰韵,你的眼辉,处处都能撼的我动魄惊心!
这样凄零如焚的心境里,我在这酒店内成了个奇异的来客,这也许就是你怀疑我追究我的缘故吧?为了躲避过去梦影之纠缠,我想不再看见你,但是每次独自踽踽林中归来后,望着故人的遗像,又愿马上看见你,如观黄泉下久矣沉寂消游的音容。因此我才强咽着泪,来到这酒店内狂饮,来到这跳舞厅上跹蹁。明知道这是更深更深的痛苦,不过我不能自禁的沉没了。
你也感到惊奇吗?每天屋角的桌子上,我执着玛瑙杯狂饮,饮醉后我又踱到舞场上去歌舞,一直到灯暗人散,歌暗舞乱,才抱着惆怅和疲倦归来。这自然不是安放心灵的静境,但我为了你,天天来到这里饮一瓶上等的白兰地,希望醉极了能毒死我呢!不过依然是清醒过来了。近来,你似乎感到我的行为奇特吧!你伴着别人跳舞时,目光时时在望着我,想仔细探索我是什么人?怀着什么样心情来到这里痛饮狂舞?唉!这终于是个谜,除了我这一套朴素衣裙苍白容颜外,怕你不能再多知道一点我的心情和形踪吧?
记得那一夜,我独自在游廊上望月沉思:你悄悄立在我身后,当我回到沙发上时,你低着头叹息了一声就走过去了。真值得我注意,这一声哀惨的叹息深入了我的心灵,在如此嘈杂喧嚷,金迷纸醉的地方,无意中会遇见心的创伤的同情。这时音乐正奏着最后的哀调,呜呜咽咽像夜莺悲啼,孤猿长啸,我振了振舞衣,想推门进去参加那欢乐的表演;但哀婉的音乐令我不能自持,后来泪已扑簌簌落满衣襟,我感到极度的痛苦,就是这样热闹的环境中愈衬出我心境的荒凉冷寂。这种回肠荡气的心情,你是注意到了,我走进了大厅时,偷眼看见你在呆呆地望着我,脸上的颜色也十分惨淡;难道说你也是天涯沦落的伤心人吗?不过你的天真烂漫,憨娇活泼的精神,谁信你是人间苦痛中扎挣着的人呢?朋友!我自然祝福你不是那样。更愿你不必注意到我,我只是一个散洒悲哀,布施痛苦的人,在这世界上我无力再承受任何人的同情和怜恤了。我虽希望改换我的环境,忘掉一切,舍弃一切,埋葬一切,但是新的境遇里有时也会回到旧的梦里。依然不能摆脱,件件分明的往事,照样映演着揉碎我的心灵。我已明白了,这是一直和我灵魂殉葬入墓的礼物!
写到这里我心烦乱极了,我走倒在床上休息一会再往下写吧!
这封信未写完我就病了。
朋友!这时我重提起笔来的心情已完全和上边不同了。是忏悔,也是觉悟,我心灵的怒马奔放到前段深潭的山崖时,也该收住了,再前去只有不堪形容的沉落,陷埋了我自己,同时也连累你,我那能这样傻呢!
那天我太醉了,不知不觉晕倒在酒楼上,醒来后睁开眼我睡在软榻上,猛抬头便看你温柔含情的目光,你低低和我说:
“小姐!觉着好点吗?你先喝点解酒的汤。”
我不能拒绝你的好意,我在你手里喝了两口桔子汤,心头清醒了许多,忽然感到不安,便扎挣的坐起来想要走。你忧郁而诚恳的说:
“你能否允许我驾车送你回去么?请你告诉我住在那里?”我拂然的拒绝了你。心中虽然是说不尽的感谢,但我的理智诏示我应该远避你的殷勤,所以我便勉强起身,默无一语的下楼来。店主人招呼我上车时,我还看见你远远站在楼台上望我。唉!朋友!我悔不该来这地方,又留下一个凄惨的回忆;而且给你如此深沉的怀疑和痛苦,我知道忏悔了愿,你忘记我们的遇合并且原谅我难言的哀怀吧!
从前为了你来到这里,如今又为了你离开。我已决定不再住下去了,三天内即航海到南洋一带度漂流的生涯,那里的朋友曾特请去同他们合伙演电影,我自己也很有兴趣,如今又有一个希望在诱惑我做一个悲剧的明星呢!这个事业也许能发挥我满腔凄酸,并给你一个再见我的机会。
今天又到酒店去看你,我独隐帏幕后,灯光辉煌,人影散乱中,看见你穿一件翡翠色的衣服,坐在音乐台畔的沙发上吸着雪茄沉思,朋友!我那时心中痛苦万分,很想揭开幕去向你告别,但是我不能。只有咽着泪默望你说了声:
“朋友!再见。一切命运的安排,原谅我这是偶然。”
醒后的惆怅
深夜梦回的枕上,我常闻到一种飘浮的清香,不是冷艳的梅香,不是清馨的兰香,不是金炉里的檀香,更不是野外雨后的草香。不知它来自何处,去至何方?它们伴着皎月游云而来,随着冷风凄雨而来,无可比拟,凄迷辗转之中,认它为一缕愁丝,认它为几束恋感,是这般悲壮而缠绵。世界既这般空寂,何必追求物象的因果。
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
汝爱我心,我爱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
——楞严经
寂灭的世界里,无大地山河,无恋爱生死,此身既属臭皮囊,此心又何尝有物,因此我常想毁灭生命,锢禁心灵。至少把过去埋了,埋在那苍茫的海心,埋在那崇峻的山峰;在人间永不波荡,永不飘飞;但是失败了,仅仅这一念之差,铸塑成这般罪恶。
当我在长夜漫漫,转侧呜咽之中,我常幻想着那云烟一般的往事,我感到哽酸,轻轻来吻我的是这腔无处挥洒的血泪。
我不能让生命寂灭,更无力制止她的心波澎湃,想到时总觉对不住母亲,离开她五年把自己摧残到这般枯悴。
要写什么呢?生命已消逝的飞掠去了,笔尖逃逸的思绪,何曾是纸上留下的痕迹。母亲!这些话假如你已了解时,我又何必再写呢!只恨这是埋在我心冢里的,在我将要放在玉棺时,把这束心的挥抹请母亲过目。
天辛死以后,我在他尸身前祷告时,一个令我绻恋的梦醒了!我爱梦,我喜欢梦,她是浓雾里阑珊的花枝,她是雪纱轻笼了苹果脸的少女,她如苍海飞溅的浪花,她如归鸿云天里一闪的翅影。因为她既不可捉摸,又不容凝视,那轻渺渺游丝般梦痕,比一切都使人醺醉而迷惘。诗是可以写在纸上的,画是可以绘在纸上的,而梦呢,永远留在我心里。母亲!假如你正在寂寞时候,我告诉你几个奇异的梦。
梦回
这已是午夜人静,我被隔房一阵痛楚的呻吟惊醒!睁开眼时,一盏罩着绿绸的电灯,低低的垂到我床前,闪映着白漆的几椅和镜台。绿绒的窗帏长长的拖到地上;窗台上摆着美人蕉。摆着梅花,摆着水仙,投进我鼻端的也辨不出是那一种花香?墙壁的颜色我写不出,不是深绿,不是浅碧,像春水又像青天,表现出极深的沉静与幽暗。我环顾一周后,不禁哀哀的长叹一声!谁能想到呢!我今夜来到这陌生的室中,睡在这许多僵尸停息过的床上做这惊心的碎梦?谁能想到呢!除了在暗中捉弄我的命运,和能执掌着生机之轮的神。
这时候门轻轻地推开了。进来一个黑衣罩着白坎肩戴着白高冠的女郎,在绿的灯光下照映出她娇嫩的面靥,尤其可爱的是一双黑而且深的眼;她轻盈婀娜的走到我床前。微笑着说:“你醒了!”声音也和她的美丽一样好听!走近了,细看似乎像一个认识的朋友,后来才想到原来像去秋死了的婧姊。不知为什么我很喜欢她;当她把测验口温的表放在我嘴里时,我凝视着她,我是愿意在她依稀仿佛的面容上,认识我不能再见的婧姊呢!
“你还须静养不能多费思想的,今夜要好好的睡一夜:明天也许会好的,你不要焦急!”她的纤纤玉手按着我的右腕,斜着头说这几句话。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她,我只微笑的点点头。她将温度写在我床头的一个表上后,她把我的被又向上拉了拉,把汽炉上的水壶拿过来。她和来时一样又那么轻盈婀娜的去了。电灯依然低低的垂到我床前,窗帏依然长长的拖到地上,室中依然充满了沉静和幽暗。她是谁呢?她不是我的母亲,不是我的姊妹,也不是我的亲戚和朋友,她是陌生的不相识的一个女人;然而她能温慰我服侍我一样她不相识的一个病人。当她走后我似乎惊醒的回忆时,我不知为何又感到一种过后的惆怅,我不幸做了她的伤羊。我合掌谢谢她的来临,我像个小白羊,离群倒卧在黄沙凄迷的荒场,她像月光下的牧羊女郎,抚慰着我的惊魂,吻照着我的创伤,使我由她洁白仁爱的光里,看见了我一切亲爱的人,忘记了我一切的创痛。
我那能睡,我那能睡,心海像狂飙吹拂一样的汹涌不宁;往事前尘,历历在我脑海中映演,我又跌落在过去的梦里沉思。心像焰焰迸射的火山,头上的冰囊也消融了。我按电铃,对面小床上的漱玉醒了,她下床来看我,我悄悄地拉她坐在我床边,我说:“漱妹:你不要睡了,再有两夜你就离开我去了,好不好今夜我俩联床谈心?”漱玉半天也不说话,只不停的按电铃,我默默望着她娇小的背影咽泪!女仆给我换了冰囊后,漱玉又转到我床前去看我刚才的温度;在电灯下呆立了半晌,她才说:“你病未脱险期,要好好静养,不能多费心思多说话,你忘记了刚才看护吩咐你的话吗?”她说话的声音已有点抖颤,而且她的头低低的垂下,我不能再求了。好吧!任我们同在这一室中,为了病把我们分隔的咫尺天涯;临别了,还不能和她联床共话消此长夜,人间真有许多想不到梦不到的缺憾。我们预想要在今夜给漱玉饯最后的别宴,也许这时候正在辉煌的电灯下各抱一壶酒,和泪痛饮,在这凄楚悲壮的别宴上,沉痛着未来而醺醉。那知这一切终于是幻梦,幻梦非实,终于是变,变异非常;谁料到凄哀的别宴,到时候又变出惊人的惨剧!
这间病房中两张铁床上,卧着一个负伤的我,卧着一个临行的她,我们彼此心里都怀有异样的沉思,和悲哀:她是山穷水尽无路可通,还要挣扎着去投奔远道,在这冰天雪地,寒风凄紧时候;要践踏出一条道路,她不管上帝付给的是什么命运?我呢,原只想在尘海奔波中消磨我的岁月和青春,那料到如今又做了十字街头,电车轮下,幸逃残生的负伤者!生和死一刹那间,我真愿晕厥后,再不醒来,因为我是不计较到何种程度才值的死,希望得什么泰山鸿毛一类的虚衔。假如死一定要和我握手,我虽不愿也不能拒绝,我们终日在十字街头往来奔波,活着出门的人,也许死了才抬着回来。这类意外的惨变,我们且不愿它来临,然而也毫无力量可以拒绝它来临。
我今天去学校时,自然料不到今夜睡在医院、而且负了这样沉重的伤。漱玉本是明晨便要离京赴津的,她那能想到在她临行时候,我又遭遇了这样惊人心魂的惨劫?因之我卧在病床上深深地又感到了人生多变,多变之中固然悲惨凄哀,不过有时也能找到一种意想不及的收获。我似乎不怎样关怀我负伤的事,我只回想着自己烟云消散后的旧梦,沉恋着这惊魂乍定,恍非身历的新梦。
漱玉喂我喝了点牛奶后,她无语的又走到她床前去,我望着沉重的双肩长叹!她似乎觉着了。回头向我苦笑着说:“为什么?”我也笑了,我说:“不知道?”她坐在床上,翻看一本书。我知她零乱的心绪,大概她也是不能睡;然而她知我也是不愿意睡,所以她又假睡在床上希望着我静寂中能睡。她也许不知道我已厌弃睡,因为我已厌弃了梦,我不愿入梦,我是怕梦终于又要惊醒!
有时候我曾羡慕过病院生活,我常想有了病住几天医院,梦想着这一定是一个值的描写而别有兴感的环境;但是今夜听见了病人痛楚的呻吟,看见了白衣翩跹的看护,寂静阴惨的病室,凄哀暗淡的灯光时,我更觉的万分悲怆!深深地回忆到往日病院的遗痕,和我心上的残迹,添了些此后离梦更遥的惆怅!而且愿我永远不再踏进这肠断心碎的地方。
心绪万端时,又想到母亲。母亲今夜的梦中,不知我是怎样的入梦?母亲!我对你只好骗你,我那能忍把这些可怕可惊的消息告诉你。为了她我才感谢上苍,今天能在车轮下逃生,剩得这一付残骸安慰我白发皤皤的双亲。为了母亲我才珍视我的身体,虽然这一付腐蚀的残骸,不值爱怜;但是被母亲的爱润泽着的灵魂,应该随着母亲的灵魂而安息,这似乎是暗中的声音常在诏示着我。然而假使我今天真的血迹模糊横卧在车轨上时,我虽不忍抛弃我的双亲也不能。想到此我眼中流下感谢的泪来!
路既未走完,我也只好背起行囊再往前去,不管前途是荆棘是崎岖,披星戴月的向前去。想到这里我心才平静下,漱玉蜷伏在床上也许已经入了梦,我侧着身子也想睡去,但是脑部总是迸发出火星,令我不能冷静。
夜更静了,绿帏后似乎映着天空中一弯残月。我由病床上起来,轻轻地下了床,走到窗前把绿帏拉开,惨白的月光投射进来,我俯视月光照着的楼下,在一个圆形的小松环围的花圃里中央,立着一座大理石的雕像,似乎是一个俯着合掌的女神正在默祷着!这刹那间我心海由汹涌而归于枯寂,我抬头望着天上残月和疏星,低头我又看在凄寒冷静的月夜里,那一个没有性灵的石像;我痴倚在窗前沉思,想到天明后即撒手南下的漱玉,又想到从死神羽翼下逃回的残躯,我心中觉着辛酸万分,眼泪一滴一滴流到炎热的腮上。我回到床前,月光正投射到漱玉的身上,窗帏仍开青,睁眼可以看见一弯银月,和闪烁的繁星。
恐怖
父亲的生命是秋深了。如一片黄叶系在树梢。十年,五年,三年以后,明天或许就在今晚都说不定。因之,无论大家怎样欢欣团聚的时候,一种可怕的暗影,或悄悄飞到我们眼前。就是父亲的喜欢时,也会忽然的感叹起来!尤其是我,脆弱的神经,有时想的很久远很恐怖。父亲在我家里是和平之神。假如他有一天离开人间,那我和母亲就沉沦在更深的苦痛中了。维持我今日家庭的绳索是父亲,绳索断了,那自然是一个莫测高深的陨坠了。
逆料多少年大家庭中压伏的积怨,总会爆发的。这爆发后毁灭一切的火星落下时,怕懦弱的母亲是不能逃免!我爱护她,自然受同样的创缚,处同样的命运是无庸疑议了。那时人们一切的矫饰虚伪,都会褪落的;心底的刺也许就变成弦上的箭了。
多少隐恨说不出在心头。每年归来,深夜人静后,母亲在我枕畔偷偷流泪!我无力挽回她过去铸错的命运,只有精神上同受这无期的刑罚。有时我虽离开母亲,凄冷风雨之夜,灯残梦醒之时,耳中犹仿佛听见枕畔有母亲滴泪的声音。不过我还很欣慰父亲的健在,一切都能给她作防御的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