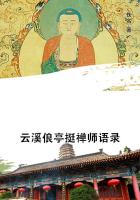郑彦搂了邓华六年,现如今只能在沙漠中独行,任干渴,落寞恣意肆虐,新婚那晚,邓华紧张而又羞涩地低喃,来生,一定给你第一次。郑彦不停地微笑,我死也可以闭眼了。
音消舞止,俩人被潮水退至广场边缘,郑彦依旧左顾右盼。女人问,坏男人一直在找人?郑彦点了点头,苦笑道,坏男人在找老婆,失联已三个月。你确定她在这里?女人问。现在不敢确定,失联前的最后一通电话是从这里打出去的,她说在这里的某个电子厂打工。郑彦又叹了口气。
女人说,你老婆叫什么名?或许我刚好认识呢!邓华,广谱人。郑彦说道。女人思索良久,摇了摇头,长得漂亮吗?兴许在别的电子厂吧,也有可能已经离开了这里,三个月的时间不长也不短,在深圳,什么事情都能发生。
比你漂亮!郑彦的眼神仿佛一把尺子,重新将女人丈量了一番,谑笑着说。女人白了郑彦一眼,纤腰半扭,语带风情地说,打击人,伤人自尊,还没人说我长得不好看的。既然你老婆是漂亮女人,那就更难说了,在这个纸醉金迷的繁华都市,没有谁能抵挡无处不在的诱惑,这里,最奢侈的不是物质,而是情感。女人顿了顿,嬉笑着探身凑到郑彦的耳边软声说道,说不定……你老婆这个时候在别处逍遥呢!
郑彦双眉一挑,正待翻脸。就在这时,异况突生,先是一声沉闷如败草坠地的响动,接着从不远处的楼栋里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声,声音凄厉,似乎惊恐到了极致,啊……!阿华!
有人跳楼了!快来人啊!阿华跳楼了!
广场的人群呼呼啦啦地涌向出事地点,郑彦被尖叫声惊得魂飞魄散,瞬间满头大汗,脑内心里皮肤里的血管统统爆裂,血翻泪涌,他顾不得其它,一把将未燃尽的烟头死死地攥在手中,心头恨恨地想,邓华,你要是死了,我和你共赴来生!邓华!他大吼一声,像一头发怒的豹子,两步作三步地飞奔出事点,出事地点离广场不远,郑彦却像跑了几亿光年那么长那么远。
当郑彦嘶声力竭地赶到那儿时,已经围了满满一圈人,他发疯地使劲拨开人群,泪眼婆娑,人群自然而然为他打开一道口子,有几个人围趴在边上已经泣不成声,楼栋边,青色路砖铺地,数道手电筒的光柱照在一位身穿黑色连衣裙的女子身上,现场惨不忍睹,,血腥味扑鼻,女子的身体无骨般软塌塌的俯趴在地,红的白的流了一地,一只胳膊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角度扭曲着,人是短发,脑袋已经变了型,看着不像邓华。郑彦依然不敢确定,他泪眼婆娑,像筛糠般抖着身子,颤颤巍巍地向有手电的人拿过手电,誓要看个明白,是不是邓华,看了才能确定。
郑彦持着手电,正要上前,却被伸过来的另外一支手紧紧攥住了胳膊,郑彦泪眼朦胧的发觉是那身着旗袍的女人,女人面色苍白,紧紧抿着嘴唇,冲着他直摇头。郑彦不管不顾,拼了老命挣开旗袍女人的手,手持手电,牙关打着颤,在断断续续邓……华……邓华的轻呼声中抵近坠楼女子,绕到可以直视女子面部的方向,郑彦用手电照在女子脸上……一张本该娇艳若花的脸变得面目全非,七窍流血,脸颊扁平,一粒眼球蹦出了眼眶,终于可以确认不是邓华了,郑彦仿佛失了魂般任手电筒从手中滑落,或者源于对生命终结的惊恐,或许源于确认不是邓华的庆幸,郑彦反而嚎啕大哭起来,踉踉跄跄挤在围观人群中,不断拉着别人的手问,认识邓华吗?认识邓华吗?在不停的摆头不语中,郑彦赫然瞬间苍老,佝偻着身躯走出人群,身影萧瑟。他跪倒在广场的地上悲戚不已,哭完又笑,笑完又哭,不是邓华,不是邓华,哈哈!状若癫狂。
广场上没了人,连路灯都不正常起来,明明灭灭,郑彦的哭笑声混合着出事地点的呼天抢地的哀嚎声,在深圳的夜空久久回荡,像一曲丧宴悲歌。
良久,女人走到郑彦跟前发出一声悲悯地哀叹,站着身子轻轻捧起郑彦的头,将它缓缓靠在她温软而平实的小腹上,凭它在肺腑里抽噎,静静流淌出压抑已久的悲凉。
突然有了依靠,郑彦脑袋里轰然碎响,仿佛坚持了数年的某根弦突然崩裂,心里乱得像塞了一大麻袋麻绳,他的头离开女人的小腹,抬头望着女人,喉结涌动,眸子里似乎有火苗在跳动,脸颊上挂着泪水。
女人轻轻摩挲着郑彦的脸,喃声道,陪我,我怕。
新秀村的某栋出租屋里,房间很大,也很明亮,靠窗的墙角竖放着一个红色行李箱。房间整洁,床上很乱。被子被揉成了麻花状,半截斜斜地耷在地上,房间里有一股浓烈的暧昧气息,地上有两团卫生纸,皱巴巴脏兮兮地滚落在床脚边上,不知道檫过什么东西,女人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棉质吊带睡裙坐在床上,睡裙明显有些皱褶,一条白皙的玉腿挂在床沿,裙里的山水隐约可见。女人的手握着床下男人的手,男人低着头在把玩写字台上的粉色Zippo。
女人笑嘻嘻地问,好久没做了吧?一触即溃耶!哎,坏男人,这样做可没意思了,真不如做点别的,刚把人家的情绪调动起来就没了!这话要是说的别人,这人肯定会羞愧不已,几欲自杀。
这人不是别人,是郑彦,他没说话,偏头邪恶地望了女人一眼,说,等着吧。
女人突然觉得嗓子里渴得要命,她侧着身子用另一只手端起写字台上的塑料水壶,就着壶口仰头灌下,秀发散乱垂落,纤脖欣长,凸凹有致的躯体隐藏在睡裙下更显得性感适从。
郑彦鼻血被引动,他转身拿掉女人嘴上的水壶……
郑彦头一次感受到死亡离他这么近,心头的悲凉在消失的一瞬间就选择了与死亡相近的抵死缠绵,他如同在洪水中抱紧了一棵树,溺水时抓住一根救命草。
墙上的影子纠结在一起,像两条垂危的鱼。因为垂危,所以挣扎,所以挣扎得如鼓点般促弹。
房间了盛开了一条迷人的河流,河流的四周长满水草,芳香四溢,一只鸟停在河塘边,看样子是迷了路,俯在芳香丛中渴望睡去。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郑彦被悬在半空,上下不得,他恨不得就此瘫软在床,化做一缕青烟消散,直到死无葬身之地。
女人看似张扬,却不爱在巅峰中尖叫挣扎,她香汗淋漓地搂着郑彦,用飘忽的语调呢喃,我死了。
窗外月光如水,风声阵阵,悬浮在半空的郑彦低吼了一声“邓华!”才最终下了地,与女人一起赴了死。欲望总与死亡相生相伴,有的人喜欢在风头浪尖挣扎,有的人坠入尘盛开着花。
他一直认为,爱是从床上延伸的。现在终于明悟,即使没有爱,故事也能从床上延伸,他想,如果有一天死了,不是因为爱就是因为床,他真想在这梦幻的世界里慢慢死去,什么地方也不要去,什么事情也不用想,就这样停止呼吸,停止心跳,最后腐烂,化为尘埃,被风吸收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