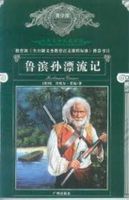当天中午十二点,四同他亲爸带着四同他亲妈到了南京军区总院特护病房,四同他亲妈一看见四同,就一下子扑了过去:“四同,我的儿,你怎么了?他们骗了我一个多月,说你去国外谈生意了,原来你一直在医院里躺着啊?”
四同他后妈走过来,好心相劝:“四同他妈,你心脏不好,不要太过伤心了,孩子已经这样了,哭也没用,把身体哭坏了,还要人照顾。”
四同他亲妈想想还是心酸:“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不心疼谁心疼啊?四同,你醒醒,妈来看你了。”
四同他亲爸站在一边,不说话。他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再流的话,就是血了。病房里,四同他亲妈一直在伤心地哭泣。
四同他亲妈一边哭,一边去摸四同的脸,摸着摸着,感觉自己的手潮湿了:“四同他爸,四同流泪了,你们快过来看。”
两个人一起围了过来,四同确实在流泪。他的眼角挂着两滴泪水,一直流过太阳穴,落在枕头上。
四同他亲妈抱着四同的头,放在自己的手里:“四同,妈真的不忍心看着你这样,早知道你这样了,妈应该过来陪你的。明天开始,妈天天过来陪你,好吗?”
四同他亲爸看着四同他亲妈伤心欲绝的样子,忍不住说:“四同他妈,你身体也不好,偶尔过来看看就可以了,这里有我们,还有曼尼和立恒照顾。”
四同他亲妈点了点头:“真是对不住你们,自己的儿子要你们大家照顾。我现在身体确实不大好,心脏动了大手术,每天靠药物维持心脏的功能。我今天人已经来了,就多陪陪四同吧。”
四同他亲爸和后妈也不再坚持,让四同他亲妈留在四同的身边。当天晚上八点,刘立恒准点来接夜班,看见病房里多了一个陌生人,心里立即出来一个问号:“这是四同的哪个妈?”
四同他亲爸看见刘立恒,主动为他和四同他亲妈介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四同的亲妈,这位是曼尼的男朋友立恒。”
刘立恒主动和四同他亲妈打招呼:“伯母。”
四同他亲妈点了点头:“这一个多月来,辛苦你和曼尼了,没有想到四同给你们带来这么多麻烦,太谢谢了。”
刘立恒接着说:“伯母,应该的,四同是曼尼的哥哥,也是我的哥哥,照顾他是我们应该做的。”
四同他亲爸看时间不早了,对刘立恒说:“立恒,四同丢给你了,四同他亲妈身体不好,今天在这里大半天了,我们先把她送回去,明天再过来。”
刘立恒“嗯”了一声:“好的,叔叔、阿姨、伯母,你们慢走。”
刘立恒说完,把三个长辈送到病房门外,看着他们离开后,才回到病房。今天第一次见到四同他亲妈,感觉还好,也没有像曼尼说的那么恐怖。
刘立恒掀开被子,看了看四同的大腿根部,给他换了尿袋,接着打了一盆热水,给他擦了擦身子。
这些日子,对刘立恒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北京之行后,他的生活似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让刘立恒最难以理解的是,他竟然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花慕容的生活中,而且具有蔓延之势。
首先,刘立恒和花慕容的小姑子张曼尼订了婚,接着,担纲起了照顾她爱人四同的重任,现在,又要做她儿子的姑爷了。
短短几个月时间,刘立恒的生活整个倒过来了。北京之行,不仅没有让他远离花慕容,反而让他更加快速地走近她。
刘立恒不敢相信,难道冥冥之中有命运之手在安排?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从开始到结束,难道都是宿命的终结?
刘立恒不相信命,但是,相信缘分。缘分不一定就是婚姻,它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像藕断丝连一样的东西,说不清道不明。
四同很安静,这个男人很乖,曾经让刘立恒羡慕不已,醋意非常多。现在,四同每天躺在他的面前,刘立恒陪着他说话,为他放音乐,和他在一起消磨时间。
换成其他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的一种关系。刘立恒摇了摇头,走过去,把四同的一条腿轻轻提了起来,然后开始做拉伸运动。
刘立恒做完一条腿,再换一条腿。做完一个胳膊,再换一个胳膊。全部活动关节的项目做完后,再放音乐。
现在,刘立恒唯一的想法是四同快点醒过来。今天晚上,张曼尼给他发了一条短信,说花慕容上午剖腹产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儿子需要爸爸,老婆需要老公,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放音乐的时候,刘立恒一直注意四同的反应。音乐比较和缓,像小河流水一样,四同的神情很安静,听音乐的时候没有什么变化。
刘立恒换了一支曲子,四同还是没有变化。刘立恒有点纳闷,他不知道四同原来喜欢什么曲子,对什么曲子最有感觉?
刘立恒想找一支曲子,刺激四同心灵的,能够引起四同灵魂共鸣的,这样的曲子,必定会触动四同的深层记忆,让他早日醒来。
刘立恒搜肠刮肚,这样的曲子太多了,而且每个人喜欢的旋律不一样,谁知道四同喜欢什么样的旋律?
刘立恒灵机一动,也许,只有花慕容最清楚四同喜欢什么样的曲子和什么样的音乐旋律。
不过,花慕容今天刚刚剖腹产,身体还没有恢复,还是不打扰她了。刘立恒继续换了一首音乐,听着听着自己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已经半夜了,刘立恒去浴室冲了一回凉。回来后,给四同翻了翻身,活动了一下四同的肌肉。
其实,对四同来说,已经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了。白天对他来说,是黑夜,黑夜对他来说,同样是白天。
四同的眼睛是没有光度的,像瞎子一样,不管谁靠近他,他都视而不见。在四同的眼里,世界是静止不动的,是永恒不变的。
人活到这个境界,是四同不曾预料到的。原来的世界多精彩,可是已经不属于四同了。
次日上午,我被一阵钻心的疼痛惊醒了。剖腹产后,我的肚子一直胀气,连半个屁也没有放出来。气流来回在肠子里转,积聚在肚子的最尖端,然后再慢慢回到肛区。
气流形成了恶性循环,一旦到了肚子的最尖端,我就疼得要死,恨不得死了痛快。等到气流回到肛区,我又觉得活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我就被气流来来回回地这么折磨着。
我后妈看见我疼得受不了,让月子保姆去市妇幼门口找店家做萝卜汤给我喝,喝完萝卜汤,肚子里的气鼓得更厉害了,简直要了我的命。
他奶奶的,平时想放屁很容易,要几个憋足劲儿就能来几个。现在,要一个屁竟然这么难!整整一天一夜没有通气了,我感觉肠子要爆炸了。
中午,继续吃萝卜汤,接着吃鸡蛋银丝面。到了下午,躺在床上,终于放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响屁。
我后妈看着我,喜滋滋地笑:“慕容,终于通气了?”
我点了点头,一脸的轻松,这个屁来得太不容易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妈,萝卜汤救了我的命,这是救命汤啊!”
我后妈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宝宝的出生证怎么还没有送来?我去护士站问问医生。”
我拉了拉后妈的手:“妈,出生证在我枕头底下,昨天你在睡觉,护士送过来的,我忘记和你说了。”
我后妈“嗯”了一声:“慕容,四同他亲爸昨天丢话给我了,说孙子姓花,名字让你找大师起。”
我心头一热:“真的,四同他亲爸和他亲妈意见一致了?”
我后妈摇了摇头:“哪里?你推出手术室后,老两口子从走廊一直吵到病房。”
我笑了笑:“他们是不是在抢儿子的出生证?”
我后妈点点头:“是的。”
说完,后妈把出生证从枕头底下拿了出来:“妈先给你保管,和家里的户口簿放在一起,等你报户口的时候,再拿出来给你。”
我后妈把出生证收起来后,我从枕头底下摸出了手机,向张筠土大师报喜:“张大师,我儿子7月19日上午8点58分出生于南京市妇幼,麻烦您给起个好名,儿子跟我姓:花。”
张筠土大师很快回复我:“嗯,恭喜你做妈妈了,我最近两天就给你做起名配置计划书,完成后发你邮箱。”
我飞过去一条:“谢谢张大师,我等你消息。”
儿子的姓名尘埃落定,我的心里就只剩下四同了。下午,护士把儿子抱进了病房,儿子的小手和小脚上,各挂了一个粉红色的扣环,上面写着床号和我的姓名。
儿子睡在小床里,很乖巧。我试着坐起来,在月子保姆的帮助下,慢慢下了床。我的双手托着肚子,走到儿子的身边。
儿子的鼻子长得有点像四同,嘴巴有点像我,脸部轮廓也像四同。看到熟睡的儿子微笑的样子,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初为人母,第一次觉得做父母的不容易。一个娃儿,从十月怀胎,到婴儿,到少年,到青年,在所有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吃尽了辛苦,到头来还不图儿女的一丝回报,只要儿女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就心满意足了。
我看着儿子,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粉嫩的小脸。儿子皱了皱眉头,眨了眨眼睛,似乎很不高兴,仿佛我惊动了他的美梦。
我接着又摸了摸儿子的小手,他立即把五个手指缩了回去,像河蚌一样,防卫本领很强。
最后,我抓了抓儿子的小脚丫,他蹬了两下。这个动作的伸缩频率和怀孕时的胎动一样,太像打太极拳了。
这时,病房的门被推开了,一束鲜花从门外伸了进来。我转过头去,看不见来人的脸。
来人一直把花举在自己的脸部,挺着微微隆起的大肚子,慢慢地朝我这边走来。我疑惑地看着她,不知道来人是谁,也看不清是哪个亲戚朋友或同事。
来人终于走到了我的面前,突然,她把花拿了下来,冲我一笑:“我做干妈了,是不是?”
我上下一打量,忍不住哈哈大笑:“死丁克安京宁,你怎么来了,我也没有发信息通知你!”
安京宁鬼鬼地看着我:“你不告诉我,我就没办法知道了?”
安京宁说完,从小包里拿出一个大红包,走到儿子的小床边:“来,干儿子,叫干妈,干妈给你带见面礼来了。”
儿子听见说话声,立即睁开了眼睛,看了看安京宁。月子保姆拿走了安京宁手里的鲜花,放在床头柜上。
我后妈在一边看着外孙子,说:“乖孙孙,你干妈来看你了,把眼睛睁开了是吧,你是见钱眼开了,是不是啊,快谢谢干妈。”
安京宁哈哈大笑:“这小子鬼精,见钱还真把眼睛睁开了。呵呵,不谢不谢。”
看着安京宁显怀的肚子,我招呼她坐了下来:“告别丁克族了?几时怀孕的,也不来个电话报喜?”
安京宁傻傻地笑:“上次和你电话后,我就决定造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