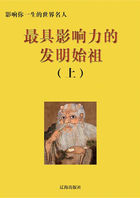“觉得好些了么?”
觉得好些了么。
这几个字,蔷薇后来也常常会问自己的病人。
蹇骞人医术精妙却脾气古怪,询问病人时经常用的是‘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吧’这种话,近墨者黑,连带着几个师姐也几乎是一样的问诊风格:
‘叫什么叫,死了全家的也未见有你断个胳膊叫的这么痛!’
“若是鬼哭狼嚎停不了,本姑娘可就直接拿金针扎哑你!”
......
而这些还算是比较好的部分。
唯有蔷薇,虽然个性之中也颇藏棱角,技艺初成为人问诊时却温温柔柔,真好似个悲悯众生的女菩萨一般。蹇骞人为此还大发过脾气,赌咒发誓说自己细心调教十三年,怎么调教出这么个不肖之徒来!染上了俞清和的虚伪嘴脸,有损自己鬼医人的英名。
师父说的俞清河是悲流刹寒凉派医祖,她自己,则是五术论医的创始人。悲流刹医道昌盛,系分七派,各有推崇。蔷薇所在这一派论走偏锋,收徒既严,又只收女弟子,相较之下,倒是最式微的一脉。
其实蔷薇入门既晚,又是年龄最小的弟子,学习之时也并未过多接触外人,故而也并未深究师傅师姐问诊之礼有何不妥,直到她十二岁那年,随师姐苏绸外诊,那一次,是为一个名叫颜烟的女孩子瞧病。
悲流刹的石阶又窄又长,蔷薇提着沉重的药箱亦步亦趋的跟在师姐身后。
那时她还脸蛋圆圆,眉目未展,梳着稚气未脱的发髻,额前盖着齐齐厚厚的刘海,冬日里衣衫厚重,她滚滚团团,像只小皮球艰难地拾级而上。
她走得欲哭无泪,手臂发酸,又穿过长长的回廊,步之尽头,便终于来到那女孩子候诊的地方。
帷帘低垂,榻中静卧着一少女,眼眶微红,肤色胜雪,即便在病中,一身素白,她依然很美,柔弱得直教人想去保护她。
少女床榻边立着个黑衣少年,身形笔直,背着一把长剑,似也是风尘仆仆而来,靴边还带着泥,他距床榻一步之遥地站着,不退后,也不敢上前。
蔷薇彼时正跟着师父研习骨相,抬眼见他侧脸,棱角已现,鼻骨高挺,下颌曲线也很美。
她不自觉拿这少年的侧脸比照师父给自己画的图样。
他的发缘点、眉间点、鼻尖点、颏前点真的是一道圆形轨迹!蔷薇望着他侧脸出了神,心说世间还真有这样完美的骨相,该看一看正脸啊......
她这样想着,那黑衣少年便当真转过头来。
她一惊,吓了一跳,忙低下头去看药箱,心中懊恼是否方才自己看人家看得肆无忌惮被发现。
也当然没来得及好好端详他正脸是否依然比例完美,低头的瞬间只捕捉到他的眼睛,黑亮黑亮的。
苏绸师姐当时的诊断是‘急痛迷心,气血亏柔。’只说不碍事,提笔开药方命蔷薇抓药煎煮,便赶场子似的去了另一处。
嘱咐蔷薇好生等她,等会儿来接。
蔷薇当然依照,配好药材,拎着砂锅,一个人窝在厨下生火煎药,煎好药端进屋来。
那少年起身来接,蔷薇垂眼看着眼帘下捧着药碗的那双手——那双手对于一个少年来说,粗糙了些,他手很长,关节分明,虎口处磨了厚厚的茧,手背上也尽是干纹。蔷薇怕刚煎的药烫还特别端了托盘进来,他却徒手接过捧着。
这人手掌该有多厚呢?
他轻声叫她起身吃药,那病中的少女拉下被子来,眼眶却又红了一圈,她不出声也不起身,只望着他。
少年立无所措,看向蔷薇,“小妹妹,麻烦你扶她起来好吗?”
他连说话声音都极中听,低沉有厚度,入耳的感觉好似温了口酒在喉间,再缓缓咽下。
蔷薇点点头,走到床边伸手去扶那少女起来,少女一见她过来,却陡得由悲转怒,一把拉过被子转过身去,“我不要别人碰我!你走开!”她语气极嫌恶的,蔷薇尴尬地还伸着胖乎乎的小手,心上一凉,收了回来,退后两步,拉了拉有点短的衣袖。
“颜烟!这是做什么!起来道歉!”
少年也动了怒,把药碗扔在床边的小几上,力道掌握的极好,一滴都没洒出来。
那少女在被子中却哭了开来,“欺负我!连你也来欺负我!见我没了母亲!都来......都来......”她哽哽咽咽,说不下去,蔷薇听到‘没了母亲’这四字,心中一酸,只觉这少女无理取闹也带着几分可怜。
少年叹了口气,伸出大手去拍了拍那被子,“没人欺负你,你没了妈妈,还有我,我会保护你的。”
少女掀开被子,紧紧抱住那少年的腰身,哭得梨花带雨,“高修哥哥!我没有妈妈了!没有妈妈了!”
她哭得好伤心。少年轻轻拍着她的后背,轻声安抚着,终于劝得她吃了药。
蔷薇远远站着看着他二人,看着那黑衣少年坐在床边一勺一勺地喂她吃药,看着他用手指拂去溅在她脸上的药汁,听他问她——
“觉得好些了么?”
觉得好些了么?
就那一刻,从来没有那样的一刻,蔷薇觉得自己如此粗糙,好像突然间脸上爬满了络腮胡。
她只想躲开这感觉,躲得越远越好。
怔仲间,有人敲门,师姐苏绸的脸探了进来,一见蔷薇在墙角站着,“薇薇,走了,药都吃到嘴里了还不撤,还指望多给你点诊金吗!”
她伸出手来,蔷薇如梦方醒,答应了一声便收拾药箱。黑衣少年放下药碗起身至门口道谢,苏绸一牵蔷薇小手,点了点头,也就走了。
那条回廊还是很长,蔷薇走到快一半的时候,偷偷回过头去望了一眼,只见他还在门口立着,身形笔直,见她回头,竟然还向她挥了挥手。
她回望一眼还是转回头来,也并没受什么委屈,眼眶却发酸。
只这一面牵扯出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蔷薇放任它在心中生根发芽。她并无奢望,亦无野心,只是有时静坐堂前温书试药,眼前便会闪现那少年的侧脸,挥之不去,忘之难平。
后来她听师姐说起,那日名叫颜烟的少女是大将军嫡女,她母亲过世后不久,便被父亲接回府中调养。
倏忽光阴易过,她孤孤单单在牵机阁中长大,几个师姐医业已成,纷纷下山,自立匾额。唯有苏绸师姐,一直留在师父身边。蹇骞人在蔷薇入门之后,便再不收弟子,只说自己心力不足,也少了与别派一争高下的机心,只喝茶下棋,种药研经,督促两个弟子课业,其他一概不管。
师父带她下山那一年,她十五岁。
那年悲流刹建成百年,又逢论剑之期,听说一剑封冠的是个讲武堂的黑衣少年,名叫高修,大将军亲赏佩剑,一时风光无两。
她很想亲身去看,师父却催她动身。
蔷薇一想也罢,自己何苦去凑那热闹,心中酸涩得像是一夕之间又回到了十二岁那年。
人家少年情侣,登对非常,将军今日赏佩剑,明日便该嫁女儿,她缘何生这无妄之心。
蔷薇收拾行囊随师父远行游医,山高水远,一去三年。
再回夜墨,她独自一人,师父寄情山水,云游州外,不肯归来。牵机阁前草木已深,只有苏绸师姐言笑依旧,站在门前迎接她。
那年蔷薇十八岁,按着阎浮洲的习俗,已到了嫁人成亲的年纪。她心中无想,左右又无人催促,也就这么耽搁下来,终日埋首案前整理三年来的所见所感,药稿医经。
悲流刹繁盛更胜往昔,一年春试,便又有新人入山。
蔷薇提着药箱自己出诊,走在山路上听着身后两个女孩子窃窃私语地讨论:
“讲武堂中要说出色当然还是顾师兄啊!他可是今年论剑第一。”女孩子无限钦羡。
“没什么了不起,他也被人打败过。我听说三年前的论剑大会,哦,就是咱们悲流刹百年盛典,魁首可是别人,叫高修!剑术登峰造极啊!我张师兄亲眼见过,叹为观止!”
“姓高?说不定是宗主的儿子!那剑术当然好!”
“呸呸!瞎说什么!宗主儿子早夭!你来的晚不知道,宗主如今膝下无子,悲流刹五代啊!如今,啧啧!可不许胡说这个啊!让别人听到你就——”另一个作势吓唬她。
“那还不简单!宗主有个那么年轻貌美的夫人,赶紧生一个呀!”
“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个呢!”这女孩子四处张望了一眼,一看左右没人,只有前面老远有个红衣黑发的姐姐,才放了心,压低了声音,“你还不知道呀,宗主这夫人娶了五六年啦!偏偏生不出孩子来,别说儿子了,膝下连个女孩都没有,谁想年初却怀了孕——”
“那不挺好!”
“挺好什么呀!那段时间宗主压根就没在碧离山上!”
“吓!”
“重点还不是这!记得方才我同你说的那三年前的论剑公子?”
“高什么来着?高修?”
“就是他!你猜怎么着?宗主夫人一口咬定,高修包藏祸心,染指于她,肚中的孩子就是高修玷污她的明证!夫人还——”
“胡说八道!”
两人俱均一惊,抬头看去,可不正是方才走在前头的红衣姐姐,凤眼生威,横眉冷对,那张完美无瑕的脸上,隐隐压着风雨欲来的怒容。
两个女孩子对视一眼,生怕惹祸上身,忙不迭地原路跑了。
蔷薇心中生乱,一念两人方才所说更是天旋地转,竟然转身向那鬼见愁讲武堂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