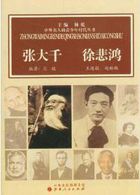一
阴风习习,一晚上死了好几个人,邵家沟是给阴魂缠住了,连猪、鸡、狗都没有了往日的欢实,尤其是猪,哼哼叽叽的,不拿好眼色看人,作出找杀的样子给人看,就算是有热风刮到人脸上,感觉也是凉,死冷死冷的。
九月九日,后生们把当胡子的约定暂时搁住,但见识过胡子的威风,心里还是痒痒的,摩拳擦掌,也要做出胡子的样儿来,当然也把对胡子们的仇恨记下了,尤其祥子,把仇恨当成大牙打碎后咽进肚里,再吐出来,再咽进去,咯得心里一阵阵绞痛,思谋着要给秀娟报仇的,一时又不知找谁。
黑黑的夜里,那一枪究竟是谁打的,哪里看得清,就想起于家洼,人是死在于四虎的马背上,虽说于四虎死了,到底邵玉娴还在胡子窝里,可是邵家沟的闺女哩。
就商量着安葬的事,邵二狗这天显得格外勤快,早早就扛起铁锨跟着广贤还有其他几个人到山上挖坑,他是要躲开抬死尸的活计,怕沾染上死人的晦气。广贤简单地给看了一下坟址,都是横事死的人,离村子不要太近,地势要背风向阳,风水要适当,这样死人才会安稳地睡在地下,而且地方又不能让孩伢们轻易寻得见,以免不知深浅地疯跑,把阴魂带回家,还不得迷糊活人呀。
邵二狗是按照广贤指引的地方挖下第一锨土的,土刚扬起来,冷不丁看见眼前不远处,一只蟾蜍浑身的疙瘩,正瞪着眼睛望他。邵二狗啊地叫了一声,简直要昏厥过去,双手哆嗦着不敢再挖土。广贤转向邵二狗,说:“真看不出,这儿还真是处风水宝地呢,这是金蟾子呀,有吉祥之物守着,肯定是好风水,二狗侄你别怕,赶紧着挖土。”
一股风顺着山坡刮,把一小块纸刮过来,是谁家上坟烧过的阴纸,正挂在邵二狗的脖子处,呵呵呵地响,像鬼在笑。邵二狗急忙把纸摘下,纸放在手上,还是不停地动,拿小手拍打邵二狗。邵二狗有说不出的惊惧,看看广贤,说:“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广贤叔,你说是不是阴魂不肯老实地走呀。”把手中的纸举给广贤看,广贤心里也不托底,定定地看着邵二狗的手,轻声叫:“是满斗吗,你不愿意走我知道,可阴间也有好闺女哩,你若相中了谁家的,就知会我一声,我帮你张罗着娶阴亲哩。”
无人应答,邵二狗手中的纸却不动了,广贤是信这些怪事的,东山根人们取土盖房抹墙,挖出一个坑,雨水多时就成了水泡子,里面死了留换,他弟弟留代老说哥在叫他,在阴世上没有伴哩,就躲了大人,到水泡子玩,后来也死在那儿,还不是留换的魂儿勾去的。后来水泡子给村里人做了大粪坑,把猪、鸭、鹅都赶去洗澡,又把死老鼠、荆条往里扔,要赶走留换的冤魂,别再拖拽别人,孩伢子们嫌臭不去了,可说也怪,过不多久水泡子就干了,除了下雨天还能存点水,平时就是个空地。满斗死前找广贤掐算事,说这些日子总是心神不定的,老想着找什么事做做,心里憋闷,让广贤给看看到底是咋的了。满斗坐在炕边上,广贤坐在炕里,找出三枚铜钱,正要给起卦,不经意地抬起头,就看见满斗正在院里给小猪抓痒,还摸猪的奶,可满斗分明就坐在炕里。广贤猜着如果不是自己眼花,满斗就是灵魂出窍了,卦没有起,就告诉满斗阳世上的寿可能不多了,这不就应验了,满斗死时躺在街上,小猪还去拱他的脸,是恨他连猪的奶子也摸么。现在,念叨两句纸就不动了,说不定真的是满斗死得不甘心,阴间没有女人伴着,想女人哩。
广贤神情庄重,从邵二狗的手里接过那片纸,低低地说:“满斗,我知道真的是你哩,你等着,我答应的事是要给你办的呀。”把手中的纸向天上郑重其事地举了举,随手撒出去,让那纸做了信使,给满斗传话。广贤晓得,神祗并非高居天上或隐于地下,是会溶于自然万物,在世间游走的,满斗的灵魂也不例外,他盯着飘去的纸,让纸做了坐标,指出坟地的穴眼所在,要在那个方向立下门户的。
邵二狗一直看着广贤做完这一切,内心里七上八下,紧张成一团。一声尖锐的鸟鸣,飞起一只小巧的鸟,纸已经落了地,广贤追过去,立即跪下磕头,脸颊贴上冰凉的黄土,默默祷告所有死去的灵魂,保佑邵家沟的水土安生,保佑全村人安好。邵二狗已再没有了挖坟坑的勇气,捂着肚子滚倒在地上,冷汗从头顶冒出来。
广贤惊愕,忙过来问:“你是怎么了,是冲撞了鬼魂么?”
邵二狗的冷汗流得更多,边滚边叫:“不中了,肚子痛得厉害,我得先回。”
广贤不好勉强,只好让他先回,回头指挥别人继续挖土坑。从坟地处往回走,越过一个土坎,走一段长长的坡道,翻过山梁,上到这边的坡地里,那里有一条下大雨时拦截洪水的堤坝,堤坝有半人高,形成人为的土坎,再过去就是通往邵家沟的小路了。邵二狗心里有事,总觉得身后有小鬼跟着,更怕满斗的魂追上他,只顾低着头走路,不顾抬起头来看道,走得急慌慌的,路“嗖嗖嗖”地往身后飞跑,太阳也跟着快步走,刚越过堤坝,忽然,邵二狗一个前趴跌在地上,正晕头晕脑,身后传来“哎哟”一声女人的尖叫。
原来眼看着就要秋收,地里的粮食打得少,没有了粮,少不得吃些葱皮、树叶添补的。张寡妇心里着急,更担心田地里着了贼,把不多的粮食再愉去些,就一早上来地里看秋。走到堤坝这儿,觉得有泡尿憋得慌,就蹲在下面解手,脑袋露出坝沿,看迷迷离离的阳光下,草儿们低头低脑,俯首贴耳,跟田野说悄悄话,远远望见有个人影正往这边急走,害怕给人看见怪羞人的,就把头缩回去,听声音是近了,解完了手也不好意思起来,就继续蹲着,偏偏邵二狗要走几步近道,不顺着堤坝的豁口处过去,从上边往下一跳,一下子把张寡妇扑倒在地上,张寡妇这一惊吓非同小可,有一阵子竟吓得说不出话来。
更惊怕的是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的邵二狗,人倒下了,手捂在张寡妇的腿裆处,拇指就伸进女人热乎乎刚给尿冲洗过的肉缝地,把张寡妇挫得生痛,连惊带怕,忍不住“哎哟”一声,待看清是邵二狗,翻过身“啪”地就是一耳光,正打在邵二狗还迷糊着的脸上,接着双手齐上,“劈里啪啦”又是一阵打,尖着嗓子叫唤:“强奸人了,强奸人了。”
吓得邵二狗急忙去捂张寡妇的嘴,惊恐地四外观看,压低了嗓音说:“别喊,别喊,我不是故意的哩。”
张寡妇说:“你不是故意的,可你要日我么,你的手是把我日了哩,我要你赔我的清白。”邵二狗着急地说:“我要是真的日了也不冤枉,可我手指头连滋味都没尝到,反倒沾上你的尿骚,哪里就日了你。”
“你放屁!”张寡妇说:“你还要把手再放一次呀,连脑袋也塞进去做我的儿子呀。”邵二狗气恼地说:“你咋不说人话,给你做儿子你不怕给撑破了呀!”
张寡妇就叫:“邵二狗日我哩,邵二狗日了我还不承认,还要给撑破哩!”
邵二狗吓得忙又去捂她的嘴,张寡妇张口就咬,邵二狗“哎呀”叫了一声,麻溜抽回手,手指肚给咬出了两个牙印,都见血印了,邵二狗揉着手叫:“你是狗呀。”
张寡妇瞪着眼说:“你到底承不承认日了我?”邵二狗说:“我没日你让我承认啥?”“你就日了,你还流脓了哩。”张寡妇嚷。
邵二狗跟她纠缠不清,脸气得红一片白一片,不是好颜色,瞪了她一眼,转身要走,张寡妇竟扑过去,骂:“你还瞪我,你是汉子你承认么,你走啥,你有本事躲到你妹妹小花的X里呀!”拾起一块土块就打,邵二狗头一歪躲过去了,转身就走,大腿给张寡妇抱住。张寡妇长得比邵二狗粗壮,手劲用得足,裤角竟给扯破了,邵二狗自觉理亏,不敢来硬的,只是连声叫嚷:“你这是干啥,快放了我,让人看见以为咱俩有啥事哩,你害了满斗还不够么,又来害我。”
张寡妇又嚷:“邵二狗你流氓,你奸了我还不承认。声音大得震人的耳鼓。”
邵二狗吓得直跺脚:“你小点声,你别嚷别嚷,我承认还不中吗?”
两人像买东西,争争讲讲,邵二狗又是一通劝,女人总算不喊叫了,邵二狗松了一口气,把张寡妇扶起来,张寡妇“哎哟”一声又坐到地上,叫骂:“我吓着了,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走不动么,你得把我背回家去。”
张寡妇人长得黑丑,又胖粗得像口缸,不是满斗看上了,邵二狗还真从没打过她的主意,讲不得条件,只得蹲下身子,不远处似乎有什么人探头探脑地望了一下,一闪就不见了。邵二狗没心情想,脑袋里是一片空白,踉踉跄跄背起张寡妇,竟像背一座山,一步三晃走下山坡,直接把她搁到炕上,临走时张寡妇扔下话:“这事不算完,你承认日了我,我要讨个说法哩。”
抬尸体下葬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出来了,人们找来几块木板,把尸体放在上面,前后穿上木杠子,用绳子绑住,四个人一组,另有四个人做替手,一齐往山上抬。抬死人有规矩,半路上是不能落地的,抬起时谁先用力谁占便宜,搭上肩就走,手脚慢的就要拖拖拉拉,半天追撵不上,还要多吃力气,有广田安排,由身体差不多的人为一组,看他们一哄而起,急急匆匆地走。一向不爱出头露面,在村子中一直装聋做哑的邵花氏也来了,活了这么大岁数,她也是头一次见着这样惨烈的场面,头一次见着人死得这样脆生,这天日到底还有没有安生呀,老天爷呀,还让不让人活?邵花氏拄着拐杖,把死去的人挨个看了一遍,走到满斗的尸体前,竟还唾了一口,再看看天日,然后默默地看着众人把尸体抬到山上,驻立好久才离去。
老刘头倒背着手,走到陈满堂尸体面前,面无表情地看了看,又点了一下头,走了。
抬秀娟的尸体时,祥子忍不住要往上扑,给来顺死死按住,连山都没让他上。
邵小花不知好歹,竟也来凑热闹,看着一个个的死人,都当成了爹,哭得甚是伤心。小花的模样不像是傻子,哭完了,还认认真真地给死者逐个磕头,起来后安安静静地,并且一直跟到山上,看人们掩埋,跟好人并无二致,连经多见广的广贤也暗暗称奇。邵满斗家穷得四壁露风,打不起棺木,连炕席也买不起,满斗家的又给悲伤捆住手脚,哪里还有张罗丧事的力气,就由着村里人找个山包草草地掩埋了。陈满堂一家做了另一处坟,陈家已没了人烟,院子显见着是空闲了,村里人便拆下些檀木,打成棺材盛殓,原说也要给邵满斗打一副的,就有人提议,陈满堂生前是做生意的,钱财上仔细,随便把他家的东西给了别人,让他在阴间也不安生呀,还不得跟满斗讨要,两人在阴间打闹,活人看着也难心静哩,还不是搞破鞋死的,哪里还有了脸面?就只好做罢。陈满堂临死到底比满斗体面些,少了野猪野狗的骚扰,下辈子也能托生人呢!至于胡子于四虎,不管他生前有多做恶,这是死了哩,活人不跟死人计较,也安葬在满斗的坟边。随着火苗的忽闪,一张张纸钱由白变红再变黑,化成了烟灰,又随着吹过来的风飘散了。
到岁数的提议,陈满堂的宅院到处是血,阴气很重,怪吓人的,村中有这么一处凶宅,任谁都害怕,可是怎么才能除去这份凶恶?就去找广贤。广贤想了想,说:“按说,水火能压邪气,水引不来,只能用火烧,只是可惜了这处宅院。”
老人们说:“可惜是可惜,但陈家人死了,谁又敢去住,还不如烧了。”
好在陈满堂家属于独门独院,与别人家有一些距离,众人意见统一,就把人分成两拨,有几个人回村里来点起一把火,任火光冲天而起。
二
祥子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跟来顺商量,于四虎刚死,于家洼定是乱成一团,少了提防,这可是个机会哩,反正下葬的事也用不着我,就咱俩去,先探听一下虚实,能见着玉娴姐把她带回来更好,带不回来再想别的法子。
有全说:“你们俩去人手少,就只有一把枪,我总觉得不放心。”祥子说:“于家洼可是个响当当的胡子窝哩,人去多了,咱手中没枪,反倒碍了手脚。”
小拴也说:“要不咱就都去,人多了有个仗势。”祥子死活不同意,有全解得他的心理,他是寻摸着给秀娟报仇的,又担心连累了别人,这更让有全担心,只是劝不住,怕劝得紧了,反而会把祥子憋屈出毛病来,只好由着祥子,让他与来顺先去,伸手拉住小拴,先回家去然后再想办法。
于家洼离邵家沟不过十几里的路,经过两道山梁,再走一段平整路,再上一处高坡,也就到了。对面山坡上的人能看得清清楚楚,两人就不敢走了。好在山上草木茂盛,藏身的地方多的是,便找个隐秘、视线好的所在,隐住身子,向村中张望。
站在高处往下望,整个村子就像一口锅,四周高,中间洼,老于家的宅院建得高大,格外显眼,正坐落在锅底处,据说,老于家先人考中举人,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在村中自然就比人高出一头,便请了阴阳先生修建宅院。阴阳先生四周看看,又用罗盘测了方位,说这宅子建在锅底处,才是大吉之地哩,不出文官也出武将,只是大吉之地必然也潜伏着凶险的,宅子位于村子中心,又是锅底,阳气不足,阴气有余,所以这宅子必须建得高大,才能壮其阳刚,弥补地势太过阴柔之虞。
也许阴阳先生看错了方位,或者宅院建得不够高大,压不住阴气,除了那一辈出了举人,后几辈于家文官武将都不曾出,家业反倒日渐破落了,到这辈上,干脆出了一窝胡子,人们琢磨着,这宅基地到底是有些名堂的,上中下三元之气,一个大轮回就是一百八十年,小轮回六十年,说不得下辈人还出胡子的,只是屋宅建下了,谁又舍得割舍?便一辈一辈地住下了。按说,于家人也不是先天就是胡子,于大虎长得虎背熊腰,在家里在外面干活都是一把好手,并不是游手好闲、好狠斗勇之徒,却是一条讲义气的汉子,只是女人命寡,跟他过了两年,连个后代也没留下,一场痨病就匆匆离去了,剰下于大虎孤单单的一个人过夜里的日月。那年赶庙会,于大虎到桃花吐老李家讨水喝,竟看中李家的闺女,偏李家闺女也看中了他,两人朝上了面,胆大妄为的于大虎竟把闺女直接拥到炕上变成女人,又领了出来。老李家也是大户体面人家,发下人来找,就找到了于大虎的一个亲戚家,李家人领出闺女,说什么也不许“把你嫁给一个死过老婆的人”,赶紧给闺女找个远方婆家嫁人,于家老爷也大骂儿子不争气,李家闺女挣不过父母,临走时愉愉地给于大虎留下一封信,说:“身行千家远,心在哥身边;此情扯不断,至死不相分。”
于大虎看得热泪盈眶,犟着脖子跟爹说:“非李家闺女不娶,你们要是不答应,我就去当胡子。”于大虎本来是吓唬爹的,说完话就去了亲戚家,一待就是三天,家里人毛了,以为他真的当了胡子,乡里有乡公所,区里有区公所,区公所里设有捕盗营,谁家有人当胡子,或者知情不报,全家人都是死罪。
大虎爹认定,儿子是当胡子了,这还了得,怕累及全家人,急忙跑到区公所,把儿子告下了,说:“于大虎不是我儿子,缺他一个不少,我还有四个儿子哩,你们杀他剐他与我于家无关。”
第四天,于大虎大摇大摆地从亲戚家回来,一进村,几个人见了他就说:“大虎你真是唬,你还敢回来,你爹告官哩,说你当了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