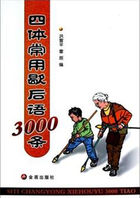没有人相信苹果是一颗心。可是,它的确就是一颗心。它是由花朵的灵魂变成一颗心,就一直藏着,藏来藏去,快要藏不住了,真的就要藏不住了,她就一咬牙,捧出来了。可是,捧出来的只是物理意义上的"苹果",世俗意义上的"心";她的心尖儿,她的秘密,她的羞涩,却留下了。谁知道留给谁呢?
只知道,那是她最善感最疼痛的部分。风来了,那里就会一颤一颤的;雨来了,那里就会一亮一亮的。她喜欢风风雨雨,那是她的仙境,她的悬念。风风雨雨给了她活着的理由。只要一静下心来,她就画呀画呀,在看得见的纸上,在看不见的纸上;画呀画呀,在时间的纸上。她把时间全都制成心爱的纸了,各式各样的纸,雪白雪白的纸,散发着香味的纸。画她的心醉,画她的神迷,画她的一闪一闪的仿佛长着翅膀的想和念,诗和歌,欢和喜,好让她的回忆都完完全全地留在那里,好给她寄托一个既明亮又温暖的家。它们全都长着一个模样,有着风的无拘无束、无忧无虑,有着雨的清清爽爽、明明净净。其实,风和雨,在她的心里也只不过是同一样东西,是她的滔滔不绝,是她的缄默无语,是她的天也好地也好,是她的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反正,没有人真正懂得她的时候,她就画啊画啊。她的画最懂得她。一不小心,她就把她的心尖儿画进去了。等发现了这一点,她就很不好意思地偷偷一笑,抹啊抹啊,抹了再画。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她也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做是好,应该怎么画才能把她的一切一切都画进去。反正,她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知道,知道得比自己还要清楚。这个人就在风里雨里,或者说,就是风和雨。他当然应该知道她为什么要把她的心尖儿留着。心尖儿怎么能交给那些又粗又陋的筐子和又蠢又笨的马车呢?筐子和马车只懂得土豆和木头的心思,怎么能明白苹果的心迹呢?怎么能保证不会漏掉和擦伤苹果的好心肠呢?把心尖儿之外的那些部分给它们就已经够让人心疼的了。如果能够藏得住,谁会冒那样的傻气呢?好在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一些替代品,模仿了心的上半部分做成的一些替代品。真品仍然在这里,真品是凡眼所看不见的,无论如何都看不见的。就像神永远在我们肉体的眼所看不见的地方一样。反正,他是会看得见的。看不见怎么行呢?一个"看不见"的人,怎么能把心尖儿交给他呢?心在种子里住着的时候,就想过了,他必须是心明眼亮的人。心明,才能折射出幸福的影像;眼亮,才能看见我的心尖儿,看见我的心尖儿上冉冉升起的太阳。我之所以千难万险顺着树干爬到枝头上、树梢上,还不就是为了看清谁是睁着眼睛谁是闭着眼睛,谁最心明最眼亮吗?我在花朵里借宿的时候,曾经吃过不少苦头,他最应该知道,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画啊……画啊……画的全是含蓄。
不懂得心的含蓄,他算什么。不懂,就什么也别想。
心尖儿当然就是心的含蓄。一点儿含蓄也没有,那算什么?不真的成了一些物化的"苹果"了吗?那样的苹果只配和芋头待在一起,谁也不会懂得珍惜。烂掉,是它唯一的命运。没有心尖儿,找回心尖儿,还原为一颗心,好好地服侍这颗心,把所有所有弥足珍贵的东西都交给它去保管,交给它去使用,便是所谓的"圣胎长养"了。哪怕把心尖儿埋在肥沃的时间里,哪怕把心尖儿藏在无垠的梦乡里,只要有这份"含蓄"在,秘密的印迹就不会逃过感觉的雷达了。含蓄,懂吗?含蓄就是不要把语言做拐杖,不要给文字做奴仆。含蓄就是"水中月镜中花";就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就是"言中有言而口不能言";就是"言无尽而意无穷";就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就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含蓄就是诗情,就是画意。含蓄就是心尖儿。
心尖儿就是心的心,神经的神经。
一只苹果没了心尖儿,它仍然是一只苹果,但是嚼而无味。
一颗心没了心尖儿,它不就变成了一块木头,甚至是废物了吗?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偏偏要嚷着将心尖儿变成废物,且无怨无悔。也不知道木头能不能变成不虚其名的善解人意的能容纳整个宇宙的苹果。不知道那些随随便便就将"苹果"送人的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就像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心尖儿留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