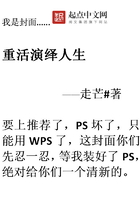27年前,在一盏煤油灯的漆黑小屋里,年轻的妈妈孤单地生下了一个女孩,取名魏筱晚。来得有点晚的小丫头,没有父爱,没有庆贺,没有亲吻,没有祝福,只有妈妈的眼泪迎接……
3天后,那个原本该守在床头的男人出现了,带回一张离婚协议书,一个妖精一样的女人。妈妈卧在床头撕碎了那张协议书,她的男人带着那个妖精,踏夜归来,又奔进了夜色。
2岁半时,那个身份应该是父亲的男人,某一天突然回了家,却是在妈妈极力的阻挠之下,搬走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让妈妈那点儿薄弱的期望最终跌向了绝望的深渊。那一次的见面,魏筱晚没能记住那个叫父亲的男人的样貌,却记住了她死死拽住的妈妈的衣角。本该没有记忆的幼龄,或许是恐惧太深,刻在了脑海。
8岁时听村里人说,那个叫“父亲”的人在城里和那个妖精又生了个儿子。魏筱晚只是心里别扭,却并没有多难过,也许是习惯了没有父亲,没什么感觉。但是在夜里醒来听到妈妈压抑绝望的哭泣声,魏筱晚的心就痛了。她终于恨,恨那个无情的男人,恨那个毁了自己一家幸福的女人。
为了她,妈妈放弃了追求自己的幸福,把自己逼成了女超人。不仅干女人的活,男人的活她也逼着自己去干。
犁地、种地、挑担子,从山脚到山上,一趟又一趟,一年又一年,终于把她养大成人,并供她念了书。
十八年里,魏筱晚的生命里没有父亲,没有一次春节的团聚,没有一分来自父亲的抚养费。
有的只是为省米粮一日两餐的日子,顶着月亮割稻子的日子,半夜下雨起床抢收稻谷的日子,的日子……
而这些并不是魏筱晚记忆里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无数个深夜醒来听见妈妈绝望的哭泣,怎么也学不会无视别人嘲笑没有父亲,总是不知道材料里父亲一栏该怎么填!
魏筱晚以为这辈子不会再和那个叫父亲的男人有交集时,却不曾想到18岁高中毕业那年,妈妈把她推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面前。
“筱晚,这是你爸,让他给你上大学的钱。”多么戏剧化的情节,却真实地发生。
那是个身高一米八的高个子男人,黝黑的脸,厚重的眉毛,一瞥浓黑的八字胡。他一只胳膊腋下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另一只手掸了掸燃着灰烬的香烟后,放到嘴边深深的吸了一口,才抬眼打量着魏筱晚,似乎在等她唤一声“爸爸”。
她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要开口叫“爸爸”,在她看来父亲不等于爸爸,“父亲”是她无法改变的事实血缘关系,而“爸爸”这个词这是一个父亲用心血浇灌出来的爱的称呼。所以,她不会叫他“爸爸”。
“我不念大学,也不需要钱。”魏筱晚不想因为自己让妈妈去求那个负心的男人,却没想到妈妈却恨铁不成钢。
“那是你爸,他有义务给你钱念书,你为什么不要,你妈我这一辈子为的什么,不就为了你能出人头地,我也争口气。”妈妈的话至今犹如耳旁。
最终魏筱晚还是借助那个叫“父亲”的男人的力量,进了大学,在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双重导向下,完成了四年大学学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公费研究生。只是,她始终不肯开口叫那个男人“爸爸”,只唤作“父亲”。
尽管现在已成年,艰辛的日子也已经过去,但却从懂事起,魏筱晚就讨厌两种人,即风流不负责任的男人和甘愿当小三的女人。魏筱晚发誓不嫁这样的男人,不做这样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