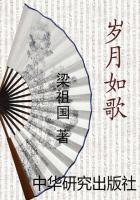鲍勃、多德森和约翰抢劫“蓝日号”快车的保险箱时,
约翰被击毙,
鲍勃的马在逃亡途中折断了腿,
多德森为了逃亡残忍地枪杀了老朋友鲍勃。
多德森用独吞的钱财成立公司后,
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掠夺钱财。
赤着的脚
——[中国]叶圣陶
站在台上的中山先生眼里闪着沉毅的光,
而他眼中那些穷苦农民赤着的脚却让他想起了从前那些苦难的岁月,
此时更让他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中山先生站在台上,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直望前面。虽然是六十将近的年纪,躯干还是柱石那样直挺。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站在他旁边,一身飘逸的纱衣恰称她秀美的姿态,视线也直注前面,严肃而带激动,像面对着神圣。
前面广场上差不多挤满了人。望过去,窠里的蜜蜂一般一刻不停地蠕动着的是人头,大部分戴着草帽,其余的光着,让太阳直晒,沾湿了的头发乌油油发亮。广场的四围是浓绿的高树,枝叶一动不动,仿佛特意掩饰这会场似的。
这是举行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大会的一天。会众从广东的各县跑来,经过许多许多的路。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或是坛子,盛放那些随身需用的简陋的东西。他们的衫裤旧而且脏,原来是白色的,几乎无从辨认;原来是黑色的,反射着油腻的光。聚集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会,他们感觉异常新鲜,又异常奇怪。
但是他们脸上全都表现出异常热烈虔诚的神情。广东型的深凹的眼睛凝望着台上的中山先生,相他的开阔的前额,相他的浓厚的眉毛,相他的渐近苍白的髭须,同时仿佛觉得中山先生渐渐凑近他们,几乎鼻子贴着鼻子。他们的颧颊部分现出比笑更有深意的表情,厚厚的嘴唇忘形地微微张开着。
他们中间彼此招呼,说话。因为人多,声音自然不小。但是显然不含浮扬的意味,可见他们心头很沉着。
人还是陆续地来。人头铺成的平面几乎全没罅隙,却不如先前那样蠕动得厉害了。
仿佛证实了理想一样,一种欣慰的感觉浮上中山先生心头,他不自觉地阖了阖眼。
这会儿他的视线向下斜注。看到的是站在前排的农民的脚:赤着,留着昨天午后雨中沾上的泥,静脉管蚯蚓一般蟠曲着,脚底黏着似地贴在地面上。
好像遇见奇迹,好像第一次看见那些赤着的脚,他一霎时入于沉思了。虽说一霎时的沉思,却回溯到几十年以前:
他想到自己的多山的乡间,山路很不容易走,但是自己在十五岁以前,就像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一样,总是赤着脚。他想到那时候家族的命运也同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相仿,全靠一双手糊口。因为米价贵,吃不起饭,只好吃山芋。他想到就从这一点,自己开始怀着革命思想:中国的农民不应该再这样困顿下去,中国的孩子必须有鞋穿,有米饭吃。他想到关于社会,关于经济,自己不倦地考察,不倦地研究,从而知道革命的事业必须农民参加,而革命的结果,农民生活应该得到改善。他想到为了这些意思撰文,演说,找书,访人,不觉延续了三四十年了。
而眼前,他想,满场站着的正是比三四十年前更困顿的农民,他们身上,有形无形的压迫胜过他们的前一代。但是,他们今天赶来开会了,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这是中国一股新的力量,革命前途的——
这些想头差不多是同时涌起的。他重又看那些赤着的脚,一缕感动的酸楚意味从胸膈向上直冒,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便潮润了,心头燃烧着亲一亲那些赤着的脚的热望。
他回头看他夫人,她正举起她的手巾。
河豚子
——[中国]王任叔
他从别人口中得知,河豚子可以毒死人,
于是讨来一篮与挨饿的妻子共同分享。
可那煮了很久的河豚子毒性消失了,
求死不能的一家人依旧挨饿。
他从别人口中得来了这一种常识,便决心走这一着算盘。
他不知从什么地方讨来了一篮的河豚子,悄悄地拿向家中走来。
一连三年的灾荒,所得的谷只够作租,凭他独手支撑的一家五口,从去冬支撑到今岁二三月,已算是困难极了。现在也只好挨饥了。
但是——怎样挨得下去呢?
这好似天使送礼物一般地喜悦,当一家人见到他拿来了一篮东西的时候。
孩子们都手舞足蹈地向前进去。
“爸爸,爸爸!什么东西呵!让我们吃哟!”
这么样的情景,真使他心伤泪落的了!
“吃!”他低低地答一声后,无限地恐怖!为孩子生命的恐怖,一齐怒潮般压上心头,喘不过气来。
他嘱咐妻子把河豚子煮熟来吃,自己托故外去一趟。他并不是自己不愿死,不吃河豚子,不过他不忍见到一家人临死的惨状,所以暂时且为避开。
已过了午了,还不见他回来。孩子却早已绕着母亲要吃了。这同甘共苦的妻子,对于丈夫是非常敬爱,任何东西断不肯先给孩子尝吃的。
日车已驾到斜西,河豚子还依然煮着。他归来了。他的足如踏在云上一般。他想象中一家尸体枕藉的惨状,真使他归来的力也衰了。
然而预备好的刀下舍生的决心,鼓起了他的勇气。早已见到孩子们炯炯的眼光在门外闪发着,过后,一阵欢迎归来的声音也听到了。
“怎么还没有死呢?”他想。
“爸爸!我们是等你来一同吃呀!”
“哦!”他知道了。
一桌上争争抢抢地吃着。久不得到鱼味的他的一家人,自然分外感到鲜甜。
吃好后,他到床上安安稳稳地睡着,静待这黑衣死神之降临。但毕竟因煮烧多时,河豚子的毒性消失了,一家人还是要安安稳稳地挨饿。
他一觉醒来,叹道:“真是求死也不得吗?”泪绽出在他的眼上了。
早上——一堆土一个兵
——[中国]沈从文
战争中,一个老同志很有经验连连击中敌寇,
一个戴钢盔的学生也学老同志的样子,
结果一命呜呼,阵地上只剩下一堆土一个兵。
天欲发白。一切皆静静的。这分沉静便孕育了稍后一时金铁齐鸣的种子。
老同志伏在山地土沟边如一只狗,身穿破棉袄儿,见得多,听得多,胆量稳稳的,心沉沉的,不怕冷,不怕饿。
为的是会那么一手,有了经验,到时候天空中燕子似的钢铁飞窜,“来,X你的娘,炸你个七块八块!”一下子把那个黑沉沉的玩意儿,向远处抛去,訇——一堆烟子,一堆石头,一堆泥土,向上直卷。一口猛劲的犁,一只瞧不见的大手,这么一下翻起多少东西!那大腿,那手指,那点撕碎拉长的内脏;起花的肠子,水蛇似的肠子。“来,X你祖宗,再来一下!”又再来了一下。
在那时节老同志是半疯的。空中的一切声音皆使他发疯。“来,X你……”便又再来了一下。每一个动作相伴而来的是个粗俗的字眼,这包含了一种力量,一分气。
老同志可没有死,天知道这是谁出的主意,勇敢人照例就不会轻易死。枪子儿常常赶人背后穿,你想跑,只一下子你便完事了。你不跑,你不会在冲过来的毛子以前完事。
嘘——一颗流弹;一只紫色的鸟儿打头上飞过去,一个信号,暴雨中第一滴雨点。来了,昨天的事又快来了。同天明一样,黑夜一走终究要来的。
一切过去了,黑夜和沉默皆已过去了。远处有了机关枪声音一阵,过后又异常沉静了。
天已亮,好像再不会有什么事。
老同志把手在空虚里抓了一把,看看风向什么方面吹。老同志身边有一个小同志,一个学生,那顶圆圆的钢盔搁在头上,代为说明他来到这儿还不多久。那学生哑哑地说:
“老同志,别开玩笑,小心一点儿。”
“小心一点儿?小心你做皇帝的命!你是来干吗的?我问你。”
那一边便无回嘴声音了。
过一会儿,那戴了钢盔的学生却说:
“老同志,老同志,到了一万顶钢盔,今早冲锋时可不怕机关枪了。”
人年轻了一点,话说得那么傻,真像机关枪子儿单拣脑瓜子钻,别一处皮肉不兴穿过似的。故老同志听到这儿时笑也不笑。后面的人要买帽子爱国,前面的可不要。他们要大炮小炮,要机关炮同向空中飞机瞄准的高射炮,向谁去要?从学生看来这老同志正有点傻,像那么勇敢,那么猛,不是傻子谁做得出这件事。看看地面各处已现出了淡淡的轮廓,壕沟如一条黑色带子,向高处爬去。学生问:
“老同志,老同志,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为什么到这儿来?鬼明白。你为什么到这儿来?我问你。人明白的都不来,来的就不大明白。大家都想搬了宝贝向南边跑,不要脸,不害羞,留下性命做皇帝,这块土地谁来守?”
“你有家……有土。”
“我有田土舍不得离开吗?我有坟土。毛子来了,占去咱们的土地,祖宗出了多少力,流过多少血,家门前一块肥土让他们拿去,不丢丑?读书人不怕丢丑我可怕丢丑。站不住了,脑瓜子炸了,胸脯瘪了,躺到那炮弹犁起的坑里去,让它烂,让它腐。赶明儿有人会说:‘老同志不瘪,争一口气,不让自己离开窄窄的沟儿向宽处跑。他死了,他硬朗,他值价。’”
那学生一句话不说,也把手在空气中捞了那么一下,想爬过来一点,似乎要亲老同志一下,老同志说:
“伙计,小心点,不是玩的。”
“得啦,我让你去做皇帝。我把你这个……”他想脱下那顶帽子,这帽子使他害了羞。
呦——
一下子小雏儿完了,放翻了,一个滚便转到壕沟里泥水中去了,一顶钢盔留在老同志身边。
“发明这玩意儿帽子?”老同志道,“天空中落雪子时,戴它到头上去,挡一阵雪子。送来一万顶,好像全望着别炸碎脑子,枪子儿赶别处进,把受伤的填满一个北京城,让人知道抵抗了那么久,伤了那么多,就来讲和似的。妈妈的,你们讲和我不和,我怕丢丑,我们祖宗并不丢丑。”
稍远处有了枪声,左边有了枪声,右边有了枪声。老同志摸摸身边,身边有一十七个炸药作馅的铁棒槌。寒气中一切皆结了冰似的。空气结了冰,铁也结了冰。
今夏流行明黄色
——[中国]刘心武
珊珊穿衣讲求时髦,
她的杏黄色连衣裙刚穿上两天就又换成了明黄的上下分开两件套,
可是当她又一次与男朋友约会时却穿了一件淡紫色的连衣裙。
猛不丁觉悟过来,已经晚了!
珊珊急匆匆地跑过几个自由市场,最后总算在秀水东街那儿买到了一件连衣裙,金黄色!黄得扎眼!
她穿着它去赴约会。
“我差点没认出你来!”男朋友上下打量着,眉毛飞上去。
“你没想到我也能弄着一件吧?唉,都怪我小病了一场,才半拉来月,跑到大街上一看,嗬,时兴上这号亮黄亮黄的了!怎么样,够派吧?”
“嗯——”男朋友的眼光分明不怎么能赶上趟。
穿着那连衣裙去上班,刚一进财会科,几位女伴就围了过来。
“哟,你这不对劲儿,眼下时兴的是明黄,不是这号杏黄!”长着一双丹凤眼的吴淑丽警告着她。
“当年不是只有皇上家才能用明黄色吗!这年头,个个姑娘都想当女皇了!”韩大姐一边叹息着。
珊珊不计较韩大姐的评语,可淑丽的话却让她全身冒汗。
回到家,妈妈责问她:“怎么刚穿两天的新衣服,就让你这么一尾巴扔到了一边?”
“您懂什么!它黄得不对!”
妈妈耸耸肩膀。这年头,姑娘们竟敢一身黄地摇来摆去。她当姑娘那阵,连“黄”字也不敢说哩。“你这人真黄!”那就离坏分子不远了。
再一次赴约,珊珊转着身子让男朋友看清楚:“是正经明黄的,不是错色的!”转完了,她指点着远近的黄衣姑娘向他宣谕,“瞧,不对,又一个不对,她们都没弄着正庄货,杏黄,多怯!浅黄,太嫩!土黄,老气……”
男朋友想表现一下独立思考能力:“我觉着柠檬黄不错!”
“柠檬黄?!还桔子黄呢!”
珊珊得意地把明黄色穿到了财务科,吴淑丽头一个尖叫起来:“新潮!这回真新潮了!上下分开两件套,比那古古板板的连衣裙洒脱多了!”
珊珊正笑成一朵花,淑丽凑到了她身前,没想到用手指头一捻她的料子,一双丹凤眼就“开了屏”:“呀!你这料子不对!如今时兴的是光面软缎,你这个——”
珊珊的笑容枯萎了。
再一次赴约,她往伸脖瞪眼的男朋友后背一拍:“你瞧哪儿呢?”
男朋友扭过头,一瞧:“你——我以为你还是明黄色呢,让我好找,满眼尽是明黄色了!”
珊珊这天穿的却是一件淡紫色的连衣裙。
我们选择的道路
——[美国]欧·亨利
鲍勃、多德森和约翰抢劫“落日号”快车的保险箱时,
约翰被击毙,鲍勃的马在逃亡途中折断了腿,
多德森为了逃亡残忍地枪杀了老朋友鲍勃。
多德森用独吞的钱财成立公司后,
采用另外一种方式掠夺钱财。
在不停地行驶了十几个小时后,“落日号”快车不得不为车里的人员补充水源,而加水的地方就在图林以东的某个地方——一个不太大的供水站。
列车的工作人员开始忙着给车子加水,而与此同时,有三个人爬上了机车。他们是鲍勃·蒂德博尔、“鲨鱼”多德森,和一名有四分之一克里克人血统的名叫“大狗”约翰的印第安人。三只火枪口坚定地对准了正在抽烟的司机。显然,司机很惊慌,因为烟头掉在了地上,而且几次张嘴都没有说出一句话。
“鲨鱼”多德森是三人中的首领,他干脆地命令司机走下机车,脱下机车和后面的煤水车的挂钩。接着“大狗”约翰蹲在煤堆上,用枪威胁着司机与司炉,命令他们把机车开出五十码之外。司机和司炉面对着枪口,不得不服从。
“鲨鱼”多德森和鲍勃·蒂德博尔认为,在乘客那里并不会有太多的收获,不必多费手脚去沙里淘金,列车的保险柜才是更大财富起源。他们发现,服务员以为“落日号”快车不过是在加水,对于车里发生的抢劫之事一无所知,因而显得从容自若。当鲍勃拿他的左轮手枪和枪柄把这种念头敲出他的脑袋时,歹徒已经将大包的火药堆向了保险柜。
随着一声巨响,金钱与宝石全都呈现在歹徒的眼前。旅客们偶尔把头伸出车窗外,瞧瞧天空有没有雷雨云。列车长拉了拉铃索,铃索似乎失去了弹力,一拉就掉了下来。“鲨鱼”多德森同鲍勃·蒂德博尔已经将战利品收拾干净,从车厢跳下,脚登高筒靴,慌慌张张地奔向机车。
司机有碍于眼前的手枪,心里的气无处发泄,还好他并未被冲昏头脑。他遵照命令将机车驶离车厢。可是要知道,没有一个计划是天衣无缝的。列车的报务员看出了蹊跷,瞧准空当,掏出手枪向歹徒打去。“大狗”约翰先生对这个列车员太大意了,无意间一步失算成为了活靶子,子弹穿透了他的心脏。这位克里克的骗子从车上滚到地上,他这一死无疑使他的同伙分赃便宜了许多。
从水塔开出二英里,歹徒逼迫司机立刻停车。
现在列车已不再具有先前的吸引力了,他们迫不及待地离开车厢寻找一个可以分赃的地方。他们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呼啦啦地猛撞了五分钟,来到了他们先前找好的地方,那里有三匹马拴在下垂的树枝上。其中一匹马在等待着“大狗”约翰,他可不会再来骑它了,尽管他生前非常想拥有这一时刻。强盗们卸下它的鞍桥,显然重获自由这一刻的兴奋可以令它暂忘主人一段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