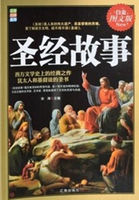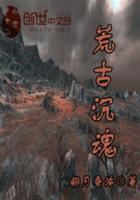星移斗转,潮涨潮落。
不知不觉中,早已步入“耳顺”之年,但我一直记不清自己的年龄,也每每忘记自己的生日。如同武则天问慧安禅师“多大年纪”一样,慧安说:“人从孩提到老死,就像始终都在滚动着的圆环一样,既无起点又无尽头。心如流水,中无间隙,看到的只是水泡的生灭。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年月可记的呢?”
活得够糊涂的啦!但人生也难得这“糊涂”二字。
唯有一点却始终不能忘怀的是,总弄不清自己为什么与佛道结下了不解之缘。
家住长江边。四川省江安县安乐乡江边的一个平坝,名曰“大中坝”,那就是我生长的地方。
当时的大中坝,宗教气氛特别浓郁,单是土地堂就有五座、“登口”四尊、庙宇一座,名曰“五神宫”。乡民信佛信道,烧香拜佛的老太婆特别多。每年每节,都要做法事,开水陆道场,放“焰口”、漂“河灯”、讲“圣喻”……儿时的兴味和时光,大多乐在其中了。
更巧的是,我“发蒙”读私塾的地方,就在“五神宫”内。当时家乡父老要聘师设教,苦于没有地方,商量后便将庙里菩萨统统搬走,以此作为“学堂”。所聘的塾师,偏巧又是一个崇禅好道的落第秀才。
暇时每每去江边独钓,口吟“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
他教我们读“人之初,性本善”,但兴来时便教我们读“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后来我去安乐乡镇上读“国民小学”,而地点却又是“观音寺”。
后去离安乐乡15公里的南溪县读中学(二中),偏巧学校又是一座寺庙改建的。三年后我参军入伍,当时部队还没有建立军营住所,又住在一座寺庙里。同我最合得来的苏参谋,虽已投笔从戎,但仍忘不了山林之乐,经常带我去参观寺观雕塑。
从事出版工作以后,原本任责编和从事美学研究,但不久又要我参与佛道石窟这一大型项目。从此成天与佛、菩萨和天尊打交道。
就这样,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活动,也就从文学、哲学、美学转向了佛道禅学。从而,写出了《禅的人生与艺术》、《红楼禅话》以及与禅道有关的《潜能与人格》。
接下来,又写了不少书佛道禅。
我的朋友们大都感到奇怪,见面必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信佛的?”
我说:“还谈不上信佛,只不过敬佛而已。”接着又补充说,“佛,可以不信,但不可不敬。”
他们见我说得认真,又问:“什么是佛?”
我反问他们:“什么不是佛?”
他们说:“别兜圈子啦!这么说吧你信佛或敬佛以来,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是如来,我就是佛。信佛——佛在;不信佛——佛自在。”
朋友们一听,都睁大眼睛瞪着我,如此大言不惭,莫不是因学佛而弄得精神错乱了不成?
我说:“其实,你们也是佛。释迦牟尼早就说过,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智慧,人人皆得成佛,个个都有资格当老佛爷。后来的禅师们也常讲,是心是佛,我心即佛。这个‘我’,就是‘无位真人’之我,也就是‘自在’之我。”
朋友们又问:“这个作为佛的自在之我,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禅’?”
我说:“不是的,‘禅’只不过是‘佛’的特质,也可以说是佛的风采、神韵。”
这一下,朋友们议论开了。
他们问:“禅究竟是什么?禅在何处?”
我借用一位禅学大师的话来告诉他们:
禅是空气,禅是大海,禅是高山,禅是雷鸣,禅是闪电,禅是春花,禅是秋月,禅是夏日,禅是冬雪。
总之,禅无时不在,禅无处不存,茶道中有,花道中有,剑道中有,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中也有。禅,几乎俯拾皆是,伸手可触,但你却很难找到它,不过无意中却又不招自来。
朋友们说:“玄啦,太玄啦!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比如说,最有禅味的事情是什么?”
我说:最有禅味的事莫过于“无事忙”。
最有禅味的饮料是什么:
茶。
最有禅意的动物呢?
乌龟。
最有禅韵的女人呢?
飘逸。
最有禅风道骨的人是什么?
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最有禅境的时间呢?
万古长空,一朝风月。
最有禅趣的东西呢?
幼儿老人,野生动物。
最有禅机的……我说:
商家捕捉的是“商机”;兵家抢占的是“战机”;领袖关注的是“时机”;儒家看中的是“天机”;道家注重的是“玄机”;佛家推崇的是“禅机”。
朋友又问我,你找到“禅机”了没有?
我说,我也有我的禅机。我的“禅位”在文而不在官,在道而不在术。时机往往与我失之交臂,也每每错失良机。所以我一生都发不了大财,但也不愁没钱花。
朋友们还要问,我说,你们不要再问了,若有兴趣的话,不妨看一看《独眼看禅机》,它会告诉你们的。
李哲良
2006年夏末秋初写于重庆出版社蜗居“栖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