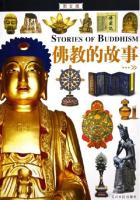在裸与不裸、脱与不脱之间,在“社会人”与“自然人”之间,在“发现自我”与“回归自我”之间,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裸派主义们是否找到平衡、超越二者之间的“支点”呢?是否从现代人的“危机”中找到了“转机”和“生机”呢?抑或是从中发现了解决“裸与不裸、脱与不脱”的“天机”呢?或者干脆就来个对传统文明进行彻底地颠覆,冲破文明“底线”,以求别有洞天的裸体世界?
(二)
这里,不妨先拈出佛家来求证,从禅与情的角度来看看禅师们是怎样参悟的。
在河西走廊西端有一个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此窟保存有自十六国至民国等时期的壁画,内容涉及宗教信仰和民俗风情等数十种珍贵的形象资料。
信仰和风俗,是构成一个社会与民族大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这早已为世人知晓,但前不久当“新西游记”采访团来莫高窟观光考察时,却无意中发现了隐藏在敦煌壁画中的另一个秘密——这便是“性文化”。
据报上披露:“第285窟中,绘制于西魏的飞天一身赤裸,形态逼真,工艺精湛,让人在赏心悦目中浮想联翩;第465窟中,一幅男女和体修炼壁画毫不隐藏地传递出一种性文化信号;笫209号窟中的清代灵官神像脚旁,那幅绘有猴子右手持桃,左手握阴茎,面露欣慰欢快神态的壁画更使在场女记者们脸红耳赤……据亚洲性学联合会会员、甘肃省性科学学会会长史成礼介绍,这些壁画都蕴藏着丰富而极其珍贵的性文化资料,它反映出古人生活的真实感受,也表现了人的本“性”
色彩。
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也赞成这种说法。他称,对此进行研究将对敦煌学会产生一定影响。
此外,采访团还观赏了嘉峪关长城内戏台上《老僧窥女》、魏晋墓石壁上的7个神秘圆阁等性文化壁画。据悉,目前,“敦煌性文化”的提法已得到专家科学证实,正引起国内外性学家的极大兴趣,认为是拓宽敦煌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
其实,像这样“一身赤裸”的飞天女神,在全国石窟雕像的壁画中,并不鲜见。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太子观舞》和《吉祥天女》,一个个都是裸体细腰,丰乳肥臀,洋溢着女性青春的美。还有国王的后妃,也都是裸体。
从时间上看,是中国早期佛像,属犍陀罗风格。
至于有关男女生殖器和性交做爱,在云南、四川等地的石窟艺术中,也早有发现。
可见,佛家似乎并不回避这个问题。尤其是佛门中的禅师,则更为豁达、开放,毫不讳言。
有一位禅师,见邻家女身寒如冰,快要冻死了,他便毫不犹豫地解怀脱衣,用自己的肉身去温暖她。
还有一个叫愚堂的禅师,则更为大胆。他竟敢在众多女人面前,一丝不挂地洗浴。
当一位想修禅的妇女去参见师太时,师太要她“放下着”。她便毫不犹豫地脱光衣服,一丝不挂。
师太对她说:“你虽然一丝不挂,但心里还挂着呢。”意思是说,她还是在想着自己是女人,心里并没有完全放下。师太要她进一步去参悟,直到男女无性别之分,穿与不穿并无不同的境界。
禅师们认为,当你大悟大觉时,便是一个“无我”之人,不会妄起分别和心存杂念。也就是《心经》中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而且,“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一切皆无,一切皆空,一切都出自天然,一切都出自本色。人穿衣,又不是衣穿人。因此,衣与不衣,裸与不裸,全在于人。它本身只不过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外在形式而已,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内在修为。
禅师们要求修行者不仅要从外在形式上消除男与女、穿与脱和雅与俗的对立,而且还要求从内在心念上彻底“放下着”,从而进入男女同一,穿脱不二的“空”的境界。
释迦牟尼说的“有情为本”、“人身难得”和生命在“一呼一吸之间”,其中就包含了对肉躯、情感和生命的珍惜与呵护。
因为凡是红尘中的每一具肉躯都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与存在,都是一种难得的缘分,而且就这么非常快速的一次。所以应好好的珍惜,给他们更多的自然而自适的空间,让他们有机会展示其天然的本色,万不可委屈和轻视他们。
《佛经》中有一篇《美女宣佛化》的故事,讲的就是佛陀对“裸体外道”的评判。
有一天,谟尸罗长者在家中举行供斋法会,特别邀请了许多裸体僧侣来家欢聚。长者的媳妇善无毒见了这些裸体僧侣后非常生气,便质问长者:“为什么要供养这些形态丑怪的人呢?”
长者听了媳妇的抱怨,吃惊地说:“难道世间上还有比他们更有修行的最上导师吗?”
媳妇视裸僧为“丑”,是一群无礼貌、无德行的“怪人”,不值得供养他们。
公公却视裸僧为“道”,是修行境界最高的“导师”,应该受到人们的珍重和供养。
但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去请求佛陀来评判。佛陀说:“裸形外道、城内士民和芸芸众生,俱受法喜,皆得供养。”这叫“世法平等,一视同仁”。
就这样,一锤定音,结束了这场公媳关于裸体的争论。
(三)
但是,由于“裸体”受到文明、进化、风俗、习惯、道德、法制、审美等多方面、多层次、多元化的制约,所以又不能不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打压与非难。即使是禅师,也不能不顾忌到世俗的习惯。
不论是道德观念,还是民族风情,一旦被人接受,约定俗成之后,便很难违背了。
习惯势力是最难冲破的人生防线。尤其是当这种习惯势力被人套上“道德、文明和进步”的光环之后,则更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戒律。
从东方到西方,从孔子、老子到柏拉图、苏格拉底,这些圣贤先哲们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同一个法则,那就是“用道德来胁迫别人,以道德来驯化身体”。
在圣贤先哲们的心目中,只有衣冠楚楚者,才是有道德、懂礼貌、有教养的“君子”,也才是最正直、最善良、最聪明的人。你要是衣冠不整,不遵守穿衣服的规矩,那你就是无操守、无道德、无教养的愚昧“小人”。你要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非要一丝不挂的话,那就不仅是“小人”,而且是“妖人”、“坏人”了。
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承传积淀之后,这个“以道德来驯化身体”的法则,便顺理成章,牢不可破了。
从而,穿衣就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穿衣就成了道德操守的象征。连莎士比亚也不得不说:“衣裳常常显示人品。”
因此,有人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驯化身体和欲望的历史。”
看来穿不穿衣服已不是一个小问题,倒成了一个人类文明不文明、道德不道德的大问题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妨继续“驯化”下去,也许能把“道德”、“文明”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但是,这样“驯化”、“包裹”了几千年,也未见得人类文明和道德好到哪里去,倒是在衣冠楚楚中,包装出了形形色色的伪君子、真小人。
不难看出,早期的裸运爱好者,他们主要就是冲着圣贤先哲们的这条“用道德驯化身体和欲望”的法则而来的。他们说:“以前,我们更多地表达的是一种反抗精神。现在,我们以创造一种既强身健体又净化灵魂的生活方式为宗旨。”
如果说在专制结构中,裸体需要的是勇气的话,那么,在民主体制下,裸体更需要的则是智慧和禅机。
《科学生活报》刊发了一篇题为《裸体:德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后被多家媒体所转载,连像重庆《党员文摘》这样的党刊也予以摘发。
文中说德国有许多裸体运动爱好者,他们早已成立了一个裸运协会,30年来已经有10多万会员。其中有艺术家、运动员、大学生、企业家和专家教授,既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还有小孩子。他们不仅在公园、市郊裸跑,而且在地铁和大街上也旁若无人地裸体行走,甚至在课堂和购物中心也一丝不挂地裸来裸去。
奇怪的是,人们见了并不惊讶,反倒习以为常,更没有人去横加干涉。裸者神泰自若,观者见惯不惊。你裸你的,我走我的,互不相干。他们说:
“只要你心是洁净的,你的身体也会变得洁净。”
“只要你自己出自本色、自然,别人看你的眼光就不会变色。”
裸运俱乐部或协会宣称:
他们现在追求的是一种“自然美”和争做一种“自然人”,而且认定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只要不是商业性的裸体行为,人们不会加以阻拦,甚至会受到“法律保护”。
这里,尽管未看见“禅风”的字样,但他们倡导的“心洁身也洁”、不去对穿与不穿进行人为的区分,和敢于袒示肉躯的“自然之美”、争做“自然之人”,似乎都与中国“禅风”一脉相通。
只不过,二者的侧重点略有不同而已。
禅者之裸,重在于“心”与“质”。
常人之裸,重在于“身”与“形”。
禅者视裸为“空”。
常人视裸为“美”。
其实,家家有路透长安,条条道路通罗马。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对“人格面罩”和“心灵枷锁”的一种突破和超越,追求的也都是一种自然之美的生活方式。
但对传统道德和文明尺度而言,这都可说是一种挑战,也可说是一种“异端”行为,一群“离经叛道”者。
随着“性感经济”的出现和道德理念的转型,人们也许会宽容这些离经叛道者。正如当年比基尼、三点式和露脐装出现一样,开始反对者是何等激烈,但若干年后的今天呢,人们却早已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了。如果丢掉恩格斯所说的“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也许会更能理解这些裸体现象了。
其实,今日之裸体与当年之三点式,仅是一步之遥,都是一种离经叛道,异端行为。但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成了谬论,裸体若跨过了底线也就只不过是一道刺眼的橙橙肉光罢了。
再说了,即使大家都宽容了“异端”,但不等于大家都要成为“异端”。也就是说,少数人裸,并不意味着大家都要裸。就算是少数人裸,也要裸中有禅,裸中有美,裸得高雅,裸得自然。
这样,裸才会有生存的空间和生命的活力。
而且,可以这样说:在当今这个文明世界里,哪怕是已步入了“后玩乐时代”,也不论人们疯狂到何种程度,都不会成为“裸”的世界。
因为,人类自从穿上文明的外衣后,就再也脱不下来了。事实上,裸与不裸、脱与不脱本身就是人类自己为自己制造的一个难以超越的“悖论”。
所以,最要紧的还是从中找到一个平衡和超越二者的支点和契机,最妙的自然是天下禅机中的“不二法门”。中国禅师大多是离经叛道的异端人物,但他们非但不危及社会,反而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开拓和发展。佛祖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异端者,所以他便宽容了“裸体外道”。
“衣与不衣”的挣扎
妙喜好唐突,光着脑袋找衣服。
我裸我无罪,天赐人间自然物。
裸者未必低贱,不裸者未必高贵。
(一)
有一天,一个三十开外的女人,突然闯进山门,径直来到法堂,口称要见宗杲和尚。说得好呢,她便在此出家。
众人一看,是丞相苏颂之孙女,早听说她放着相府千金不做,偏要闹着当尼姑。但闹来闹去,既未出嫁,也未出家,成天东奔西跑,今日倒跑上山来寻和尚开心。众人见她旁若无人地站在法堂中央,摆出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都在心里想着:这是佛门净地,不是丞相之家,容不得你来撒野。大家都想把她轰出山门,但一看师父和颜悦色地端详着她,只得作罢。同时也都觉得奇怪,师父为什么不怒反喜呢?其实,宗杲早已听说她性情古怪,家人拿她没有办法。今日一见,果然超凡脱俗,全然不像侯门千金,大家闺秀,倒像是一个久闯江湖的女艺人。他隐隐感到,似乎有某种“缘分”。于是安排她去禅房小住,又暗中派大弟子道颜去观察其动静。
道颜是个老实和尚,曾参克勤,后参宗杲,终于开悟。他奉师之命,到禅房门口往内一看,不禁顿时目瞪口呆,大惊失色,忙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同时赶紧把眼睛一闭。
原来这个女人寸丝不挂、全身赤裸地仰卧在禅床上,看去悠然自得,十分潇洒。
道颜正色说:“这是什么地方?”意思是说,这里是出家人的参禅之地,岂容你来亵渎?
女人明知其意,但偏不正面回答,反倒借题发挥说:“三世诸佛,六代祖师,天下和尚,皆从这里出。何必大惊小怪呢?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道颜一听,倒抽了一口冷气,但暗想:话丑理端,说的倒也是实情实理。因此,他睁开眼睛,大大方方地问道:“还许老僧入否?”
女人明白无疑地对他说:“这里除了驴马之外,任何人都可进出。”
不错。上自三皇五帝,如来佛祖,太上老君,下至僧尼道俗,士农工商,圣人凡夫,都是母亲生的。任何人皆从此出,谁也躲不过这一关。故曰:“人间伟大,确是母亲。”
因此,佛教把女性生殖器刻于石上,供于神龛,与佛祖平起平坐,有的还置于老佛爷的头上。东北喀什东山嘴供奉的母神坐像;云南剑川石窟中供奉的“阿央白”(女阴),即是明证。
再说,历代僧尼对此也不忌讳,还每以“一丝不挂”为话头,当做公案来参悟。这个女人想必是知道这些来历的,所以才有此举动。不过,在和尚庙里,敢于如此寸丝不挂,足见其胆略不低。而且,当时宋儒理学家们正在倡导“存天理,灭人欲”,大讲女人必须三从四德云云。在此情况下,此女竟敢对着干,如此蔑视理学,在欲而行禅,则更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再说,她分明以“一丝不挂”来作为她要求出家入室的见面礼,这不啻是对大名鼎鼎的宗杲禅师的挑战,也是她唯我独尊、充满自信的一种表现。
道颜将他看到和听到的,都小心翼翼地向师父如实地汇报了。他原以为师父会大为光火,准会叫人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
但出乎意料的是,宗杲禅师听后却一反常态,对道颜说:“先留下,待明日升堂后再说。”
(二)
次日,大师升座,也不多言,开门见山地便说:“你倒有勇气,就这么赤条条地来啦?”
来者也不示弱,干脆一句话顶了过去,说道:“莫笑本姑陈色相,谁人不是赤身来?”
首次接招就不把师父放在眼里,敢于顶撞一代宗师,在场者都不禁为她捏了一把汗。
但大师毕竟是大师,他见对方以问代答,虽然显得十分傲慢,但问得有理,也就不去计较,反而心悦诚服地笑着说:“一丝不挂这桩公案,其本来的意思,无非是袒示本心,独露纯真而已。这只是一种意象,一种象征罢了。你倒好,干脆化虚为实,以实代虚,居然真的来了个赤身露体,一裸到底。我且问你,你一丝不挂,到底想表明什么呢?”
来者见大师再次发问,她便见招拆招,朗朗说道:“纵然‘一丝不挂’,我也能‘一尘不染’。通身上下,里里外外,干干净净,明明白白?”
大师说:“好一个一尘不染,通体透明。可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
来者早不耐烦了,说:“老和尚!你这么胡搅蛮缠的还有完没完啦?
你这么啰唆,哪一天才能修成正果?只要内心干净,一尘不染,我就不怕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再说啦!他人走路,别人又何必去多管闲事呢?
只有那些心中有鬼的人,才会妄起分别,乱嚼舌头。看来我是投错庙门了,你只不过是浪得虚名而已。”说到这里,不禁仰天长啸,说“茫茫宇宙无人数,几个男儿是丈夫”。然后又惆怅低吟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任俺芒鞋踏遍天涯。”说罢,正想离去时却被大师唤回,问她既然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为什么还成天东寻西找,又为“丈夫”事而长吁短叹呢?
这一问,直把她问得哑口无言,这才知道大师的厉害。无奈中只好搪塞说:“就算有牵挂,也是一尘不染。”显然,这分明是强词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