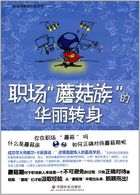“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早晨校园广播放着歌,任子柏从被窝里露出发顶,“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耳边歌声嘹亮,翻身看了一眼阳台,看见赵小美在洗毛巾便又闭上眼睛想着再睡一会儿。
“任子柏,起床了!”邹佩仪一边擦着脸一边拽任子柏的被子,“我们像一首最美丽的歌曲,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
忽的被拽开被子,任子柏也索性起身穿衣服下床洗漱。任子柏扭开水龙头看着水花溅起,“为什么你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然后留下最痛的纪念品。”忽的想起穿着西装拿着一张离婚协议书走出家门的父亲,现在想来那个背影陌生得可怕。
“任子柏还没睡醒啊?水满了!”邹佩仪走上前来扭紧水龙头。
“本来还想睡一会的,谁知道你拽我起床了。”任子柏将水杯凑近嘴唇,含着水感受回忆翻涌的冰凉。
“哎哟!还怪我!”邹佩仪将毛巾搭上衣架晾起,“五一假期居然有五天,你不早点起来享受这份喜悦啊?”
“你赢了!”任子柏吐掉泡沫,拽起水杯往嘴里灌水,“你想到去哪里玩了?”
“那是自然!我顺便载你回去吧,今天我爸过来接我呢。”
“不了,昨天罗玉娇叫我等她放学去她家玩。”任子柏将毛巾打湿擦脸。
“那下次好了。”
“好啊!”任子柏将毛巾放在水龙头下边冲洗,脑海里却尽是父亲的面容。任子柏有些烦,索性再洗一次脸,这次的水比方才的还要凉,心情似乎也平静了些。
“玉娇,不是去你家吗?怎么来医院了?”任子柏将伞向后摆,看着跟前人来人往的大医院。
“任子柏我怀孕了。”罗玉娇低着头一副可怜模样。
“你。。。不是,你怎么就怀孕了呢?你检查过了?”
“我没有骗你,我上个星期和罗一端一起去做检查的。我已经和罗一端在一起了,对不起,我没有告诉你。”
“你不是说你不会和他在一起的吗?”
“感情这东西来了你躲也躲不过啊!任子柏,你先别走,”罗玉娇拽住转身想走的任子柏,“我知道你不喜欢他,可是我们真的很好啊!”
“好到过来医院?”任子柏扯开罗玉娇的手,有些生气地看着罗玉娇。
“我们不还是学生吗?况且是我说拿掉的,他本来还想和我一起来的,可是我不想他看见我那个样子。”
“不是和你说了他这种人不要靠近了吗?你当时还答应我了呢。周婷这个例子还不足够让你清醒吗?”
“我知道,可是我就是喜欢他啊,我第一次这么死心塌地地喜欢一个人呢,你就随我吧,后果如何我都接受。你先陪我去排队好吗?”罗玉娇拽着任子柏转身面向她,“我三点多就要做手术了,我有些害怕,你陪我好吗?”
耐不住罗玉娇的软磨硬泡,任子柏陪着她走去医院手术预约台报到,而后坐在冰冷的走廊等待护士叫号。
“任子柏,你别生气啦,我知道我很过分,可是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啊。”罗玉娇和任子柏僵持许久,看着人迹罕至的走廊,心里有些慌乱。
“我在想你要是可以的话就呆在这里一晚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再走。”任子柏将书包卸下放在大腿上,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靠在凳背上。
“一端已经帮我弄好了,我家里又没人,所以我明天下午才回去。”
任子柏点了点头沉默不语,忽的想起翟荣说过的话,终究是自己白操心。
“罗玉娇,”一位护士拿着纸走了过来,“你们谁是罗玉娇,把东西放在外面跟我进来吧。”
罗玉娇将书包递给任子柏,任子柏起身抱了一下罗玉娇,“别怕,我在外面等你。”
看着罗玉娇进去手术室隔壁的房间,印着手术中的灯亮起,任子柏无聊地瘫坐在凳子上数对面瓷砖的数量。
“任子柏?真的是你,”一个身穿西装的男子走了过来,扫了一眼任子柏怀里有两个书包,“好久不见,你怎么在这里?”
“你觉得呢?”任子柏抬头看了眼满面春风的得意父亲,重新数瓷砖。
“你古灵精怪,我怎么知道,”任书同见任子柏良久不回话,便隔着两个位置坐下,“最近怎么样?”
“没你好。”
“还是那么呛人,有钱花吗?”
“没你有钱花。”
“你连基本礼仪都没有,你妈教的都是些什么?”任书同翘起二郎腿,幽幽地说着。
“真是委屈你过来和我这种俗不可耐的人说话了,任先生。”
“这里面有二十万,没钱打我电话,给,”任书同将纸条和银行卡递给任子柏,见对方一脸疑惑补充:“没有密码,这是我的卡不计入方家,你可以放心用。”
“所以说是私房钱?你别坑我,里面没钱找谁说理去?”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这医院对面就有提款机,你等一下去查就好了,”任书同看了一眼腕表,起身整理衣服,“我先走了。”
“拜拜。”任子柏将纸条和银行卡塞进书包头也不抬。
“你刚刚去哪了?我以为你去厕所了,去找了也没有。”方淑仪摸着大肚皮有些着急地走向任书同。
“抱歉,让你担心了,走吧,车在外面。”任书同扶着方淑仪走出医院,看着太阳有些猛,忙让方淑仪走向树荫等他开车过来。
任子柏站在医院门口看着任书同这般温柔贴心,心里似乎长了一根刺,阳光经过地板反射,弄得任子柏眼睛发疼。看见两人上车远去,任子柏想着转身回去等罗玉娇出来,这才发现书包有些重,压得肩膀有些疼,手臂也被勒出红色的伤痕,心里不禁想起:“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医院里消毒水扑上鼻腔,冰冷得令人难受的走廊似长无止境,任子柏有些明了住院已久的那些人为何双眸都如一潭死水平静冷寂,语调平缓,他们已经被这冷寂同化,被这白色压制情绪,难言其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