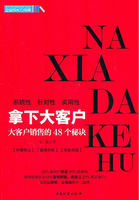可怜可爱的小黄气愤离开后,我们三人前后走在一起,奇怪了,你总是走在我的身后,我时不时得回过头看看你还在不在,我不想冷落任何一个与我同行的人,不论男女。
学校大门口处的长桥没有完工多久,白色的石栏杆上雕刻着许多好看的图纹,桥下面是一汪池水,多雨的时节还没到来,水面看起来浅浅的,池水的颜色也不那么诱人,晚上的它更显得小家子气。
奥特曼的心情依旧处于极度的危险边缘区,气氛有些郁闷,黑沉沉的夜色将我们滴水不漏地包围起来,谁也别想逃走。
“哎,给你介绍男朋友你又不喜欢……人家小黄对你不好么?还经常给你买早餐呢!”奥特曼唉声叹气地扭头对你说,我在一旁竟找不到话语的缝隙,生硬地入戏不如沉默地呆在一边,扮演哑巴的不言何尝不可呢?
奥特曼不停地叹气,我想哑巴开口的时机到了,“你老是叹气,你有什么心事啊?”
“哎,哪有什么心事。一个人,独来独往这么多年,心事早就被狗吃了,不提也罢。”
我继续猛追不放,“还真有心事啊?说出来听听咯!”
“明天是她们约定七年的日子,所以姐姐现在很纠结。”你平静地说出了奥特曼难以启齿的陈年旧事。
“我的妈呀,七年?你们纠缠了七年?还没分手?”我着实吃惊地反问她。七年是一个什么时间概念啊,能够为对方坚守单身阵地七年而不逾矩,实在不能不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分了,早分了,七年前就分了。”奥特曼一脸严肃地认真回答了我的夸张惊讶。从她严肃的脸庞上,我隐约看得见她的心在收缩,又在扩张,一呼一吸,有规律而又无规律地日夜不停地跳动着。这些年真是委屈她了。
她从高中以来就是一个很要强很刻苦耐劳的女生,我不敢说她算不算女强人。在大学里,她每天都做好几份兼职,每个星期的某一天还得去附近的小学支教,她在班上也是赫赫有名的打不死的小强。因为超负荷的工作,每天子夜时分,女生宿舍的围墙上将闪动一瞥黑影,跟着那抹黑沉沉的影子移动的步伐,你将寻到她的寝室,黑灯瞎火的寝室,寂静无声的寝室。她说自己经常凌晨三点多才疲累地爬上床歇息,早上七点许便刻不容缓地滚下床来,她多么苍白呵,脸上的血色几近为零,阻碍她变美的痘痘愈发猖獗。劝她吧,她总能找到很多理由来扳倒你。
我说:“七年的时间,你可以放下了。”
“谁说我没放下?”她强词夺理时,脸色是沉重的。这不是明摆着撒谎么?我在心里鄙视她,干脆回她以“呵呵”一句。
绿树脚下的草坪一半枯黄一半新绿,它们的甘霖在不远的前方徘徊,它们也许清楚地知道,令人心生希望的甘霖就在不远的某一朵白云上,或者在某一座山峰乳白的雾岚内部;它们也许已经对吃吃不来的甘霖绝望了,纵使事实不是这样。人,何尝曾超越过植物?相信爱情的人,若爱情在漆黑的冷夜里失散了,先前一起许下的海誓山盟就如枯草们的甘霖,等也不是,不等也不是,爱情是折磨人的东西,让你生不如死的同时,又给你无限的生生不息的光灿的希望。
时间已经滑过十点半的钟摆,食堂已关门,眼看奥特曼难过得不死不活的,我想买杯奶茶给她润润干苦的喉咙。
“走,买奶茶给你俩喝。”我提高嗓门建议道。
事与愿违,奥特曼坚决不喝,所以只好买了瓶农夫山泉委屈你,可你反复强调:我要喝农夫山泉,我喜欢喝农夫山泉。
到了分道的路口,你们沿着既定的方向徒步走远,逐渐隐没在朦胧的夜色中,我的灯为我撑起了一扇光明。我愿意想象一下七年的约定是什么样子,这欲罢不能地纠缠承载了几许重量的爱恨交加,我愿意细细品味,慢慢加工改造。
在我不长不短的生命旅途中,我听过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爱情故事,奥特曼的七年之约算是一个特例,七年是一条颀长幽深的大河,在之间,足以掀起数不清的狂风骤雨,足以守得云开见月明,足以忘却曾经无比深爱着的那个人,足以投入另一段感情开始另一种新的生活。她却偏偏选择了原地踏步,这其中饱含的深情可不是一个具体数字所能诠释清楚的。我不知道奥特曼挥霍青春芳华苦苦为他坚守岗位的那个男人到底是一个何许人也?他很有才吗,那一定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首屈一指的稀有人物?他深谙女生的心思吗,那他一定口齿伶俐,一定非常懂得伪装的绝技,或者学习了无数多的有关心理学的著作,或者他就是半个天才?难道他亦是凡人一个吗,女人所热烈渴求的温柔,他都一一具备吗,我非常好奇地想一探究竟?
哪怕那个男人是天才,是五百年才出现的一枚罕见才子,是人间的极品男人,我都觉得他是虚伪到了极点的男人,要么就是奥特曼实在能装、实在能耐得住寂寞。可是,在我浅薄地看来,奥特曼始终是不值的自残。如果一个男人真爱你,他岂会忍心让你苦守空闺数个春夏秋冬而不姗姗前来?尽管这样,我还是一百个乐意歌颂奥特曼一番,你是人,你因了所有的真诚,终究促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举世无双的你。但是,未来不可再如此忠贞不渝了,他如果要走你别挽留,如果他要来你就去万水千山之外接他,如何?(我想男同胞们更该如此吧,至少才更像一个男人嘛,你说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