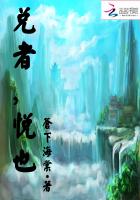来J市一年多了,我才发觉J市是没有春秋的——只有冬夏。所以国庆的时候还是一如既往的五房六月(ps热)。热本就易使人燥,况且我是特殊的。
在我打算全身心地读莱恩的《分裂的自我》时,那该死的室友们又因为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聒噪不已。她们一直都是聒噪不已的,总是为了一件无聊的嚷嚷不停。不管好的,坏的,开心的,不开心的,施舍或追讨。总是一些毫无价值的争端,毫无意义地浪费自己的时间,影响别人比如我。我需要读书,我需要静静,我故意爬上床去,躺下佯装睡觉,就这样暗示她们别吵了,可她们仍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手舞足蹈。
“你们不能静点吗?”我是真的被烦得头疼欲裂的。
她们似乎像没听到我的话,并且有进一步挑战我的忍耐。“XX,一起加入啊,健美操老师教的那个动作怎么跳来着?”然后该死的,她们居然跟着该死的低音炮,该死的乱跳起来。
我无奈下床,我找出了水果刀,我真的很想杀人了。是不是非得有人流血了,她们才会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才会安静。我反复地摩挲着那把不甚锋利的刀,明晃晃的金属面刺地我的眼睛很痛,此时我已是头目欲裂的状态了。我不清楚我是从何时又变得这样暴躁起来,我只知道我一直在忍,我真的很想和她们撕逼。我很想告诉这群****不要再为****的事瞎****还打扰别人的休息了。这样自私,这样残忍,这样作死......
医生的话在我脑海又响了起来,那个和蔼的戴着粗框眼镜的中年人很凝重地对我说道:“如果下次再来,你就必须住院了。”我一点都不想再见到他,那绝对是我人生的耻辱。我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水果刀,然后闭上双眼,我需要安定,我需要镇静。然而总有****要惹我,逼我不得不转过身去面对她们。“今天不是我死就是你们亡”这句话夹杂在聒噪烦死的打闹声中,一遍遍地被提取出来,在我的脑海里轰鸣。
我快要爆炸了,我不记得我是如何手握水果刀转过身去,面目狰狞地朝她们吼道:“吵你妹!想死吗?”同时往我自己的手腕上划了一刀,血流出来的疼痛震醒了我,她们面孔苍白,眼瞳放大,十分惊诧地看着我,都离我远远的,终于不再闹了。
我没有继续看这群自私的蠢货,我自己把血用纸巾擦干净,我已经不在乎是否会感染了,就只找出了一瓶碘酒,擦上贴上很多创可贴,把伤口盖住,从抽屉取出氮氯平,倒出一片吃了,我就缓缓地爬上床,然后似乎变得轻松起来,脑子终于慢慢归于一片寂静。我盖上被子,慢慢地沉沉睡去,如同一切并未发生,如同整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
沉寂,沉寂.....最舒服地沉寂。
Part2没有消停
那次爆发之后,这群****们终于消停了一阵子。直到辅导员找我谈话,我才意识到--事情永远不会消停了。
他打电话给我时我正在去医院的路上,公交车上是很挤的。手机响起的时候,我被吓了一跳,忙乱之中掏出手机。
他说:“慕琳吗?我是你们的李老师。”
我们的李老师?呵呵,我对于这个只会讲一大堆废话还有无用的心灵鸡汤的名义上的辅导员并没有多大印象,然而我现在无暇再听他扯圈子了,也无暇对他礼貌了。我说:“有事吗?我要去医院,我很忙。”
他似乎怔了一下,有些奇怪地问:“去医院?你得什么病了?”
我就知道他除了会说一堆废话以及名义上的关怀的话别无它用,所以我当时是很有些气急地说:“没事,我这几天身体有些不舒服,就是去医院检查下,劳烦您给批准一下今天的假条。”
接下来他的话简直让我怒不可遏了。他依旧是用那种不咸不淡的语气说道:“为什么不舒服?哪里不舒服?你得先给我说清楚才能给你批准假条。还有你室友......”
我打断他,几乎是吼了:“我得什么病也不要你管,假条我管你批不批,我要去医院,出了什么事我一力承担不要你负责好吧。!”
他还在那边叽里呱啦,我直接关机。艹,就知道撇清自己推卸责任。也许是我吼得太大声,车上的人都用一种鄙夷的眼神瞧着我。看啊,看啊,看够了没?一群****。
到医院,我似乎听到自己的心破碎的声音,我听见了,就和玻璃破碎的声音一样,我仍旧惧怕面对医生,我仍然是脆弱的。我不敢走进那里。我连挂号的勇气也没有。早先是预约好的。此时时间也正好。我前面也没有人。但是我双腿沉重。我觉得我瘫痪了,像被人定住了。当前面的护士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不能进去。我几乎是狂奔出那里的。顾不得周围人的异样眼光。我一路狂奔,直到看不见刚才那些人和护士。
啊,老天!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我突然觉得很委屈,我很想谁给我个希望,谁只要能给我看见生活的一点点光就好了。可是没有,我周围全是黑暗的,肮脏的,自私的,龌龊的,永无宁日的。我哭了,我抑制不住我自己的眼泪,它们滚烫而奔涌,可是没有人,没有人理会我,也不会有人来安抚我。
我不知道我流了多久的眼泪,直到我的眼睛有些胀痛,我的喉咙有些干涸了,我终于安抚好了自己。最终我只去取药处,拿了一瓶氮氯平。
回到那个****聚集的地方,我又开始控制自己的呼吸了。我总是觉得那里的空气会使我窒息,她们把有毒的音符无限制地投进了空气里,搅拌均匀,然后一步步地毒杀我。
我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我会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