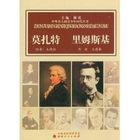奢华的赌场
有一天,杜月笙来到一家酒吧,这是“吃角子老虎”大王美国人杰克?拉莱开设的。
上海人将硬币称为角子,旧时市面流通的角子有银制和镍制的,分2角、1角两种。所谓“吃角子老虎”是一种赌具,它体积不大,外形方方正正像只匣子,上面有一个可塞进角子的小孔,下面有大漏斗状的出口。赌徒把一枚角子塞进小孔,再扳动匣子右方的铁柄开关,匣内的机械装置就转动起来,待停转后,下面的出口处有时会吐出二枚、四枚甚至大批的角子,这时赌徒便赢了。但大多数时出口处一无所有,这时赌徒便输了。
由于这种赌具吃进角子后一般都只进不出,似猛虎吞食,故被人们称为“吃角子老虎。”
“吃角子老虎”本是美国市场上出售糖果的自动售货机,后经改装成为赌具,风靡欧美。将这种赌具运进上海,骗取中国人钱财的,就是杰克?拉莱。
杰克?拉莱在美国时是个无业流氓,曾因使用空头支票诈骗被判刑坐牢。刑满释放后,这个穷极无聊的流氓在美国实在混不下去,他听说中国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便远渡重洋,孤身一人来到上海。
开始,杰克?拉莱在一家外国人开的酒吧间当服务员,后来又在大华饭店打杂差,这些工作都相当辛苦,收入也不多。
浪荡惯了的杰克?拉莱不堪忍受,便想方设法另谋出路。
这时,他看到上海赌风盛行,便想到了家乡的“吃角子老虎”,他在美国时是玩“吃角子老虎”的老手,深知这种赌具对于赌徒来说是十赌九输,而对赌主而言则利市百倍。于是,他回美国偷运来一台“吃角子老虎”,在上海街头摆了个小小的赌摊。
当时的上海人,从未见过这种新式机器赌具,出于好奇心,不少人都掏出角子塞进“吃角子老虎”里试试运气,结果大多数有去无回。而杰克?拉莱却每天能从它肚子里捞取几百元钱。
杰克?拉莱发了一笔小财后,又从美国运来几台“吃角子老虎”,当时中国海关禁止赌具进口。为了瞒过海关稽查,他将机芯拆散混装在行李里,运抵上海后再装配。
他这样经常拆拆装装,几年后对机器构造已相当熟悉,便自己投资设厂在上海生产制造,这样,大批的“吃角子老虎”就成群结队地出笼了。
到了30年代,“吃角子老虎”已遍布上海,凡舞厅、戏院、咖啡馆、游乐场等公共场所,到处可见,总数达千余台,杰克?拉莱成了“吃角子老虎”大王。
当时,每台“吃角子老虎”平均每天能获利200多元,由赌具的所有者和设置场地的主人按比例分成。杰克?拉莱因此暴发,从一个穷流氓变成了腰缠10万美元的富翁,还在上海开了三家颇有气派的DDS酒吧。
坐在豪华气派的酒吧里,杜月笙想,应该向杰克?拉莱学学,也开一个赌场,上海这地方各色人等都有,赌场只要办得有自己的特色,那一定会赢得广大赌徒的青睐的。
主意即定,杜月笙便去找黄金荣、张啸林商议,二人听后,拍手赞成。
“上海滩的赌场我也进过不少,都不够气派,我们要选一个气派点的房子。”张啸林说。
第二天,三大亨又找来了金庭荪、顾嘉棠、范回春、马祥生等人在“三鑫公司”的密室里商议了半天后,一致认为开赌场与贩鸦片同样是好买卖,并选定了环境幽静、装饰豪华的福煦路181号洋房作为赌窟。
福煦路181号的这幢大洋房,原系汇丰银行买办席鹿笙之父所建,后由于席家又住了别的房屋,便闲置。杜月笙一出面,就买了下来。
杜月笙看中这幢洋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考虑到赌场的安全问题。181号前门是公共租界。后门是法租界,万一公共租界巡捕来捉赌,赌徒可以逃到法租界。如果法租界巡捕来捉赌,赌徒可以逃到公共租界。
“181”号开张之初只是“三鑫公司”同仁俱乐部。须凭会员证入场,后来扩展到会员的家属、亲友都可进去。最后凡有钱愿赌博的都来者不拒。于是,一些闻人、大亨、财主纷纷前来豪赌。
按照杜月笙具体制定的措施来实施,财场内的赌博项目,有轮盘、摇宝、麻将、牌九、扑克等等。
场内供应齐全,服务周到,实行“三白”。
所谓“三白”,就是赌徒凡先付200元买了筹码并已下注开赌后,便可以白吃、白喝、白吸。赌场内设有中西餐厅,供应精美菜肴,有酒吧间供应高级名酒,有烟榻供应上等鸦片,这些都任凭赌徒随时享用,不收分文。如果是乘自备汽车来的,赌场还会付给司机4元钱,乘出租汽车来的,车费则由赌场支付,如带保镖侍从来的,每人还发给4元饭钱。
赌场如此大方,其实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以蝇头小利诱骗赌徒的大笔钱财。可笑的是有些爱占小便宜的阔太太,以为到了181号便可不花钱地大吃大喝。连司机的工资都可以省却,何乐而不为。于是,乘了自备汽车开进去,买了200元筹码后,两个小姐妹串通好赌摇宝,一个押大,一个押小。自以为反正输赢都是自己人,岂知赌场早在骰子里灌了铅,能控制骰子的点数,于是摇宝人连开几次三粒骰子同点的“宝子”,不管押大押小,统统被赌场吃进,200元筹码转眼间就全部输光,自作聪明的太太贪小失大,200元大洋只换得一顿酒菜和司机4元小费。
太太们的如此遭遇,在181号只能算是微不足道的小输,那些一掷千金,以致倾家荡产,赌得丢掉性命的还大有人在。
广西有个军阀因武装走私鸦片得了一笔巨款,他将20万元交给太太带到上海存银行。这位太太到上海后未进银行先进赌场。她先下小注几百元小赌,一会儿就赢了1000多元。她见手气如此好,便放手大赌,结果20万元巨款输得精光。太太害怕回广西,就在181号烟榻上吞服鸦片自尽。
还有一个从外省来上海采购物资的小吏,携带一笔公款一头闯进181号想碰碰运气,一夜间居然赢了几千元,小吏兴奋不已,休息片刻又赌,却连赌连输,数万公款化为乌有,他躺在地上嚎啕大哭,赌场的人开恩给了他20元钱买船票回老家。小吏上船后想回到家无法向上司交差,便一头扎进了黄浦江。
为了进一步招揽赌客,杜月笙又在赌场的三楼开设了一个土耳其浴室。
这土耳其浴室,有40位年青貌美的按摩女郎,她们对赌客提供“一条龙”服务,从搓背、捏脚、捶腿,到陪浴、陪睡,全都免费服务。
不少赌客在输得精光后,就跑到餐厅里海吃一顿,吃完后便来到土耳其浴室,搂上一个漂亮的姑娘……
这些姑娘异常辛苦,除要不停地满足这些输得精光的赌徒的发泄之外,还要始终面带微笑为那些家伙们按摩。
等到赌场收场后,那些“工作人员”又会上来……
最令按摩女郎们万分痛苦的是,有时候能一下子涌上来上百个输得精光的家伙,他们几个人围住一个女郎,轮番射击,常常一折腾就是几个小时。那年夏天,有个叫桃红的姑娘恰巧被几个身强力壮的家伙碰上了。从下午5点一直到晚上11点,结果桃红就那么被活活地折腾死了。
在这181号赌场中,杜月笙另外又辟了一个特别的雅静房间,由他自己专门陪一些达官贵人们豪赌,他把这当作拉拢一些军阀、政客的重要手段。
杜月笙的赌术十分高明,在很多场合,都是十赌九赢,在这181号的雅静赌室中,他当然更是得心应手。
有一次,四川军阀范绍增与杜月笙一起赌,结果一夜输了80万。这80万块钱是他从四川带来要购买军火的。因此,他十分沮丧。
但杜月笙接过他递来的80万支票后,却掏出打火机,打出火苗,把支票烧了。
“不过是玩玩,何必这么认真呢?”杜月笙说。
范绍增感激异常,从此与杜月笙成为莫逆之交。
181号开张后,生意兴隆,日进斗金,惹得洪帮三合会的人眼红,他们派人找到杜月笙,说:
“杜先生,我们三合会的弟兄们每日在福煦路上行走,很是辛苦,杜先生日进斗金,时进斗银,能否一个月给5000元的小意思呢?杜先生放心,有了这份津贴,我们保证赌场平安无事。”
“我要是不给呢?”杜月笙微笑着说。
“那我们就不清楚了。”
“在上海滩,除非我杜月笙不愿意干,只要愿意干,还没有干不成的事。”
“能这样,当然最好不过。”
“好,我等着。”
其实从赌场开张那天起,杜月笙就派了心腹顾嘉棠率了20名保镖身藏短枪充当赌场警卫。他们连上海滩上的所有外国巡捕都不怕,别说小小的三合会。
三合会的人自认自己在上海滩还是相当有实力的,杜月笙不给面子,当然应给他点颜色看看。
三天后的一个下午,4点半,181号赌场开张已两个小时,大厅里面的人已满了。突然有两个头戴鸭舌帽的人来到门前,往里面扔了几个东西,接着,里面响起了几声“轰轰”的巨响。
“不好了,有人扔炸弹!”
赌客们一窝蜂地往外涌去。一时间,人挤人,人碰人,人踩人,堆在一起推搡不开。
闹腾有半个多小时,赌客们才全涌出大厅。一些桌椅及玻璃烂掉了。幸亏只有两个赌客被踩伤,无人伤及性命。
而另有十几个人都被炸伤了。扔进来的是将火药装在香烟听子里的土炸弹,杀伤力极小。那十几个只不过是被擦破了点皮。
这几枚土炸弹是三合会的那帮家伙所扔。为此,181号赌场关闭了三天。
这三天里,三合会的大堂主、二堂主、三堂主的脑袋全被人割掉了,放在三合会堂口的门前。而扔炸弹的那几个家伙则莫名其妙地失踪了。直到一个星期后,一个打鱼人从黄埔江里捞上来一个装着尸首的麻袋,人们才知道,这几个家伙全被绑上手脚,装进麻袋扔进黄浦江里种荷花了。
至此,再也没有人敢到181号来找麻烦了。
为谋官失钱财
杜月笙广交天下友,目的都是为了一个“财”字。只要能发财,用什么手段去交友,他一点也不在乎。
当时,有个北洋官僚叫陈少侯,河南省正阳县人。北洋政府皖系军阀倪嗣冲治皖时的财政厅长。1924年,倪嗣冲病死,倪氏在安徽的势力走向崩溃。陈少侯也随之下台。他先是潜居天津,那时北洋政权已转入直系,他与直系没有渊源,只得携眷南下上海,在新闸路购进一幢小楼房,做起寓公来。
但是,此人不甘寂寞,依仗自己搜刮来的万贯家财。在上海广事交游,以求再起。他听说杜月笙交游广阔,路子多,与下野总统黎元洪都关系密切,便积极找关系,托门子,与杜月笙结识。一来二去,双方很快熟悉,陈少侯觉得,杜月笙这人的确不错,很够朋友,就告诉他,自己身边有一笔钱,很想再运动运动,再出山。谋个一官半职。杜先生路子广,要是遇到机会,千万别忘了推荐。
杜月笙满口答应。
1924年暮春的一天。
上午10点多钟,一辆黑色轿车在陈少侯公馆门前缓缓停下。从车上跳下两名身强力壮的保镖,随后从车内钻出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他扶了一下金丝边眼镜,然后用手杖指点着铁门。
一名保镖走过去,叫开铁门,随即递上一张名片,说:“请通报一声。”
陈少侯正在吸食鸦片烟,姨太太杨氏接过名片念道:“保定电灯公司董事、天津利丰大米庄采办主任陶然客。”
陈少侯马上放下烟枪坐起来,因为保定电灯公司、天津利丰大米庄都是当时的竞选大总统曹锟家的产业,军阀们都知道。陈少侯从杨氏手中接过名片,琢磨着:“这可是曹锟大总统的家产呀,陶然客。咦,我怎么想不起这个人来……”边说,陈少侯边站起来,穿好长衫,吩咐道:“请到客厅。”
来访者陶然客一见陈少侯,就大声惊呼:“少侯兄,还认得我吗?”
陈少侯仔细端详了他一眼,不无疑惑地说:“年代久了,年代久了。请坐!”
陶然客问道:“少侯兄,还记得倪毓菜,倪老三吗?”
“他是倪督军的胞弟,当然认得。”
“倪老三那时在正阳县聚赌,输了就到我那里借钱,听说还到你的票号(钱庄)借过钱的,是吧?”
“旧事一桩哕。请问陶先生那时在正阳县做什么生意?”
“东关豫新粮油行。”
“噢——,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当年豫新的陶掌柜。哎呀,模样全变了!”
“到底是20多年了嘛,还能老是那么年轻!”说着,陶然客哈哈大笑起来。
陈少侯也微微一笑。
接着,陶然客侃侃而谈曹锟的家产,以及这次要在上海采购的一批大米的事,说:“曹三爷说了,有多少收多少,要赶紧北运。”
陶然客神秘地伸出三个手指头:“老兄也不是外人,曹三爷派专人送来了3000根条子!”
陈少侯听得目瞪口呆。
侃了半个多时辰,陶然客起身告辞了。
陶然客走后,陈少侯静下来沉思,觉得这个人叙说20多年前他在老家的事,一桩桩都说得清清楚楚,像是那么回子事,可是这个人的相貌怎么就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呢?
上海滩是个险滩,要防备着点才是。为了防止上当,陈少侯备了一份礼品,去了杜月笙家,把前一天陶然客登门来访的前后情况叙说了一遍,疑心其中是否有诈。
杜月笙说:“这事我也拿不准。陈先生在上海,有事尽管找我杜月笙。我给你四个保镖,任凭你使唤。依我愚见,陈先生不妨就去回访一下那位朋友,探探虚实,倘若有诈,他是跑不掉的!”
杜月笙立即打发人叫来四条汉子,吩咐道:“你们随陈先生去吧。今后一切听陈先生的指使,不准出一点差错。”
陈少侯带着四个保镖没有回家,却按照杜月笙的嘱告,根据名片上的地址,直奔陶然客在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的寓所。
陶然客乐呵呵地把陈少侯迎进客厅。
这是一幢十分气派的花园洋房。庭院里,绿草如茵。客厅里,豪华阔气,一幅曹锟手书的“虎”字挂在客厅正中,特别引人注目。曹锟大字不识几个,但“虎”字却写得不赖,还钤着朱红的印章。
陈少侯不禁多看了几眼。
陶然客见状,随口说道:“曹三爷过年时给我写的。”
陈少侯点点头,说:“大总统的字有气魄!有功力!”
遂即坐下,接着说:“曹大总统处还望老兄举荐一二。”
陈少侯是个官迷,耐不住下野以后的冷清生活,看到这位陶然客竟与当朝大总统有关系,便不愿放弃这个攀缘的机遇。
其实,陈少侯“以求再起”的欲望早有流露,陶然客一眼就看出来了,忙说:“少侯兄,我们是老乡、老朋友,请放心,待粮食收齐,我是要去见三爷的,到时候一定代为举荐。少侯兄出头之日,可别忘了我陶某人哟!”
“拜托拜托!友情后补。”
两人正在谈话之间,从楼上走下一位十分妖娆的年轻女人。
陶然客指点着说:“这是小妾明珠。”
陈少侯站起来向走来的女人点点头。明珠走到陶然客旁边坐下,轻声地向他耳语了一阵子。
陶然客笑着对陈少侯说:“她有一笔私房钱,想交给陈先生从安徽购进一批货,转手赚两个。”跟着嘿嘿笑了几声。
“可以,可以,少侯愿为嫂夫人效劳。”
陶然客拍拍明珠的大腿:“去把你的私房钱拿来吧。”
明珠嫣然一笑,急步往楼上走去。不一会儿功夫,抱来了一只小铁箱子,当着陈少侯的面打开来,数清一共是每根1两重100根“小黄鱼”,交给了陈少侯。
陈少侯拿出一根看了看,掂了掂,说:“好吧,我给嫂夫人写个字据吧。”
“不必!”陶然客伸出手掌阻拦:“区区小事,少侯兄也太瞧不起我了!”
回到家中,陈少侯逐条鉴定,果然是足金100两。
从此,陈少侯不仅对陶然客不再有半点疑心,而且加倍信任。他果然尽朋友之道,给姓陶的小妾购来货物,叫她发了一笔小财。于是,二人常来常往,成了要好的朋友;后来,陈少侯索性把杜月笙派来的四个保镖也辞退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