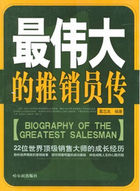杜月笙自己觉得,在高桥镇上他再呆下去,更不会有什么大出息了。他很清楚,若是继续呆下去,到头来只会和赌棚里的那些打手、赌棍们一样,终日糊个肚子圆。不远处的上海,五花八门,五光十色,才是大显身手的地方。
终于有一天,他试探性地向堂嫂露了口风,他想把归他名下的那一半祖屋卖掉,得来的钱,他带着去上海打天下。
堂嫂听后大吃一惊,连忙去通知他的舅父和他的姑父万春发。
舅父早已对他恨之入骨,如今听说他胆敢出卖老宅,不由勃然大怒,连忙跑去把杜月笙捉住,带到老宅的堂屋,狠狠地打了一顿,直到杜月笙连连求饶,他才罢手。
“今后你要再敢提卖老宅,我就把你打成哑巴。”
杜月笙不敢再打杜氏老宅的主意了,但上海他依然要闯。他打算,自己边走边讨饭,一路讨进上海。
本来杜月笙是准备悄悄离去的,但他想起老外婆一直为他牵肠挂肚,便跑去告诉了她。
老外婆觉得,这无异于生离死别。回想起杜月笙身世的凄凉,生活的艰辛,心中一酸,当时就哭了。
当晚,老外婆多方设法,找到一位邻居写了一封荐函,叫他带到十六铺的一家水果行,去当学徒。
就这样,杜月笙在上海算是有了一个落脚的去处。
十六铺水果店的小学徒
杜月笙初到上海,年纪小,又是乡下人,识字也不多,什么都外行,百事不懂,难免要受气吃苦。他到鸿元盛的头三个月,生意上的事情,连一点边都沾不着。他的主要工作,是服侍师兄、店员、跑街,被他们支来支去,做这做那。慢慢的,他才巴结上老板、老板娘,成了老板的小厮,老板娘做家务的得力帮手。倒夜壶,刷马桶,什么苦差使都落在他身上。
杜月笙为了求生存,图发展,开始那段时期,他倒也真正尽心尽力,任劳任怨,不叫苦,不叫累,天不亮起床,一直干到深更半夜。等店里每一个人都安歇了,他才拖着疲惫万分的身子,摊开地铺睡觉。
由于杜月笙能吃苦耐劳,讲究信誉,店老板渐渐地对他寄予了信任,开始派他上街跑腿。跑腿之初,做的全是粗活,譬如背负肩挑,送货提货,工作毫无意思。不过,这总比倒夜壶强,所以,他心里还是很高兴。
杜月笙来到大街和马路上不久,他便发觉这十里洋场,花花世界,真可谓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
当时的上海,五方杂处,各路英雄好汉云集,来此的中外人士,都认为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赌徒、骗子、盗贼、扒手,都把大上海当做他们大显身手、一展鸿图的理想之地。他们软骗硬抢,揩油调包,巧取豪夺,令人防不胜防。
开始时杜月笙也上过几次当,吃过几次亏,回到店里,被师兄斥骂,老板责打。杜月笙慢慢开始醒悟,要想在上海滩上混,处在牛鬼蛇神、三山五岳的人物之中,结交朋友,应该是当务之急。
杜月笙明白要想在那种光怪陆离、波谲诡秘的复杂环境中交朋友,凭杜月笙一个十五六岁的乡下小伙计,既没有请客置酒的本钱,又缺乏实力派人物做靠山,谈何容易?
杜月笙在学做生意时,开始四处留心起来,遇到成群结伙的人,他总是喜欢凑上去。但是,别人看不上他这个新来乍到的浦东乡下人。
杜月笙17岁这一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沪上震动。同时,黄兴组织的华兴会,在湖南起义失败,消息传到上海,民众为之热血沸腾。此时,因为美国人虐待童工,上海人民倡议抵制美国货。
在那一段时间,常常有人上街示威游行。杜月笙觉得挺有意思,一有时间就到街上去看,有时,也走进队伍里,喊几声口号。
但是,鸿元盛的老板,并不希望自己的水果行产生这样那样的麻烦,尤其是与当局相对立的麻烦。他指责杜月笙不应该时常与人成群结队,招惹是非。跺脚大骂了一通后,他把杜月笙赶出了水果行。
杜月笙有些心灰意冷,在街上孤独地转着,他无意之中遇见一位旧相识,当年和他同在鸿元盛当小伙计的王国生。
王国生比杜月笙当学徒早,一年前就熬出了师。如今,他自立门户,开了一家叫做潘源盛水果行。
王国生见杜月笙三四年来毫无进步,看在同门师兄弟的份上,就拉他到潘源盛去帮忙。
这位王国生在以前与杜月笙的交往中,觉得杜月笙将来定能成大器,因而对他优礼有加,两个人不分店东伙计,平起平坐。
杜月笙因感恩图报,刚开始,兢兢业业,帮着王国生,把潘源盛的业务做得井井有条蒸蒸日上。
那时的上海,建筑物大都是两三层高的房子,望衡对宇,街道狭窄。但是,火车轮船,轿马舟楫,却从国内国外,四乡八镇日夜不停地带来如潮的人流。外来资金的大量涌入,东南财富渐渐集中,几十年前还是芦花满眼的黄浦滩,现今却已沧海桑田,楼房林立了。
随着建筑物的增多,都市畸形发展的加剧,黑暗下的阴影也越来越多。
上海古老破旧的旧城,和现代面目的租界地区犬牙相错,唇齿互依,交界之处便成为罪恶的渊源。
店员、车夫、小贩等人,在劳累了一日之后,往往把有限的血汗钱花进那些低级的游乐场所。这些低级的游乐场所,大多是赌馆和妓院。
上海的赌场大多由广东人开设,虹口一带是他们的根据地。这里大小不一、各式各样的赌场星罗棋布。除此以外,北门外城根还有彩票发行场,贩卖各国的彩票,而尤以吕宋彩票历史最久,风行一时。
宝带门外,一长串东倒西歪破落户的屋,那便是“风光迷人”的烟花间。烟花间是最低级的人肉市场,在此进进出出的全是短打客,偶尔也有被野鸡拉来的乡下粗汉子。
这一切,都时时刻刻地在撩拨着血气越来越旺的杜月笙。
杜月笙20岁时,在潘源盛水果店颇受王国生的重视。他已算是潘源盛的店员,按月可以支领一份薪水,一年三节,还有花红银钱可分。
有了钱,杜月笙先拿去添置了一些日用品,接着便把全身上下来个焕然一新。俗话说:“人凭衣服马凭鞍”,20岁的杜月笙,眉清目秀,身材修长,服饰整洁,说话也比原先流畅几分,往昔那副憔悴褴褛之相一扫而光。
由于经常耳濡目染,平时又肯“虚心学习”,十里洋场的市井少年习气,可以从他一举手一投足间,很明显地看出来。
杜月笙在黄浦滩上混了几年后,仿佛已经脱胎换骨,再世为人。他早已不是高桥镇上窝窝囊囊的乡下小孩子,也不再是高桥街上,三瓦两舍到处打流的小瘪三。他有固定的职业,丰厚的收入,他有些心满意足了。
当然,倘若他能始终保持这种心情,和王国生一直合作,小心翼翼,谨慎办事,以衣食相安为满足,那么,上海滩上也许会多一个成功的水果商,但却永远不会出现一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杜先生了,一个叱咤风云几十年的“教父”了。
然而,上海滩是个光怪陆离、波谲诡秘的花花世界,是一口藏污纳垢、五花八门的大染缸,处处充满诱惑,处处充溢罪恶,杜月笙因其性格本身,而毁了内心中的堤防,投身到了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之中。
杜月笙起先,结交一些年龄相仿的小朋友,杜月笙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好交朋友也可能是杜月笙的天性,也许是因为他幼失怙恃,感情饥渴,急于获得人间的温暖。不论如何,杜月笙一直看重友情,每一个和他结交的人,都能对他推心置腹,当做知己朋友。
住在附近的邻舍街坊,水果市场的同行,有的世属沪上,有的来自乡间,他们都比较纯洁天真,玩不出什么花样。杜月笙和他们相处,反倒显得远比他们成熟。因为他曾受过苦难的磨练,同时又与高桥镇上的一批浮浪子弟深交过,胆子大,谋略多,遇到纷争,敢出头,为双方摆理,能摆平,常常化干戈为玉帛。所以,他在小朋友间渐露头角。
“请月笙哥评评理。”那些小朋友一遇纷争,往往先说这句话。
杜月笙的声誉逐渐在法租界八仙桥一带鸣起。就当年的地势而言,这一地方恰好是大上海的中心地带。
同时,杜月笙结识了几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们自诩是嫖赌两道中的高手,他们经常在杜月笙面前大谈其嫖经与赌经,逗引得血气方刚的杜月笙心痒难忍。开始,杜月笙不停地告诫自己:到那种地方去,干不出好事来。万一搞不好,身败名裂,眼前的饭碗,还可能又要被敲掉。
有一次,有位朋友却和杜月笙打起赌来:
“杜月笙,你要是有种,跟我一起去白相!倘若你能过赌场而不下注,看见光屁股姑娘不动心,那才算你是君子!”
“这算什么?去就去!”杜月笙信心十足地去了。
结果,罪恶吞噬了他。
杜月笙不但下了注,而且越赌越上瘾;不但动了心,而且越陷越深。
进香堂加入青帮
当时上海的赌场,首推豪华奢侈的俱乐部,次属固定地址的中型总会,最下等的是幽僻角落临时摆设的赌棚,以及流动性质随遇而安的赌摊。
杜月笙先从设在马路上的赌摊赌起,掷骰子、押单双,赌法单调,输赢极小。他觉得这太不过瘾,又钻进赌棚去吆五喝六,推牌九,搓麻将,有一度他还迷上了34门押其一,中了获利30倍的花会。从制钱、铜板,他一直赌到角子、银洋。
后来,这赌就成为杜月笙的终身爱好之一。抗战前他在家中每日设局,一场输赢,高达三五十万。
至于妓院,上海的妓院分为三等,长三、么二和低级烟花间。20岁的杜月笙,不敢上长三书寓,也逛不起么二堂子,他只有在那些拉客野鸡、肉身布施的烟花间里流连徘徊。
小东门有个叫陈世昌,绰号“套签子福生的人”,此人胸无大志,干的是赌和嫖两档营生。
所谓套签子,是一种街头巷尾、小来兮的赌博。它脱胎于花会,简单而便利。用一只铁筒,插32枝牌九,下尖上方,作签子状;或16枝分缠五四三二一不等的五色丝线铁签,庄家赌客,一人各抽五支。赌牌九就配出两副大牌,比较大小,赌颜色就比较谁的颜色多。这种小赌庄家多是副食品,如花生糖、苹果等,而赌客输了则付现钱。
“套签子福生”陈世昌,就抱个铁筒子,在小东门、十六铺一带,沿街兜赌;为了谋求保护,他早早地就加入了青帮。还是“通”字辈。
当时,杜月笙想找个靠山,就拜了陈世昌为师,算是入了青帮,为“悟”字辈。
和杜月笙同时进香堂,入青帮,拜陈世昌为“老头子”的,大概有10多个人。这10多位“同参兄弟”中,后来闻名上海的除杜月笙外,还有马祥生和袁珊宝,而其中尤以袁珊宝和杜月笙最为接近。
袁珊宝是上海小东门当地人氏,在潘源盛隔壁的一家水果行里学生意。杜、袁二人少年时期,志趣相投,同出同进,是顶要好的朋友。后来,杜月笙跻身上海三大亨的行列,在华格臬路营建华宅,袁珊宝便盖一幢房子在李梅路,和杜月笙的住宅前后毗连,以便两人经常走动、谈天。
当时的马祥生,比杜月笙、袁珊宝路子宽得多。他是常州人,到上海来谋生路,不久便由朋友介绍,进了法租界同孚里的黄公馆。
学徒在裱画店
黄家世代居住在浙江余姚,祖上没有出过什么人物,在黄金荣之父黄炳泉之前,家世不传。黄金荣父亲黄炳泉年轻时任余姚县衙门的捕快。所谓的“捕快”并不是什么官职,而是旧时在州县的官署中担任缉捕盗匪工作的差役,大概相当于今日的刑事警察。作为衙役的公人,还是生活在社会的较底层。
黄炳泉凭着自己的辛勤工作和破案能力,缉捕盗贼,不仅在苏州站稳了脚跟,而且有了一官半职,人称“性豪爽而慈祥,生平行仁积善明德”。到了此时,步入中年的黄炳泉才得以经媒人撮合,娶苏州女子邹氏为妻。
邹氏一生勤俭持家,一共生育了5个孩子。第一胎生了个儿子,但不幸早夭,老二是个女儿,大名黄凤仙,乳名阿宝,长成后嫁与上海邹家,生子邹金寿。过了好几年,邹氏才生下了儿子黄金荣。第四胎为女儿招弟,后嫁给了徐步洲,有一子四女。邹氏最后一个儿子叫木金,幼时早夭。此外,黄炳泉还有个姘妇,在高桥旧校场开设糕团店,人称“麻子阿金”,也曾与黄炳泉生过一个女儿。
黄金荣排行第三,小名阿荣。1868年12月14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一)生于苏州,这样如按祖籍算,黄金荣是浙江余姚人,如按出身地算,应是江苏苏州人。但是在黄金荣的户籍里籍贯一栏,他一直填的是上海,可见他与上海感情之深。后来黄金荣一直以阴历十一月初一作为自己的生日。当儿子呱呱落地,黄炳泉中年得子,自然异常高兴,取苏州俗语“千金万银才是富,荣宗耀祖才算贵”之意,他便给儿子起名“金荣”,小名“阿荣”。黄金荣出生后,体质十分虚弱,整日啼哭。一日请了个算命先生,这位先生竟大胆预言,这个孩子寿命不会太长。爱子心切的父母急忙从算命先生处讨得“解法”,将他送入佛庙,以托佑于佛祖,当然不久即抱回家中,没有吃什么苦头,只是从此黄金荣得了一个“小和尚”的雅号。
黄金荣的童年因父亲是个捕头,在苏州城里好歹也算个人物,经济上应称得上殷实。“小和尚”吃母亲的奶,一直吃到6岁,倒也茁壮成长。接着,像苏州一般殷实人家的儿女,黄金荣被父母送入了私塾。第一天,私塾先生看到“金荣”两字,不禁摇头,便提笔给他起字“锦镛”。苏州乃书香之地、状元之乡,私塾虽亦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读起,但由于私塾先生要求严格,使得在学业方面没有多少天分的黄金荣痛苦万分。他生性顽皮好动,也给望子成龙的父母添了不少麻烦。
这一年,姑苏城里流行起天花,黄金荣也染上了。虽然平安治愈,但从此脸上多了一些麻子,“麻皮金荣”的绰号即由此而来。
初当捕快
黄金荣随父亲到上海时,才只有12岁。黄炳泉曾出钱,让儿子继续在城内猛将堂内的私塾读书,但小小读书郎耳闻目睹灯红酒绿的上海滩,渐生好逸恶劳之心,三天打渔,两天晒网,没多久黄金荣就停止了他的学生生涯,所以在笔者见到的黄金荣自己填写的两份履历中,一份的文化程度填的是私塾三年;另一份填的是“粗识”。此后便在家里混混。他最感兴趣的是看大人搓麻将,在这方面好像颇有天赋。因为年少记性好,往往大人还没看出好牌,黄金荣在其身后已经会叫一声“和啦”。后来他索性登上了麻将桌,从此一生与赌博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然赌场没有常胜客,甚至有时输得只剩短裤衩回来。看儿子如此荒唐不成器,黄炳泉想:“家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便在儿子虚岁17时,将其送入姐夫开设的裱画店。
在裱画店,黄金荣除了烧柴炉、做饭菜外,就是调糨糊、裁纸张,收入只有月规钱50文;因为是在姐夫开的店里,没遭什么打,但对装裱,黄金荣也没有多大兴趣。好不容易熬了三年,黄金荣终于学徒满师了。那一年黄金荣19岁,据说可以有9600文的工资。但他显然是不喜欢在店里受姐夫的管束,他心中向往的天地比这一间小小的五尺店面要大得多。父亲没奈何,又托人让他进了可以开些眼界的萃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