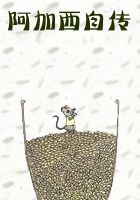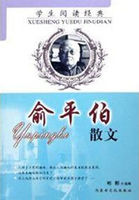别看戴笠只是个上校,其实权势可大多了,有许多县长、团长都被他罗致到门下,作为部下驱使,而且有人是******直接安排给戴笠的。1935年,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团长杨继荣突然接到命令,让他到庐山见******。******见他后,没问什么话,只是告诉他:“戴科长的工作很重要,你去帮助他。”就这样,杨继荣成了戴笠的书记,也就是秘书。
在特务处,戴笠把黄埔学生都“摆到表面上”充充样子,然后从社会上广泛搜集各种三教九流的人才。当时,参加特务处的手续很简单,只要填一份履历单,由介绍人签署意见,再报上级批准就可以办理手续了。但后来,手续逐渐严格起来,要填报名目繁多的履历表。申请人被批准吸收后还要组织宣誓。
这个宣誓仪式颇有几分滑稽:宣誓人面对******的肖像,桌上放一本《三民主义》和一支手枪,说道:“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宣誓之后,从此便互相之间称“同志”。
戴笠规定,对加入特务处的人,不得发给任何证明和文件,只是在人事部门和工作单位具名而已。然而,加入者从此不得再脱离特务处,也不得请长假或辞职休息,戴笠把这称为“生的进来,死的出去”。
在戴笠的控制之下,特务们无不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没人敢与戴笠为敌。而“生的进来,死的出去”,后来一直沿用,成为军统的规矩。
1932年,戴笠的特务处已发展到100多人,各方面开始初具规模。1933年以后,特务处逐步设立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大区以及各省的基层站,还开始向日本、朝鲜、美国、德国、意大利、越南等国家派出情报人员。特务处已开始得到长足发展,并逐渐显示出它的力量。
“嫡子”与“养子”
与此同时,“特务处”的竞争对手、国民党另一个特务组织“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1935年升格为“党务调查处”),也在南京瞻园路的办公处积极工作着。
******手下历来有三大政治派系:政学系、CC系和黄埔系。政学系多半为辈份较高,政治经验丰富的国民党元老级人物;CC系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代表,掌握着党务和文化教育大权;黄埔系则以复兴社为代表,他们虽然班级辈份低一些,但组织严密,下层力量雄厚,权力欲和排他性强,向外进攻凌厉。
戴笠的“特务处”属于黄埔系。而“党务调查科”为陈立夫兄弟所掌握,以徐恩曾为科长,属于“CC”系。“特务处”与“调查科”,是当时旗鼓相当的两大特工组织。
从时间上来说,CC系的调查科成立在先,戴笠的特务处成立在后;从发展的速度上来说,特务处发展更快,调查科发展较慢。特别在行动工作方面,调查科显然比不上特务处更有成绩。此外,调查科只在南京、上海、九江、汉口有行动表现,而特务处的行动成果已经遍及全国。
为此,在1932年夏天,CC特务系统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专门检讨与特务处的斗争问题。在会上,陈立夫等人都认为戴笠的特务处“后来居上”,调查科的破案率只及特务处的十分之一。
这次会议后,CC特务系统决定成立肃反委员会,又计划成立东南、西南、华北、华中、特区等五个分局,准备与戴笠抗衡。而特务处和复兴社因自己的蓬勃发展而洋洋得意,根本不把“调查科”放在眼里。
“复兴社”自诩为******的惟一嫡系,而把CC系看作是******的“螟蛉子”。而在CC系眼中,复兴社只不过是******的“保镖”,他们居然也想染指政权,CC系当然不能同意。
在初期,戴笠与CC系斗争时,双方还顾及到一些面子,没有撕破脸皮,只是在暗中着劲较量。相互通过各种方法,抬高自己,贬低对方,以便把对手踏在脚下。不过,派系间的明争暗斗,简直成了双方组织活动的重心。有时,他们对付“异党活动”只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但碰上两个特务机关之间的明争暗斗,却是劲头十足,斗志昂扬。
有很多文艺作品,提起戴笠,人们就认为他是反共高手。其实,要论起反共,戴笠的特务处却是甘败下风,而CC系更胜一筹。
首先,CC系把最有水平的一批高级特务,放在主管反共斗争的第二组。在对共产党的理论研究方面,CC系也有一套高明的办法,这就是搞小组学习,要特务们读马列主义书刊,讨论共产党的建设,甚至有专人负责深入钻研《联共党史》。相比起来,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十分封闭禁锢,以至谈“马”色变,谈“红”色变,这就降低了他们“反共”工作的实际能力。
再次,CC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劝降”技术,他们对被捕的****党员进行“劝降”审讯的时候,一般都是心平气和地“说理”,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来“辩驳”马列主义,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促使其叛变革命。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甚至亲自用刑逼供比较起来,也有水平高下之分。
此外,CC系特务们一旦发现共产党基层人员,并不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进行引诱、威胁,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内线“细胞”,然后扩大战果,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入高一级的****组织。而特务处对付共产党,往往是发现一个抓一个,如果再严刑逼供至死,这条线索就断了。
正因为CC系特务在反共方面有这些“高明”的手段,在上个世纪整个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CC系特务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尤其是反共方面,CC系特务组织无疑是权威机关。
而对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来说,他们向来看不起“小瘪三”出身的戴笠,认为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做法是“土匪作风”。不过,陈立夫虽不满意戴笠的做法,但从不公开批评,只是常在闲谈中讥讽奚落对方。
比如,有一次在特工训练班上,陈立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立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戴雨农欢喜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如果便衣武装能代替一切,那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
戴笠何尝不知道CC系对他的态度?于是,他也处处与CC系为难。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CC系的势力出现,复兴社的特务们就要打上门去。
此外,CC系特务组织所属各单位要搜捕和处理人犯等,必定要经过各地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而警察机构大多掌握在特务处手里,戴笠就借此与CC系为难。只要是CC系提出要捕人,警察机关总是千方百计予以掣肘。30年代中期,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因而上海市的警察机关成为双方斗法的场所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戴笠和CC系之间的斗争也就越加尖锐,以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也知道,“亲儿子”与“干儿子”打架,自然会削弱特工系统的总体力量,他认为有必要将其“特务处”和“调查科”统一起来。于是,他下令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任副局长。局内设3个处,其中军警处为复兴社特务处的全部人马,处长由戴笠担任。
1935年5月4日,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园,其中戴笠的二处,地址仍设在南京鸡鹅巷53号。
这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虽然和后来出现的“军统”同名,但并不是一个机构,实际上它仅仅是一个被架空的机构。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内部就没有停止过明争暗斗。特别是一处与二处之间,仍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
陈立夫本来就看不起戴笠那一套粗鲁和穷凶极恶的做法,他认为,特工工作应该讲究技术。现在把戴笠的特务处隶属给自己指挥,可是自己又抓不住他,这使陈立夫更加恼怒,于是,他对戴笠处处予以抑制。然而,戴笠有******这个大后台,陈立夫也是奈何不得。
其实陈立夫清楚,蒋不会同意让CC系把戴笠的特务处吃掉,当然也不会同意让特务处把CC系的特务系统吃掉,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只要不危及到蒋手中的权力和地位,蒋不但会默许,而且还希望有这种矛盾存在下去。
戴笠处处与CC系为敌,使CC系感到如鲠在喉,咽不进,吐不掉。CC系头子陈立夫深知******的一贯手法是要使两大特务系统互相掣肘,以利于其掌握运用,以防形成尾大不掉,权重震主。
CC系的特务们有时与戴笠摩擦吃了败仗,陈立夫总是对特务们晓喻说:“人办事,要用脑筋。用脑必目有所见,耳有所闻。而且,耳与目不能只有一个,必须有双耳双目,才能兼收并蓄。因此,情报机关必须同时有两个,才能心明眼亮,决策无误。作为领袖的耳目,也应有两个,兼听则明嘛!”
不过,在这场斗争中,因为陈立夫的一个疏忽,形势突然向着有利于戴笠的方向发展了。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时,陈立夫的得票竟然比******还多4票。陈立夫自然不敢和******一争高下,他立即亲自在黑板上擦掉1个“正”字,成为比******少1票。
戴笠知道其中必有缘故,他派手下人多方调查,得知是陈立夫利用CC系的力量操纵选举,于是他搜集了很多CC系在会中幕后活动的证据,向******奏了一本。******当即就下令把陈立夫扣留起来。
陈立夫耳目众多,他提前知道了消息,马上躲进天目山“养病”,然后托了许多“重臣”元老向******求请。他甚至动员了自己的叔叔陈其美关系。当时,陈其美的独生子学习驾驶飞机摔死了,******也为之惋惜不已。陈其美的夫人就向******哭诉说:“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胆子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陈其美)绝后吗?”
******只得原谅了陈立夫的“死罪”,不过,从这以后,他就下大力削弱CC系特工的力量。而戴笠则不失时机地反扑。
这时,戴笠派到德国考察纳粹特工技术的唐纵回国了,他向戴笠详细介绍了德国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领导的一个专门窃听电话、破译密码的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每年监听电话和破译密码4万份以上。
戴笠听了唐纵的介绍,发誓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同样不逊色的研究所。当时,******同意将原先在各大城市秘密进行的邮电检查转变为公开的活动,并挂出了邮电检查所的招牌,由调查统计局三处主管。戴笠一心想把“邮检处”抓到自己手里,当他得知戈林的研究之后,更是有意效仿了。于是,戴笠一方面向CC发动凌厉攻击,一方面向******不断揭露CC控制邮检处的黑幕,要求取得邮电检查的垄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