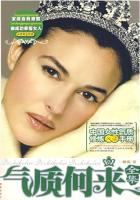现在,他们挨得很近,靠得很近,几乎挤在一起,亲密无间,落落大方。一会儿,又稍稍拉开点缝,断开点小距。亲近而不轻佻,亲热而不狎亵,亲昵而不出格。
一阵不加掩饰的畅怀的笑。笑声过后,他?她?先哼起了令人惬意的流行曲,软软的,甜甜的,醉醉的。当我感觉到是歌声的时候,浪漫的旋律已像两只灰鸽子一样向碧空飞去。……此刻,不唱了,不笑了,只是静静地行走。他们的内心在想什么呢?他们在想这个人类赖以生存而又刀光剑影的世界上他们是多么自由幸福么?他们在想人的青春多么短暂,而他们短暂充实的青春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么?
也许,他们什么都不想。
我感到庆幸,觉得宁心悦目。我纵意放慢脚步,静静欣赏他们勾勒在雪地上的倩影。雪野很圣洁。雪野小路纯净而美。我想起法兰西作家于勒·列那尔的啧叹:“自然界是真实、生动而纯净的世界。”同时感到,雪野小路上的他们使大自然逢荜增辉。
我羡慕这样年龄的他们,连他们思索中的孤寂也感到羡慕。当然,我在羡慕中也有一种淡淡的惆怅和莫名的妒意。我哀叹我和我的许多同龄人,我们没有激荡不安的青春,没有这种伊甸园般的快乐的初恋。我们的青春在无休止的政治风暴中泯灭了,连那几乎刚刚滋生的脆弱的情窦之苞也全被那春寒扫落……
他们是勇者,是另一代人。一种新的介质已注入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屑一顾的和古老抉别。他们内心迸发燃烧的是他们自由点燃的爱的焰火,他们周身流淌的是他们自己的青春血液。他们不像我们那么盲目,轻信。我们过了大半生,却连那幸福的一刻也不曾有过。当我们三十多岁晚婚的时候,我们才发觉自己似日暮乡关中归来的人,不由生出几分淡淡的失落情绪……
皮鞋依旧嚓嚓的。高跟鞋响得更脆。
藏蓝色、淡褐色,好像并不谐调,却各有特彩。我喜欢他们这种独具个性特点的不谐调风格。我想,男的就是男的,应有男子汉的气度。女的就是女的,应有当代女性的风采。
当代摩登青年,也许就该这样打扮,也许本该这样打扮。我很自信我的这种赏识。
背影,始终是两团模糊跃动的淡褐色、藏蓝色。直到丁字形的路段,才转过摩登青年的脸庞:一张,俊美脸颊下束着手工精巧编织的雪白的围脖。另一张,面孔饱满健朗,眼里溢着和煦之光。
在融积薄水的一道冰河上,她险些滑倒,他迅疾伸出手,一个美丽的冰上圆舞曲动作。两张笑语盈盈的脸庞,引人想象他们相濡以沫的感情,相敬如宾的未来,和他们勃扬着血、肉的强盛的生命意识。
乡间小路无休止的长。山谷雪野纯净无尘。又是一道闪耀银光的冰河,便显出黄土高坡上拉拉撒撒的村庄。那对摩登青年,离开小路,慢慢拐向缓坡下的一家窑院,最先迎接他们归来的是一条大花狗的汪汪声和摇头摆尾的热情。——齐崭崭的三孔新石窑,雪白的新窗纸耀出鲜艳的红窗花。大门上赫然映着大红对联:金屋笙歌偕引凤,洞房花烛喜乘龙。横匾是:珠联璧合。
我凝视良久,唤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涨潮般的欢愉……
这伊甸园般诱人的乡间雪野小路!
蝉鸣夕阳
什么时候,我才发现那蝉声变得这样迟滞黯哑了呢?依然是这棵高高的白桑,青叶临窗荡漾;依然是这蝉声,却这样聒噪,听来索然无味。
记否,整整一个夏天,它那不知疲倦的鸣唱是何等嘹亮和富有生气呵。现在却衰落了,颓废了,衰落颓废得令人沮丧……
我曾疑窦是这酷热季节之故。烈夏的最后日子裂变它全部的热核横意杀生,万物皆失去神儿。狗们羊们在那荫凉下躲藏着伸着长舌,躁动不安。收割后的麦田,不断散发出浑浊滞重令人窒息的燥气。或许,是自己不能涂抹出理想的文字之由,那些日子我是怎样含辛茹苦墨迹驳斑勾划着,陷入一种怎样的过去不曾有的孤独的困扰呢。但不是,那往日响亮的蝉声确是变得迟滞了,暗哑了,因为我很清醒,至少,我还没有失去理智或变得过于神经质。
往昔,它曾像小酋长国里的国王,骄傲地霸占着院落这一方碧叶荫翳的天地。那阵阵陡然而起的炽烈奔放的歌声,曾令人神怡。
窗前小院那棵白桑仿佛它的守护神,那只蝉则总像守望者一样栖身在这棵白桑的这个那个任它挑剔的枝桠。华盖蓬松,浮层厚厚白霜的桑树躯干上时时清晰地显出它的赤裸来:一只体格肥大通体铁青色的蝉,它的背部天然地雕着奇妙的褐红纹斑,羽翅轻柔得似初冬第一履薄冰般美丽。当黎明宁静的朝霞在远山刚染出一片绯红,它的鸣唱就开始了,先是低低的初试歌喉,“唔—儿,唔—儿”,随着便一声一声抑扬顿挫变化起来。许多时候,它则沿着树干缓缓爬行,一副自由自在超然度若的样子,鸣声低婉、闲适,似一泓纯净隽永的竹林流溪弹奏。每每拨墨弄文之余,我常静静坐在窗前,品味寂寞中的这歌声,很觉几丝慰藉,几丝享受。老实说,它不逊于任何一支抒情小夜曲!它缓缓地扫去倦意,勾起人一种宁馨而悠远的想象。有时那鸣叫又是那般热烈急促,似冲锋的号角疾驰的马蹄,那一刻,它劲鼓得多猛,尾部一翘一翘不停息地翕动,显示出一种强悍的不可征服的雄性之气。哪一只蝉偶尔飞来这里的领地了,都会被它震慑的。我亲眼所见,它曾挑衅般地追向那些落来的蝉儿,羽翅疯狂翕动,(我断定那一定是一种蝉们世界的不友好的挑衅)直至同类惨败地溜出那片领地。——多少次我为蝉界这种驱逐而惊奇,记得先辈散文高手朱自清在他的《荷塘月色》中曾生动描述过溶溶月色下热闹的蝉声,那真是妙极了,可人们谁曾发现过这温驯的小物儿竟会陡然发起攻击的奇趣妙闻?
这酋长国里高傲的国王!多少朝晖辐射的冉冉丽日中,那蝉鸣相伴透彻地给这个新鲜天宇带来一种潇洒,一种生命意蕴!“垂緌饮清露,流响出梧桐;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我曾细细体味那蝉儿的每一声音符,细细领悟古人笔下的每一缕诗韵,是呵,“饮清露”,“鸣梧桐”,不趋奉权势,那是何等清洁、高贵的形象,何等独立孤傲的气节!而此,概是因它栖居之高,才鸣声远播啊……
这小牲灵给人一种伟大的人格和人气的启迪。
可现在它却这样令人悲哀地无可挽救地衰落……
那鸣声早已变得断断续续,显得那样气力不足,“唔——唔……”如老牛破车砸过,听来烦噪、单调。甚尔那一次次黄昏落幕中,那每一声蝉鸣都使人森森感到晚照在向我逼来,虽然我这年龄本不该产生这种“秋风茅屋”的破落情思的。
往日那种眷恋错过季节,它已叫我彻底失望。
偶瞥那老蝉,苍白、臃肿、老态,总是老常时间一动不动地躲在一个地方。或许见它懒散地蠕动一下,也早已失却先前那种机敏和英武了。回忆起它逐赶同类,我甚尔涌出些淡淡的悲来……
我再也懒得听它了。
初秋经黄昏的几阵暮雨而来了,“天凉好个秋”!骤然感到扫去郁闷的清凉爽快。一日,又传出那种不堪容忍的时断时续的叫声。我悻悻然:那是它的“晚钟”、“晚鸣”,是它最后撒向这个世界的没落挽歌吧。
那鸣声日后又多次勃起,多次停顿,音宇不成体统,我早已厌烦之极,懒得去想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声音存在……
数日后我从树下过,偶仰起头,蓦地发现了一种不同,原来那枝桠间爬行的是一只深褐色的胸围柔黄的美丽新蝉,它在悉率响动的叶子上啜着,旁侧还粘着一个新蜕的轻柔而透明的蝉衣。和那只脊背斑红的铁青色老蝉完全不同,新的!它什么时候悄悄取代的呢,什么时候已默默孕育这样一个新生命的突破呢,刚才,或者这多天是它在叫吗?还是……我怎么压根儿一点也没觉察出这更替的变化?我还误为那断断续续残残缺缺的鸣叫全是那老蝉呢。这令人混淆的“最后”又是“最初”……
可不少时日了,这只深褐色胸围淡黄的蝉儿仍奏不成一曲完美乐章,叫声总是稚嫩羞涩,我不禁担忧它的生命旅途来,也恍惚念及起那只老蝉的当初来……
也许,是我太迫切了。它现还不成熟、不壮实呢,我压住莫名的怅惘悄然替它开脱,默默等待会有那么一个属于它的时刻……
又是一个美丽而清爽的黄昏,我正独步小院,悠然远眺那青山晚照,突然,一阵清新响亮的蝉鸣在桑林响起,“唔——儿,唔——儿”……每一声都雄健得扣人心弦,每一声都快慰得令人振奋。那高昂的鸣声似乎要征服整个高原,那是它完全成熟了的自豪鸣唱!
这令人自信而豁达的蝉声,一扫忧悒,沉闷,慵倦。那一刻,如同刚刚封闭在琥珀里的小昆虫一样,一下在我记忆里封闭下一个新鲜活泼的印象。
我大彻大悟了:新的一代在开始时也许不如它们行将取而代之的一辈,难担同类对它寄予的厚望,甚尔叫人难以分清新老衣钵。但那仅是极短暂的过程,它们完全会成熟起来的。最富于生命力和独创可能的,永远是无可争议的后来者,自然、历史和人类物类不都是这样一次次演绎、延续的吗?夕阳中的蝉声,阵阵给我如许启示……
豆角丝丝
这就是我播种下的那几棵芸豆吗?它居然悄悄长起来了,居然爬过垛在房檐下的那几棵小竹竿,攀上那高高的房尖顶端。菱形的绿叶间,淡青的茎蔓儿上,挂着一串串交织起来的洁白的、晕黄的、淡紫的、橘红的小花。丝丝水淋淋的荚,在叶片下,在茎隙间,羞涩地藏着,拥挤地缀着。挨胚部的几串荚显然已早熟了,黄黄的,干皱皱的……
我的可怜的芸豆!
面对着它,我的心真有些颤动了。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有你这般的么:被人久久遗忘,且结出饱满丰硕的果的么!诚然,它是那般纤细,不比邻里菜园黑黝黝的茂,虎势势的壮,可我,对它又能怨艾什么呢!人家舍得本,舍得气力,料理成一排排瓜棚式的架架呢!谁像我这般草率……
还是春上种瓜种豆时节。一场春雨过后,人们都忙着操务起自己的小园子来,我一时兴起,便也在房后垦出片隙地点了豆。菽类本不是什么贵重物,易种,易活,不久,那鹅黄鹅黄的萌芽就拱破地皮,冒出嫩绿来了。就在这时,我被抽去一个偏远县境下乡。记得当时拿出几根细竹竿,原是准备架一架的,无奈苗苗儿太小,不宜插竿。走得又匆促,便顺手将竿儿立在檐下了。
夏天,是个多风多雨的季节,夏天也是个酷热灼人的季节。整整一个夏季,我的芸豆儿,它是怎样忍受暴雨的袭击,怎样耐着三伏骄阳的燎烤,怎样抗着饥饿贪婪的菜素螟蚕食吞噬的呢!
记得乡下一个乌云密布的午晌。雷电撕开了铅一样沉重的云幕,铜钱大的雨没命地倾泻着,间或,还劈哩啪啦夹杂着冰雹。我猛然看到,住舍前的菜园,那一大片爬上架儿的碧绿葱茏的芸豆,在烟雨里怯生生地、惶惑惑地哆嗦着、抖瑟着,最后终于东倒西歪地全部乱倒在泥水里……
我的心猛地抽搐起来。我的芸豆儿,它也是这般的可怜吗?不,怕要更狼狈的。我没有施过肥,没有给搭过架,它那纤弱、瘦小的身子受得了如此的折腾吗?我心灵上恍然掠过一种负疚之意:如此寡淡,如此残忍,这样的杀生,还不如当初不种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