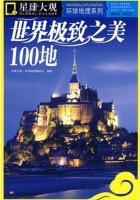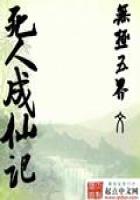崇明是长江夹带的泥沙在长江口冲积而成陆的,在唐代时还是沙洲。据资料介绍,崇明一有人烟,即有人建庙兴寺,宗教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崇明最有名的庙宇是寿安寺,乃创建于宋朝淳祐年间,屈指算来,已有700多年历史了,堪称崇明著名古刹。
我没有考证寿安寺的兴衰史,但眼前的寺庙显然是近年修复的。兵乱毁庙,盛世建寺,历来如此。
大雄宝殿等气势恢宏的建筑其油漆似乎还未干透,不过殿前并排而耸的两棵古银杏无疑是旧植。我对植物向来有兴趣,望树估算,猜测有三四百年树龄,后见一石碑注明“清植”,树上有一牌标明三百多年。可见这寿安寺在清代时还曾兴盛过。
中国的佛教庙宇,大体格局大同小异,这座寿安寺目前名气远不如灵隐寺、静安寺、白马寺等,但哪想到其实极有特色,是一座藏而不露的寺庙。其最大的特色是寺中有三尊玉佛,两尊坐像,一尊卧像。据寿安寺方丈广愿介绍:1999年4月,缅甸华侨陈梁传先生因佛缘所致到崇明考察后,慧眼识宝,称道寿安寺座落之处为难得的风水宝地,当即拍板捐赠玉佛一座。5月初,陈先生即赴缅甸境内,亲临伊洛瓦底江支流登勒湖旁的石竟玉矿,寻得一块30吨重的缅甸玉,并特聘30多位缅甸祖传玉匠,精雕细刻,终于在这一整块玉石上雕成了一尊重达15吨,高3.7米,宽2.2米的大佛,以及高37厘米,宽22厘米的小佛250尊,创了上海地区玉佛之最。同年8月28日大吉之日玉佛顺利运达寿安寺,是日下午3时20分左右,正当玉佛落座之时,天空祥云顿聚龙状,龙身横贯于寿安寺上空达半小时之久,令上千名目击者惊喜不已。此事听起来有如神话,未亲眼目睹者是很难相信的,但广愿方丈并不多言,只默默地把当时摄下的天空云彩照片相赠于我,照片上确有一状似龙蛇形的白云带,那一节节的脊椎清晰可辨,那鳞爪也肉眼可见,只是那龙头隐隐约约,已不甚清楚,不过也算有点模样,不知是巧合呢,还是穿凿附会。联想到几年前我应邀去参加太仓南广教寺的开光仪式,天空也出现过类似的祥云,曾亲眼目睹过数千人跪地磕头,顶礼膜拜,冥冥之中有些事真的说不清。我辈不是佛门之中人,且抱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姑妄听之的态度吧。
寿安寺内另有一座玉雕卧佛,重13吨,据说花费了三千多万呢,那佛相庄严中透出慈祥,其整玉巨无霸似的硕大无比,已是一宝,雕成如此精湛的玉佛,更是宝中之宝。寿安寺的玉佛早晚会吸引众多善男信女前去叩首跪拜,许愿还愿的。
在方丈室里,我还见到了1989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视察寿安寺时留下的墨宝“如来无量寿,净土万年安。”把“寿安”两字藏于结尾,乃得道高人之语。更使我意外的是我还见到了江泽民的题词“晨钟暮鼓警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途人”,我再仔细一看,边上有一行小字“录江泽民白马寺题词”。
临别寿安寺时,我与广愿方丈在佛像下边合影留念。回望寿安寺,前有玉佛楼,后有金鳌山,乃“金玉满堂”的风水宝地,那山上的镇海塔更是与寺庙相得益彰,互为风景,引人流连忘返。
喜欢朱家角的理由
江浙一带的历史名镇周庄、同里、乌镇、西塘、南浔我都去过了,唯青浦朱家角几次擦肩而过,这次总算如愿以偿跑了跑。
若用最简洁的话来总结朱家角之游,那可以把它概括为“名符其实,不虚此行”,是最最贴切的。
说实在,笔者跑过不少地方,有些地方被宣传炒作得这好那好,及至身临其境,方知上当受骗。
朱家角比我想象中大,比我想象中古,比我想象中有看头,比我想象中有味道。
上海民间向来有“三泾不如一角”的说法,看来是确乎不虚此说。
我未去朱家角时,想当然地认为朱家角一定很偏僻,用上海方言乃“幺尼角落里”,要不然怎么会起镇名为朱家角呢。朱家就算大户人家,又能大到哪里去呢,更何况只是一角。后来读了朱家角乡贤清代的周郁滨撰写的《珠里小志》才知,朱家角原名“珠街阁”,小名“珠里”,雅得不能再雅。然后叫着叫着就叫成了朱家角,这实在是俗文化战胜雅文化的又一例证。
作为一个水乡古镇,“朱家角”打旅游牌已形成气候了,既有古街古巷、古桥古寺这些历史遗迹可看,还有放生桥下的放生等民俗活动可观看可参与,商业气氛也恰到好处,既不显冷静,也不嫌繁杂。
其实朱家角在历史上就很繁荣的,与相对封闭的周庄不可同日而语。据志书记载,朱家角在明清时“水木清华,文儒辈出,士族之盛为一邑望”;“商贾云集,贸贩甲于他镇”。
我喜欢朱家角的理由有三:
首先是古树惹人思。
进入朱家角就能在慈门寺旧地看到两棵银杏树,两棵古树比肩而立,一瘦一壮,估计上一雌一雄,难怪当地人谓之“银杏夫妇”。在这两棵银杏树下,有一青石碑,上刻树龄“400年”字样,因此游人都误以为这两棵银杏乃400年树龄,其实,作为慈门寺旧植,这两棵银杏树至少有700年以上历史。因为慈门寺始建于元代,而古银杏树下的那块“树龄400年”的青石一看其风化程度,就可知也是文物年纪的老货了,若加上立碑到现在的数百年历史,这古银杏的树龄恐怕又要翻番了。
这两棵银杏树各有特色,一棵高大挺拔,叶茂枝壮;且有一株横挑枝平伸前探,造型之美,极为难得,适宜入镜入画。另一棵一侧呈枯焦状,似已枯死。据介绍此银杏为抗战时日寇炸弹之引起的大火所伤,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此银杏树才枯木逢春发新枝,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时,此株银杏再次死一回。十年后,粉碎“四人帮”,这株有灵性的古银杏又迎来自己的春天,又一次苏醒复活,成了当地百姓心目中的神树。
古银杏的几度兴衰,惹人思悠悠而想得很多很多。
其次是古桥惹人爱。
朱家角是水乡古镇,其水面颇有特色,或宽或窄,或直或曲,变化多端,不复雷同。因了水多,桥亦多,因了水面宽窄曲折无定规,桥亦或拱型、或条石型、或石桥、或木桥、或木石桥,还有廊桥,而石拱桥又有单孔、三孔与五孔之别。
给游人印象最深的当数放生桥,不仅仅此桥建于明代,距今433年,更难得的是此桥全长70.8米,被誉之为“沪上第一桥”,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之桥。摄影家、画家对此桥无不情有独钟。近年不少导演也对此桥另眼相看,多次出现在荧屏、银幕。
惠民桥虽窄小,却是座廊桥,这在江南已不多见了,加之《廊桥遗梦》的影响,总给人温馨、浪漫的感觉。雨中也能过桥,溢出一种人情味来。
平安桥的特色是质朴、自然,桥上的栏杆是整根的原木,可靠着小憩,透着一种以人为本的便民、惠民思想。此桥又俗称戚家桥,相传戚继光行军路过所造,这恐怕是附会之说。因为据我了解,戚继光并未在青浦这一带抗倭,戚继光抗倭主要在福建、浙江,可能戚将军的名头太大的缘故吧。假若是秦桧,是汪精卫,想来避之不及,决不会附会上去吧。
朱家角的桥很多,比之周庄之桥,历史要悠久得多,假若当年陈逸飞看到的是放生桥,又画了放生桥,那么我想,朱家角的名气大概远胜于周庄了。
最后便是古风惹人喜了。
真的没想到,朱家角竟然还保存下了大清邮局,这邮局大约有100年历史,据介绍是华东地区唯一保存下来的清代邮局。这说明两点。一、100年前,这朱家角是挺繁荣的;二、近百年来朱家角的发展是缓慢的,要不,早就荡然无存了,哪还能保留原址。
还有老的酱园、药号都原汁原味地恢复了,且照常营业,让老年游客过过怀旧之瘾,让年轻一代实地考察了解一下逝去年代的商业面貌,不也挺有意思。
当然,朱家角最有特色,或者说最让游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放生桥下的放生风俗。有不少当地人趁机做起了出售小鱼的生意,五六条小猫鱼卖一元,三四条小红鲤鱼卖五元,如果从放生桥顶端的龙门石上把鱼倒下去,谓之“鲤鱼跳龙门”,不少游客为了拍张放生照而去放生,其实这与放生的原义已相去甚远。
这儿,在明代时,原为慈门寺放生之处,据《珠里小志》记载,桥下方里许禁止渔人下网捕鱼的,即便渔船也不得停泊。
大概几百年来此桥上游下游不准捕鱼,故成了鱼儿的乐园。据地方志记载,清代时,放生桥下有老蚌,长二丈许,时浮水面。有善泅者近之,喷沫如冰,冷侵肌骨。中秋夜,老蚌游之波心,其蚌壳的珠光与月色相激射,自成一景,可惜,这样的奇观已久违了。
当然,朱家角好玩的地方还多着呢,但对我来说,有此三诱惑已足够了。
朱家角真的是值得一看的。
朱家角桥上的石榴
朱家角是上海郊区水乡古镇。水乡看桥,往往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故朱家角一带流传这样一句话:“到了角里不看桥,等到于角里勿曾到”。角里是朱家角的旧名,可见当地人也十分看重他们镇上的古桥。
其实,桥各地都有,有水即有桥,这不稀奇。江南其他古镇的桥并不比朱家角的少、比朱家角的差,甚至比朱家角的桥还古老,像我家乡太仓就有五座元代的石拱桥。但朱家角的桥有一大特色,却是其他古镇之桥统统没法比的——那就是桥身上长有一两百年、两三百年的石榴树。如明代万历十二年建的泰安桥两侧各有一株石榴,推算下来有420年了,俗称夫妻树,长得枝繁叶茂,与桥身浑然一体,自成一景。而始建于明隆庆间的放生桥,五孔花岗石大桥,全长70.8米,这在全国都罕见。隆庆皇帝在位仅六年,即便隆庆六年造的,也432年了。此桥的石榴虽不及泰安桥的古老,却以多取胜,两侧加起来有六七丛昵。据我对植物的了解,这些石榴应该有一二百年历史了,因为桥缝营养有限,生长艰难,要长成如今这模样,绝非十年八年能长成的。无论远望近观,那一丛丛石榴都己与石桥相依为命,融为一体,融为一景了。
关于石桥中的石榴,游人大都以为乃鸟类啄食石榴后拉屎拉在桥缝中而慢慢长出来的,因为在其他古镇的石桥上,也长有枸杞、构树等,这个推理似乎言之有理,其实不然。查当地风俗可知:朱家角人造桥,那些工匠注重口彩,所以在砌石块时,用糯米浆拌石榴籽合缝,石榴谐音“石留”,石留自然桥固。没想到石榴籽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在糯米浆的营养下,终于破缝而出。在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中,长成了如今这造型。真应该向这些崛翠无畏的石榴致敬。
写到这儿,我又想起前不久报载:北京昭陵城墙上有松柏长在砖缝里,有人建议伐去,以防古城墙的损坏,有专家坚决不同意砍伐,最后北京市长王岐山一锤定音:保留!——好!我为此明智之举喝彩。因为石桥也好,城墙也罢,毕竟可修复,乃至重建,而树却很难再生。数百年来,物种靠顽强的生命力,艰难地生存了下来,这容易吗?更何况它们己与桥,与城墙难分彼此,互为一家了。这是自然景观,更是活的文物啊。
砍伐果然是保护文物之一法,但必竟是消极的,共同保存、整体保护,这是难题,却是大有意义的。
作为读者,作为游客,我只希望主管领导中,多一些像北京市长王岐山这样有文化、懂文化的领导。
张溥是朱家角的女婿
游览青浦朱家角时,买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版的《珠里小志》,这是清代时朱家角的乡贤周郁滨撰写的一本乡镇志。回来后,我饶有兴趣地翻读了起来。竟在卷八读到了“按元初张瑄、朱清督理海运,招致海舶,太仓称为六国码头”等,我立时兴趣大增,细细阅读了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卷十三,意外地又读到了一段关于张溥的文字。“张溥,字天如,太仓人,为珠里陆氏婿。少时常在甥馆,所读书必手自抄录,有录至六七过者,故名其斋曰‘七录’。崇祯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乞假归,与同里张采创复社,里人陆文声,闽人周之夔忌之,指为党魁。提学御史倪元珙、兵备参议冯元扬,太仓州知周仲琏、巡抚张国维等申救,元珙诸人皆被斥。及溥巳卒,事犹未能竟,屡诏诘责。采奏溥未服官,怀忠入地;而御史刘熙祚、给事中姜埒亦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疏上,事始得解。溥诗文敏捷,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卒年止四十。”
《珠里小志》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距今200年左右,编撰者周郁滨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家乡的诸生,《青浦县志》称他“不营名利”,他与张溥既无亲戚关系,又无师承关系,因此他的史笔更具真实性、客观性。
从《珠里小志》的这段文字记载着。陷害张溥的,不但有太仓人陆文声,还有福建人周之夔。所谓树大招风吧。读此文后,我一则为太仓出陆文声之流的小人痛心,一则又为张溥为家乡为前辈欣慰,因为主持正义,援手张溥的不在少数,且一个个有名有姓,有官职,看来绝非虚言。张采、姜埒等文化人与张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好理解,没想到太仓的知州、提学御史、兵备参议、巡抚等大大小小地方官都为营救、平反张溥而甘冒上峰斥训之险,委实难得,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张溥的影响,以及他的人缘、人气。
《珠里小志》里还有一则涉及张溥的轶事,也颇有趣味。且抄录如下“时有僚婿某官总兵,意气傲岸,天如时为诸生,某视之如蔑如也。后天如入词翰,乞假归道,经某地,总兵适任于此。明季重文轻武,词苑声望尤重,总兵戎服谒见,亲为巡更。天如因作小诗寄外氏,有‘碧纱帐内一书生,卧听元戎击柝声’句,传为佳话。”
以我看来,这位总兵还是很可爱的,他对有成绩有声望的文化人还是敬重的,因为身为总兵,亲为巡更,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在《珠里小志》上,能读到张溥的些许文字,也是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