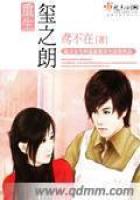是啊,他们的气血方刚,感情像永不枯竭涛涛东流的河水,舒适而其乐陶陶;他们的情感是那么纯真,热烈,忘我和无私;他们的感情是那么兴奋,那么激动——包括他们的眼睛也在燃烧。而这些动感情和思维,精神以及气血交流,是人生爱情的追求。而这种爱情是无法形容又难以言尽的。
“叶哥,人生男女之间的爱,可有意思呢!”“假若你心中没我呢?”他会心地笑了。“我总不愿离开你,短暂的相离,也让我很难受。”
他说:“兰,我们要把爱情做为激励与鼓动学习的手段和推动学习的维系好吗?”“多好呢。”江兰点头回答。
时间是不可思议的,它不仅在改变着人们的外表,也在改变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就连体态、面貌和言谈举止也在变化。幼年时的小叶、江兰,与成长中的今天相比,简直是判若天渊。
他俩离去母校回了故乡。
“奶奶!”小叶一进院,像当年孩童似的,声音是那样的宏亮,而又那么娇声,兴冲冲地喊着,“我是小叶。”接着又说:“我考上大学啦。奶奶。”
“叶子,你回来啦。”因为她没听清她的话意,所以她没回答,而只是说她要说得话。
奶奶独自一人,戴着老花镜,正在拿起剪子撂下针,为小叶修补着他爱穿的旧衣裳。忽听是小叶的声音,说他考住了大学,就愣住了,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说着她忙溜下地碎着小步,出院迎上去抓着他的手,“叶子,是真的吗?”她两眼盯着他,又惊又喜地追问着。
“奶!不哄您,是真的,还是北京大学呢。给,奶奶,这不是通知书。”他把盖有红章大印的通知书递给了奶奶。
她老人家把它捂在眼上,瞅了又瞅,端详个没完,她虽不识字,但也想看个清楚。于是她正看,放斜看,横着看,竖起看,咋看也是真真的、红红的大印子,就一万个相信,叶子真的考住北大是铁的事实了。
此时此刻的奶奶头不那么颤了,脚腕也硬了,说话的声音是那么宏亮,伸出她那骨瘦如柴的两手“啪啪”起来说:“啊!北大!北大!”她说着“嗵”地跌倒了。小叶和江兰惊恐万状地嚎啕起来……如何出殡的事不提。
夏季到来,人们忙着定苗锄草,突然刮来像狂风似的谣传,说是上帝令天上的恶神统领天兵——白郎下凡,要骟割世间的男人的睾丸,女人的乳头。河东、河西的街上散发了传单。上书:
战争虽结束,
华夏人太多,
上帝发了愁,
决意减人口。
骟掉男睾丸,
割去女乳头,
天兵将下凡,
要搞速决战。
村里的男女老少一群群,一伙伙惊惶失措地围着花花绿绿,煞气腾腾的传单念呀,听呀,娃娃女人顿时被惊坏了,有的如痴如傻,发呆发恐,有的被吓得呼爹喊娘地掉着眼泪;男人们吵嚷不休,众说纷纭,信口开河地怨天尤人。街上乱吵乱叫的,跑回家拴窗闭门的,草苗混杂的田地从此无人管理了。
刘江国与村民们一样,失去了胆,没了主意,他跑到区里找小枝。
而小枝对这种不曾听的罕闻很奇怪,也很糊涂,但他总觉得此事非同一般,大有疑虑。尽管上级没有指示精神,他个人认为这决不是正常的迷信现象,而是被打垮的反动派,被赶跑的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结发动。社会上被斗的地富,反革命分子,反动迷信道会门,煽动破坏,迷惑人心,企图复辟反动统治,颠覆人民政权。因此,他一边写材料上报,一边召集了干部会,群众会,要他们提高警惕,认清敌我,严格识别迷信与利用迷信趁机叫嚣,煽动破坏社会秩序,破坏生产,破坏人民的安居乐业。我们要揭穿敌人的阴谋诡计,狠狠地去打击——打击阶级敌人的猖狂活动,力摧敌人的进攻。
村里庄户人文化落后,没文化的人是愚昧的人,他们对小枝的讲话不理解,而不理解就不接受,至少是难以接受——尽管村民们敬重他,然而因为群众素有爱迷信、讲迷信的传统习惯,也因为小枝缺乏依据的讲话没有说服力——庄户人多数是眼见的容易接受,什么的思维、逻辑、道理,他们不懂,不懂未免就难以接受。
村民们把小枝的讲话当成“心理安慰”去理解。刘江国低下头去没说话,不说就是不理解,他对不理解的事儿从来就不表态。惶惶不安的他,夜晚不敢出门。
苏三对小枝的讲话很不服气,他说:“骟蛋(睾丸)、割奶头的事儿是敌人煽动,有点扯得太远,“这会儿日寇在日本,蒋贼在台湾哩,地主变成了穷人,你呀提那些做啥?哈,那些人——不管是谁——谁知道,说是神——神在哪里呢?”老梅说:“我是一贯道的道徒,可我是修练养身,苦修来世,我只等穿着登云鞋上得西天去见上帝,谁爱听求呀蛋呀的,那些磋牙的话呢。”她听小枝提了反动会道门,就生气地辩解起来。
小枝还行呢,他很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老百姓相信迷信而不想念自己的原因——因为自己的说话缺乏说服人的依据,而要人相信,只有自己通过调查研究,用事实去说服人,教育人。于是他要深入群众中明访暗查。
“嗨,那娃你别管。”是刘才老汉用拐杖捅着地,瘪着没牙的嘴说,“你不能任性呀,这社会虽说不打杖啦,算是社会平稳了些,可谁知天神也要杀人呢?俺孩千万不可大胆乱闯、乱管——谁人去管神,管天呢?人常说天神杀人不留情啊!”
也怪,敌人的飞机加大炮没有吓倒树林村的人民,而几张传单可把人们怕草了,是因为散传单之后,竟接连出现了许多怪事:长梅说昨晚听着了野外的吵吵声和哭声;郝白说村外出现的煮鸡蛋皮子,喝没了酒的瓶子;还有血糊糊识别不清的碎肉。苏三哭丧着脸说:“我的娘呀,这这这一百零一只蛋岂不就是五十个半男儿的蛋吗?啊,哪个人骟了蛋能活呢?冤枉啊,上帝你既降生就莫杀人,嗨……”
这怪事的出现,人们索性不敢出村办事,不敢出地干活,夜间三家五户住在一处,女人孩子睡在里边,后生们看门挡户,碗口大的石头放在门内,镐柄铁锹立在了门后,厚生们守在门里轮流站岗放哨等等。
夜,是那么黑,那么静,那么使人害怕。吃过晚饭,小枝拿着红缨枪,要夜巡去。兰兰说:“你疯啦,别人都怕死,你不怕吗?”小枝看了看她没作声,慢慢地才给她解释说:“我认为不会是事实的……天上绝对没有上帝,而没有上帝就没有天兵白郎下凡了。是敌人利用迷信进行煽动破坏。她说:“就说没有天兵白郎,也有鬼怪恶狼吧?深更半夜的,你不怕可我怕哩。要不,你可叫上我哥作个伴儿。”
“他呀,胆小如鼠,你是清楚的,此刻的他一到晚上缩在家里怕得要命。因此,他绝对不会去——他怕丢了睾丸。”
“要不,把郝白领上,两个人就壮胆啦。”
“他更是个怕死的人,你用麻绳也难牵出他去。”
兰兰尽管胆小害怕,然而为着小枝,只好去闯惊受怕,亲自陪着他——心爱的丈夫。他见她非去不可,递给她手电要她拿好,但不让她开灯,让她在紧要时刻才用。她牵着他的手,提心吊胆地轻步慢速地沿着河东的大街小巷转起来,又跑去了河西,返回来蹲在分河暗处。
夜,黑鼓隆冬的大街小巷,人影儿不见,原来村里三家五户合居到一处,竟紧闭门户,点着长明灯。他俩沿着分河畔,转到桥头暗处蹲下来。兰兰越来越感到紧张,害怕,她竟钻在小枝的胸前,紧紧地贴着他的胸部嚷嚷着,要他搂紧。淙淙的河水潺潺而去,哇哇的青蛙叫,汪汪的家犬……让她听来像似一部哭丧曲。她说:“走吧,咱莫非是为了看河流吗?”小枝说“这儿眼宽,河东,河西都可观着,多待会儿,瞅瞅坏人在哪儿,如何扰乱……”
忽然,天上一道银白色而耀眼的闪光,由东向西滑去,兰兰吓了一跳,忙摇着小枝的肩惊惶失措地说“你观着了吗?是不是上帝放下了天兵白郎?”小枝说:“是看着了,上年纪的人说,那是流星;”但如何解释,我说不清,解释不了。我咋可晓得?——要是我学了天文学,便可给你解释。”突然间,分河上游咿咿哑哑,出现了几声刺耳难听的长鸣,兰兰的心再次砰砰地跳起来,她以为——就忙闭眼深藏在他的衣襟之内。小枝说是狐狸,听人们说,它喝了水便叫;次于说为啥叫唤,有人说它每喝完水便肚子疼痛;有人说是狐狸的天性——说法不一。
夜间的野外,狼嗥怪物叫,是常事。可意外的是此刻铁架山大路“嚓嚓”的脚步声直响,渐渐地逼近。兰兰说肯定无疑是天兵白郎了,小枝说是冒充天兵白郎的坏人则无疑了。一溜五个男人,悄悄地通过河东,溜到河西去。
旧历中旬的月亮,将要沉落西山,连锁反映的村狗,吵翻了天。江国听得门外“铮铮”,“噌噌”在磨砺着刀。他就高着嗓门喊叫,屋内的娃娃女人七声二气在哭,男人们的呼喊声一阵高似一阵,石块像冰雪似的飞了出来。大胆的小枝领着兰兰匆忙从分河跑了过来。贼人越过分河,从铁架山方向溜跑了。老梅却被小枝抓着,刘江国、郝白一伙人跑出来,把她三下五除二捆成个疙疸。
二日郝秀才贴出了短文:
晴空一块云,
冰雹却降临。
太平的世间,
敌人在暗中。
树民们一见有胆有略的树区长,及时抓获了故弄事非,煽动与破坏社会秩序,破坏生产,反人民的一贯道徒——老梅,村民们就没了恐怖心理,平衡了心理状态,兴高采烈地当夜都搬回了自家,去睡放心的囫囵觉。
二日清晨,万里无云,一轮红日渐渐升上了东方的天空。那么明,那么亮,使人感到舒适。早饭后,郝白满街敲着响锣,要村民们到河西的十字大街,去批斗反动分子老梅。一会儿,男女老少济济一堂,个个眉开眼笑,激昂愤慨地欢呼,庆幸与反动道会们斗争的伟大胜利。
刘江国把老梅推上人群中间的石阶上,要她向村民们低头认罪。而她皱着挽疙瘩的眉脸,不声不响地呆呆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卑鄙龌龊的老梅站在台阶上,搭拉着脑壳,垂头丧气。眼角鱼尾似的皱纹,流露了阴险,狡猾,沮丧,诡秘的神色。她无精打采的像俱泥塑,一动不动。她那皮肤松弦的躯体,仿佛跟尸体没有两样。她穿着红色外衣,将腆着的大肚子裸露在外面。她不时揪襟遮住。可那不听话的襟老向外溜。
刘江国说:“大伯大叔们,兄弟姐妹们,暗藏隐避的敌人被我们揭穿与抓获了,我们取得了胜利!”
他还说,我们万万没想到拿枪的敌人打倒了,竟还暗藏着没拿枪的敌人。他(她)们披着修身养性,苦修来世的外衣,竟干了反人民的勾当。他们是蚂蚁撼大树——自不量力,他们妄想推翻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政权,是白日做梦!
郝白跃到老梅面前,指着她的脑袋,气愤地说:“去掉狡猾、侥幸心理,老实交待!”“交待!交待!老老实实地交待。否则,要砸烂你的脑袋!”是此起彼伏的群众纷纷大喊大叫。
老梅虽狡猾然而她并不傻,她清楚地知道,负隅顽抗不过,就苦着脸儿结结巴巴地说,她本人是反动组织的一员,多次来树林村的那五人是点传师,县城人氏,名叫张敬、柴元……总头目是北京人,张××。她说共产党政府独裁,上帝要组织国内外相对势力去推翻其政权。
“哈,哈哈哈……”村民们轰笑,他们笑一贯道的梦想是无耻的,可笑的,是……
周树平拿着包睾丸放在老梅面前,横眉冷酷地责问。“这是啥?那儿来的?”她头也没抬地说:“睾丸是猪、羊……的蛋。”
“为啥切碎变去原形呢?”树平指着那些发霉的乱肉问。
“这些用不着解释,可想而知。”她低头绷着脸支吾。
他原本是清楚的,却抓起那玩艺,使劲地摔到她脸上,并唾了她满脸而去。苏三也清楚了,他哈哈一笑:“岳母和她的同伙们够厉害又点路多,不去切碎怎可骗得了人呢?”
“鸡蛋和空酒瓶呢?”还是树平问。老梅如实地作了交待。“岳母呀,您的登云鞋让我穿着上天中玩玩,好吗?”苏三笑着恳求说。
长梅上前一把拉下了他,狠狠瞅着他,怪他任着性去发傻风,因为他的说话,她受不了——太失面子。“我苏三长着嘴不会说话……”他想“看我苏三做下个啥事,惹着了岳母,得罪了村长不提;得罪了长梅可算坏事了——我苏三真舍不得惹她的。”然而他又想:“革命嘛,还能讲情面吗?”于是他又跑上去说:“岳母啊,做错改错还行哩,若死不悔改嘛,俺当女婿的不会去认你,也不会让过你的,对吗?”
村民们恨老梅,也嫌苏三太捣乱——乱说乱道——但他毕竟是个不成器,就不理他,他们要江国、郝白把老梅捆绑紧紧的,狠狠去打。周树平、郝三和他儿子,跑上去,两个各抓着捆绳的一头,用脚发着她的背部,使劲地勒,直把她的两条大胳膊向后抽到一块了。她的脸变红而又变成白色,胳膊骨“嘎叭”,“嘎叭”地乱响,她尖叫了:
“娘呀!断啦!断啦……”说着就“嗵”地倒在地上。村民们不解恨地说,我们千多亩禾苗,草苗并举,蔫蔫地枯死。没了粮我们也得饿死呢。这是你们做得好事,应该处死你。老梅躺在石阶下,被人们用木棒“咚咚”地像擂死猪似的,而她也像岸上挨刀子的猪,“吱吱哇哇”地号吼。
小枝是个心软的好心人,他忙上去阻止了人们的乱打,并给老梅放松了捆绳。他认为尽管她是个坏人,然而毕竟是点传师的从属与信赖人——受蒙蔽的人。他要江国派人把她看管了起来,继续审问,调查和落实。
不几日,人民是报刊登了消息,全国部分省、市、县和乡村,在中央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尽快地,全面地,彻底地查清,打击,取缔了反动道会门的一贯道。县里司法部门和全国一样,及时发出了欢欣鼓舞的布告,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张、柴……反动道会门的点传师叛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俗话说,“五谷依时种,锄楼莫可迟”。由于反动道会门闹事的影响,人们未能及时锄苗。延时误期的禾苗,时间越长而越显的枯萎。没了生长能力,就没了丰收的希望。
小枝接到上级的批示,及时组织了互助组,变工队,经过村民讨论与协商,一致赞成互补缺欠,互相协作,村里所有耕畜全部动员起来,在短短的几日里,把失去收成的耕地全部改种了短日期的荞麦、黍子、白菜等等。
由于粪多、水勤,辛勤作物,五百多亩白菜竟夺得了丰收,亩均产量一万多斤。铁架山大路购菜的人、畜络绎不绝。树林村变成周围村庄的蔬菜市场。做到了粮食减产蔬菜补。光这一项每人平均收入近二十元,村民们的生活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