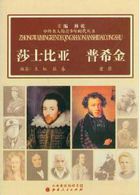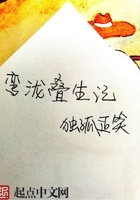王二叔组织村民把树平的尸体装棺入殓,与小梅合葬不提。仅仅安葬了只有近半个月时间,聂双双回来了,他是特意回来看望树平的。他爬在坟上恸哭了几场。他还为死者烧了沓冥票,烬了把香,供祭了些零食于牌前。哭着说:“可怜呀,我的大哥大嫂,安息吧,你们。”这也算是对大哥大嫂的祭奠,也算是送了他们一家的终。
二叔收留双双住下来。
“怎么办?出路在哪里?”他想。“人人都说八路军好。”他想的是要为大哥一家去报仇。为这,他与二叔说过多次,二叔要他去参加八路军。几年来,他的脑际里有了八路军的概念。“啥时才能盼到参军那日呢?”他又想。他抓了抓头,把焦急的愿望压进了心底里。
二婶给他做了新鞋,破衣翻了新。给他剃了头,常洗着脸,他一下子变样了,变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村里人再不称他化子了。他所以如此,不仅在于他干净利落,还在于他勤劳肯干不怕苦,他生来是个勤劳人,只因他家穷,父母劳累成疾,过早地去了世,十岁的他被逼上了化子路的。
这会儿的他一会闲不着,给二婶担水、扫院、喂牲畜,也上山去砍柴等等。村里人们聘闺女,娶媳妇以及办丧事,自然少不了他去助忙,他成了村里的唯一助忙人。
他常帮刘二元进城买药,也帮张金枝做些她所做不了的营生。刘二元见他是个勤快人,热心人,也是个忠诚老实人,党组织要培养他入党,问他入不入?他忙说:“入入入。”
从此,党组织就教育他,培养他。他清楚地知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它要领导人民彻底消灭日寇,消灭伪军,推翻伪政权,以及要打倒恶霸,清算地主富农等等。
经上级批准,王二叔要刘二元和张金枝,给他讲了党章、党纲,做了入党宣誓。
“你是否能做到永不叛党?”金枝站在他对面提问。
“四两银子一锭(定),金枝大姐。”他说完,两眼笑成一道缝,“好,双双,我们携手团结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也为解放自己而奋斗终生。”
“张大姐,我早下定决心啦,尽力干吧。”他低头想了想,又补充说:“嗨,张大姐,咱啥时去杀那王八蛋贪官县衙去?”他说着小心翼翼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他似乎觉得那县衙可厉害哩。因为他不只一次地亲眼目睹,反动政府的毒辣。“双双啊,凡恶者必有恶报,别着急,听党的话跟党走,你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只是迟与早的问题。”
双双满意地点了点头,然而他又进入了沉思。忽儿抬头说:“嗨,张大姐!老树哥探家回来,你记着要让他领上我。别忘了,我要参加八路军,上前线跟鬼子拼去……”
“好,双双。”她苦苦地一笑,两眼湿润了……双双见她的模样忙转了话题。后来很长时间的相处和多次的谈话,他概不敢再提她丈夫了。
小叶从院里跑回来,拉着她的衣襟嚷嚷着喜鹊、麻雀、他说:“妈妈,我饿啦。”他耍骄地说。她要给他找糖块,说:“乖乖,妈给你做饭。”她说完忙下地,拉开了衣柜——叶子说:“妈,我见爷爷和奶奶来,他们在场里呢。”
二小参军王二叔念念不忘,他白天想,夜里想,每时每刻觉得心理空荡而烦躁,坐卧不安,屁股刚落地,又忙站起来走了,整天东走走,西逛逛,心里像似缺了什么。日长了,他不思吃,不想喝,也睡不着觉。不几天瘦了一圈,脸色枯黄,腿儿软绵绵的,记忆力也差了,随身带的东西丢三忘四——神不守舍:“我想二小哩……”他自言自语地说。
其实,二婶跟二叔的心情一样,同在想念着儿子,她甚至比二叔还着重哩,因为她是生他养他,血肉相连而又心心相印的慈母;是她的奶汁一滴滴地喂他,使他长大成人的。人们常说“儿走千里母担忧”,难道孤儿的妈妈……?他虽没文化知识,心眼却很开通,她深深懂得儿大离母的道理,用道理去解释自己;用不提他,去避免感情的冲动;用“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的话来慰藉自己。
二婶清楚二叔从小娇生惯养儿子,二十多年来,二小从没离开过他的身边。幼年时的二小见爸干活回来,就骑在他的脖上没完没了地去耍娇。爸呢,一见他的小宝宝,疲累也没了。他说:“爸你明儿别上地去,我骑着你可好啦,咱们玩吧,爸一会儿出村捉蝈蝈去……”儿子要他干啥,他也得去,因为——他只是“嗯嗯”地答应着,很快领他去。
二小每当吃饭时,他的座位在爸的怀中。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年年也如此。直到上了学他才有了自己的座位,但还得挨着爸坐,因为他与爸一个碗,爸吃一口他吃一口,爸吃菜他吃肉。他说爸碗的饭香。
参军走时的他,虽年过二十,却还像个孩子,与爸说话娇声柔气,像是娇惯的闺女与妈妈的关系,动不动拉他的胳膊,揽他的脖子,咯咯地笑个没完。要爸做这,做那。爸呢,只要面前有了他,就高兴起来。简直高兴得忘了饥,忘了累,忘了一切。
二叔成了这个样子,二婶替他麻烦起来,这这——这让我怎么办呢?她顾不得想儿子了,她想尽一切办法去开导他,说服他,慰藉他。生怕他想儿想成个疯子、傻子,想成个久病不愈的病夫。
她给他吃糖,吃鸡蛋,吃白面馍,给他洗脸、洗手、洗浑身,给他捶胸、捣背、按摩……她看着他的瘦脸给他开导、解释:“唉,你看你,你是很精明强干的人,为啥一下子就糊涂起来呢?儿子长大要离父母,参军是你让他去的,是吧?”
二叔看了看她,答非所问地说:“你要狠狠地去杀鬼子。”又说:“二小,二小,你你啥时回来呢?”他说完慢慢上了场去。秋场上光秃秃的,只有一堆破烂——场里用过的家俱和场外成了垛的谷草、莜麦秸、稻子秸等等。草垛被孩子们捉迷藏钻了许多孔洞,像是马蜂窝,孔孔巴巴,碍眼难堪。看了使人讨厌、烦乱,引人心神不安。
一只野兔缩在草垛里东张西望,不时吱吱叫着,像似失去了伙伴,苦闷地发着愣。它一见二叔就发毛了,惊奇地发了几声浩叹,从草垛洞里跑出来,离草垛不远的地方停着踅来踅去,像心里不安似的。
王二叔没管它,他唉了声,慢悠悠走到场的边沿,出神地瞅着儿子在秋天用石块垒得那堵矮墙,“这是二小……”他想。他苦苦地思忖着,作模着,像似想象着儿子干活的模样,以及他垒墙的时间——于是他迈前一步,不自然地伸出两手,做着垒墙的姿式——二小,他流泪了,发出低低的细语:“你……你累吗……二小……”
他又一块块地摸着滑溜溜的石块,泪水一滴一滴,滴在石块上洗濯了儿子用汗水洒过的岩石。“我想你啦,我……二小……你甚时回来?我想我的娃……”而他又一次叫起来。
那只孤兔被他的叫声惊跑了,跑,跑,跑得无踪无影。二叔望着它发愣。他终于坐了下来,是坐在曾经二小搬来的板石上。这块石头生来方方正正,光溜光,专供做场务休息时当凳子坐的,所以放在场边。
“儿呀,你与可憎可恶的鬼子拼搏了。杀吧,狠狠地杀,杀它个落花流水呀……”他想。
“你吃饱吗?你穿暖吗?你挂花吗?战斗后,你请个假儿,我想你了……”他低声自言自语。
烈日当头照,二婶找二叔全村跑遍了没找到,才在这儿找到,见他脸色枯黄而又瘦骨伶仃,无精打采地坐在板石上。她心一酸流泪了。就怪怨起他来,说他不吃饭,成天东跑西逛,忘了回家。
“唉,你成天不回家我放心吗?你想儿呢?你说我想吗?人要自己解散自己,自己安慰自己。看你要得病啦,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呀,还不如我这个当妈的有骨气哩。像你那样子,要把身子骨想垮了,要把大脑想病了——得了病后悔也迟了……”
二婶见他红肿的眼圈沾了厚厚的尘土,就心痛地给他用手绢擦着,还是劝慰他说:“你要想得开,他是去消灭日寇的,你常给我说,参加八路军是件好事,只有人民大众的子弟踊跃去参军,才能打垮鬼子。你曾经说过不把日本鬼子打垮,我们穷人没活头,没出路。这话你说过吧?
“你还说好儿不会守爹待娘的,唉,你看你说是一套,做是另一套。你把饭也忘了,你把心也被儿子带去部队了。快死,快死,你如不改还能活下去吗?你要清楚,心病是害不得的呀。
“儿子未走时你要他走。我当时再三劝你不要让他去参军,因为我知道你离不开他呀,你当时说没事,这会儿后悔啦?世上没卖后悔药的。对吗?
“你常说,好儿要为国为民远走高飞。古人有个名叫左连成的,他一十二岁去告国太;刘秀一十二岁远走南洋……咱儿已二十岁了,村里参军走了多少人?谁像你那样,既吃荤又作假。你还算个大丈夫吗?你见金枝吗?人家也是你那样?你要清醒点,想上病是你自己的。”
“好啦,好啦,我不想他了。你算把我挖苦痛啦。但我还领你的教哩,因为你是一片好心为我的,想他也没用啦。”他说着就站起来拍了臀部的泥土要走了,但没走几步扭回头来看了看二婶,意思是尽管老伴既解释又批评,而自己还是想不开。他走到一堆脱粒家俱旁,弯腰捡起老树曾经用过的木锨,站在他曾经扬场站过的地方,一铲,一翻,一扬,是想象他当时扬场的姿式。演试了几掀,说:“你是扬场的棒手,你也是——唉,走了,走了,好人都走了……”他款款放下木掀,还是低声去自言自语。“我想他哩,他,他们两人啥时回来呢?”他又唉声叹气了。
日月流逝,感情永存。二叔与他是莫逆之交的穷朋友——不,是不同父母的亲兄弟,是同甘共苦,是同仇敌忾的阶级兄弟。他俩在贫穷而又艰辛的生活中,在复杂而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在反帝反侵略的战斗中,结下了如亲如故,亲密无间的友情和亲情。他想他仅次于儿子。
“尽管有我哩,但离乡在外的侄儿你,抛下可爱的妻与两个娃,难啊……”他长呼短叹,是那样的作难和思念。
“你呀,”二婶走在他面前说,“你能把他留住?我看你用铁绳也难拴呀。”这是你与我说得吧?他抛妻舍子投奔前线去,你是最清楚他的。你你你为啥不往开想,硬钻着死胡同,要从一棵树上往死吊自己呢?
“这……这……这……让我怎办呢?”她说完,拿了主意,拉他要去金枝家去。“那老汉,”她说,“咱今儿晌午去金枝家吧。”二叔不愿去,因为他清楚金枝也在害心病,何必火里去加油呢。
二婶又用好话说服他,要他去瞅瞅人家金枝的刚强劲。她说:“那老汉呀,咱老两口今儿去吃金枝的饭去,人家做下的饭比我好得多呢。”“我吃过啦,是做得美呀。”说着,她半硬半笑把二叔拉着去了金枝家。
时过境迁,新窑院里一丛丛野草被秋霜冻枯了。有的虽没枯,但也变成黄色。唯有墙角花池里的几朵茉莉花与夜来香,还放散着浓烈的香味,花朵儿鲜艳而迷人。
老树走后,金枝不怕苦,不怕累,在二叔的帮助下,抚养着两个娃还算过得去。然而为什么她成天少言寡语,愁眉苦脸,两颊又是那样地枯瘦呢?显然是因生活的重负,以及丈夫的生离久别对他的折磨罢了。
人在年轻时期,男女之间有着共同的信念,一致的情趣,至善的追求,双方无私的给予……像一串串闪光的音符,丰富与激励着双方爱的旋律。
爱情也像株耐人寻味的橄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是其赖以生存的内核,是心灵的召唤,也是人间的春风。
“老三。我想你啦……”她自言自语地低声说,“你的衣服脏吗?你累吗?你你你啥时探家呢……”烦腻了的她,流泪了。因为她还很年轻,年轻的一对有着长存的爱情。而真正的爱情并不等于娓娓动听的甜言密语,慷慨的山盟海誓和如胶似鳔的接吻、拥抱;而爱情是一种高尚、美丽、纯真的感情。
“老三,我佩服你的一切,因此……我的心永远……你的模样……你的声音……”她想。
金枝常常用左手扪着胸脯,半闭着眼沉思起来:丈夫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幕幕地展现出来。丈夫的给予,像花似的,日夜开在她的心中;也像溪水那样纯净,日夜不停地潺潺流入她的心田。然而久离的丈夫又留给了她人生烦恼。而由此引起的喜怒哀乐,只能装在肚里压在心中,像悠悠的云朵漂浮在万里长空,感怀着人生经历的喜悦;也感怀着人生旅途中的失落与惆怅。
金枝放下浇花的盆子,取了块半新旧的擦布,将院里东西走向——而又绷得很紧,明光光的铁丝捋抹干净,把洗好的衣服搭了上去。秋天的阳光虽不那么酷热,却还是那样温和。刚洗过的衣服一会儿将要晒干。阳光照着她那晶莹的眼眸,溢出银亮的波光,眼里明显地隐藏着忧郁的光,一闪一闪——像似牛郎织女相隔着天河,眨着期盼的双眼——亲昵的波光。
忽然,二叔和二婶一前一后慢悠悠地走了进来。二婶见金枝那股麻利的,一如既往的模样,扭头低声对二叔夸她说:“你看金枝的骨气呀。”
“啊,是您们。”金枝笑着把心目中的二位老人领回家去。招待他们吃过饭,又见二叔的身体欠佳,就让他躺下来休息。他睡在那儿,她瞅见二叔那模样,就清楚他时刻在想念着二小呢。他痛爱、器重儿子,像似十亩地里长着一苗谷。
二叔睡着了,金枝端详着他那慈祥而又善良的面孔,然而又——枯黄干瘦的面容、脸庞,就像有一股暖流淌入她的心田。但似乎有点伤感,她觉得是生她养她的养父躺在那儿。几只苍蝇落在二叔的脸上,她伸手攒去它。可没皮脸的肮脏苍蝇“嗡”地飞去,又“嗡”地飞来。她忙从衣包里找了块沙布,款款罩在他的脸上,让二叔不受干扰地去养身、养神。
二叔醒了,金枝化了碗艳而浓的糖水让他喝。二叔喝下去觉得有意外的香味,他把碗里的糖水倒在口中,仔佃品尝,咂摸着甜味。二婶见他喝得香甜,又见金枝的糖袋空了,就把金枝给她化了的那碗也让他喝了。她让他多喝点,对他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一会儿,小枝兄弟跑了进来。小枝抓着爷的手,小叶爬在他的背上。金枝给他俩说了许多好话,要他俩别滚爷,说他病哩。小枝大了,他听妈妈的话乖乖地坐在一旁。叶子不听话,二叔看着两个娃笑了又笑。看样子他的精神和情绪有所好转——想念转为期待——期待着孩子们战斗的喜讯,期待着孩子们胜利归来。
可是,期待也是焦心的,因他的心跟去了他们——或许会鞭策他们好好学习,狠狠地去杀敌啊,把鬼子杀光杀尽,回来建设家乡。“侄儿,你在部队我放心了许多,二小听你的话,不会出什么漏子的,不但学习你,而且团结起来,学习过硬的本领,冲啊,杀啊!”他想。
二婶见二叔变过了头脸,就放下了思想包袱而高兴起来。她要帮助金枝洗锅、涮碗、扫地、扫院。金枝虽不让她干,但被勤劳的二婶谢绝了。
二婶和金枝闭口不提参军的事——她们不是不愿提,完全是有意不提它,因为提起来觉得不如不提好。干脆无声地把它藏在心窝处,咽在心底里,慢慢地让它过去。时间长了,她们的心情就自然平静了。
“奶,今儿别走了,我不想让您们走呀。”是小枝从街上跑回来说。“要不我还不回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