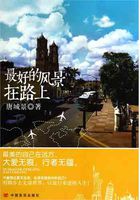在任何地方,我都找不到站在藏区土地上的沉醉。
你也许一生都不会去那里,但你可以从他人的故事里看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非常抱歉,我必须得说,到目前为止,我并不是一个虔诚的有信仰之人,如果有,那也是信仰自然与天性,信仰一切不可知。
我也在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堂里听过神父布道,在信众为主唱颂歌的时候也感受到祥和美好,也看过《圣经》,试图了解,但最终只对佛教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
史学家通常认为东汉明帝(公元58至75年)时,佛教传入中国。但现在有史料可以证明,在此之前,中原的汉族已经接触到佛教,而且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相融合。历经时光,在日常的生活中,那些没有被命名为佛教的教育和思想,早已融入于我们的血液,是我们思考问题时最直接的角度。
这也是我得以写成这本书的源泉。
不丹的活佛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是我所知的最具有西方思想的开放式的宗教领袖,同时还是一位很值得尊重的电影导演,他在西方生活多年,在接受采访时他说过,他也谈恋爱甚至还经历过女朋友劈腿的痛苦。还有他看到坐在阳光下被阳光勾勒出金灿灿轮廓的女人,立刻就爱上了她。他没有因为是一位活佛而排斥作为人的感受。佛教最关注的是智慧。
那么是什么令他成为一个佛教徒呢?他说如果一个人接受下列四项真理,那就是一个佛教徒:
一切和合事物皆无常(诸行无常)一切情绪皆苦(诸漏皆苦)
一切事物皆无自性(诸法无我)
涅槃超越概念(涅槃寂静)
你也许不是生长在一个佛教的国度,你也许不穿僧袍或剃光头,你也许吃肉而且崇拜说唱歌手或是性感名模,这并不表示你不能是佛教徒,要成为一位佛教徒,你必须接受一切和合现象都是无常,一切情绪都是痛苦,一切事物无自性,以及证悟是超越概念的。
好吧,我想了想,这些都是我愿意所接受的。
在任何地方,我都找不到站在藏区土地上的沉醉,可是对与之息息相关的藏传佛教,我始终保持着适度的迟疑。佛陀说:人人皆可成佛。而且释迦牟尼是一位真实存在的哲学家,是大智慧者,为什么要充满神性?佛陀坐在菩提树下开悟,后人为什么要修建庙堂?用真实的铜铁木头或泥土塑造出佛像,为什么去叩拜?诸多疑问,让我不能开解,不能开解我就保持尊重,同时也不排斥任何人的虔诚。而且在很多时候,听着诵经声声,或是跟随朝拜者的身影,也会被感召,也会有归属感。
在家人和朋友病痛或困扰的时候,我也鼓励他们念经,告诉他们念经会让人暂时放弃执着于自我,让心有所依靠。在我爸身体不适但各种检查又都极其正常的时候,我每天念108遍药师佛心经,这个时候我忘记了“临时抱佛脚”这个说法,更不可能再有什么疑问。
看了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的《正见》之后,才有些豁然开朗,我随手记下的空性、无明、了悟,三个看似名词,其实也可以是动词或形容词,最终是什么词性并不重要,那些疑问和看起来是否临时性的盲从,也终于不再重要。
即便如宗萨仁波切这样的智者,他父亲也还是会时常把他叫到眼前进行批评教育,令他改进,提醒他太过理智。
理智,这难道不应该是对一个人的赞美吗?
有一天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也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佛教徒。
在一个村庄里,有一个18岁的姑娘突然生了个娃,她的父母就逼问她是谁的,她说是村外寺院里的老和尚的。父母疯了,抱着娃找到了寺院,把孩子扔给了老和尚,又理所当然进行了各种斥责奚落,老和尚抱着娃只说了一句话:哦,原来是这样啊。寺院也容不下老和尚,他就抱着孩子到各处布施,到哪里都被指责。过了几年,姑娘长大明白了,跑来道歉想要回孩子,老和尚还是只说了一句话:哦,原来是这样啊!
停下来认真想一下,“哦,原来是这样啊”,其实可以解决掉很多问题。
索伦·克尔凯郭尔是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和诗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认为哲学研究的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个人的“存在”,哲学的起点是个人,终点是上帝,人生的道路也就是天路历程。站在他的意识平台上,他说“请记住,上帝不是理解,而是行动”。
我有一个朋友是藏传佛教信仰者,时常在藏地各处旅行。我看到他发的图片里,几位上了年纪的朝拜者正在磕长头,他们的背后是佛殿和密密麻麻的修行者的红色小屋。我问:虔诚的叩拜里,是不是也会包含虚妄?这么多抱同等信念的人聚在一起,是否也是彼此取暖?我并非不相信,也不全是怀疑,我想听听你身临其境的感受?
他的回答不出我所料:没想那么多,想太多就不是佛教了。
“你知道怎样才能见到美人鱼吗?要游到海底,那里的水更蓝。在那里蓝天变成了回忆,你就躺在寂静里,待在那里,决心要为她们而死。只有这样她们才会出现。她们来问候你,考验你的爱,如果你的爱够真诚够纯洁,她们就会和你在一起,然后把你带走。”
这是电影《碧海蓝天》里的台词,也像是藏着神秘的解悟之道。
佛教信仰者强调放弃执着,天主和基督教信仰者说一切交给万能的主。道家用“忘”字来概括自己心灵修养的方法和体会。圣人并不是天真无邪到老未变,他们也曾追求通常的知识,努力分辨事物和人物的是非得失,后来他们把这些都“忘”了。“无知之知”和“无知”是本质的不同,“无知”是原初,而“无知之知”则是经过“有知”到“无知”,人的原初状态的无知是自然恩赐,而人达到“无知之知”那就是灵性的成就了。
苏东坡在他敬重的朋友范镇死后说: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减节嗜欲,一物不芥蒂于心,真是学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谓景仁虽不学佛而达佛理,虽毁佛骂祖,亦不害也。
对于西藏人,从出生开始,藏传佛教就是活着的一部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信与不信这个问题。从见到这个世界那个刻起,佛就和他们在一起。
最初,三千世界形成之时,世界为一大海,海面上有被风吹起的沉渣凝结,状如新鲜酥油,由此形成大陆。此后,有一些极光净天的神祗,死后转生此处为人,他们身具光明,能够空行,依靠静乐之食生活,能够无限长寿。此时星辰、季节、男女具无分别。其后,有一人发现地醍醐味甚美,渐次人人皆取食之,由此身体变重,光明消失,星辰、季节、昼夜等产生。地醍醐食尽之后,依次有甘露观音土、谷芽菜、不种自生庄稼生出,因取食此等食物,人生男女之别,出现交合之事,时感羞愧而盖房居住。此等不种自生的庄稼并无人照管。后有一人未得别人同意强行拿取,为了对其处罚,众人商议,选举一身体健壮之人为王,称其为众人共敬之王,此人就是人间最早的国王,此时众人被称为众有情。
这段文字可不是西藏的寓言故事,而是西藏著名学者蔡巴·贡噶多吉所著《红史》的开篇,这本书历来为藏族先辈诸史学家所推崇,并有多种手抄本,是研究藏族史和唐蕃关系不可或缺的文献。
这位共敬之王的王统一直延续到释迦族的国王净饭王,也就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父亲。然后,世界就这样展开了。
进入到一个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史的世界,你还要保持所谓的理智,那这个世界你永远看不明白,永远也不会懂。这个世界也注定与你无关。
关于信仰,信与不信,在于一念,在于你愿不愿去接近,去深深接受,并能够倾注情感。对于我,西藏从一开始只是一次旅行,没想到转眼十年就过去了,始终没有离开过。起码在情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