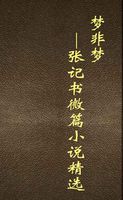接着,他就会高兴地尖叫,要父亲把他放下来。其实,在父亲强壮有力的手臂里,他感到安全极了。他认为,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棒、最了不起的人。
有一次,父亲与母亲合力抬一架钢琴,他们的手挨在一起,扶住乌亮的琴架。他注意观察了一下,他看到妈妈的手雪白、纤细、小巧,爸爸的手宽大、厚实、有力。这对比竟如此鲜明。
他大一点的时候就开始玩“捉狗熊”游戏,每到晚饭时分,他就埋伏在门背后,一听到父亲关车库门的声音,便屏住呼吸,紧张地贴在门背后。一会儿,父亲出现在门口,两条长腿一碰,笑哈哈地问:“小家伙呢?”
这时,他就会瞥一眼正作怪相的母亲,然后,猛地从门后跳出,上前一把搂住爸爸的双膝。爸爸赶紧弯下腰来看,一边大叫:“嘿,这是什么——一只小狗熊?一只小老虎!”
到了上学的年龄,他走进了学校,在交往中,他学会了忍住眼泪,也学会了摔倒欺骗他的同学。回到家里,他就在爸爸身上演习白天所学的摔跤功夫。可是,无论他怎样用劲,怎样施展所学的技巧,父亲仍坐在安乐椅里看报,纹丝不动,只是偶尔瞟他几眼,故作吃惊地柔声问:“孩子,有什么事吗?”
他在与父亲的“摔跤”中又长大了些,瘦瘦的身材倒也十分结实,他像刚刚长出角的小公牛,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想与同伴们角斗,试试自己的锋芒。他鼓起手臂上的二头肌,用母亲的软尺量一量臂围,得意地伸到爸爸面前:“看!怎么样?”爸爸用大拇指按他隆起的肌肉,稍一用力,他就忍不住大叫:“啊!快松手!”
有时,他和父亲在地板上摔跤。妈妈一边把椅子往后拖,一边叮嘱:“查尔斯,注意点别摔坏了他!”
他还不是父亲的对手,父亲把他摔倒后,自己坐在椅子里,朝他伸出长长的两条腿。他爬到父亲身上,拼命擂着两只小拳头,怪父亲没拿他当一回事了。
“哼,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摔倒你。”他这样说。
进了中学,踢球、跑步,他样样都练。他的变化之快,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他现在可以俯视母亲了。
这期间,他和父亲的摔跤不断进行,母亲一直以来对父子俩之间“争斗”不支持,也不明白。不过回回摔跤都是他输——四脚朝天躺在地板上,直喘粗气。父亲低头瞧着他,柔声问:“投降吗?”“投降。”他点点头,爬起来。
“我真希望你们不要再斗了。”母亲不安地说,“这有什么必要呢?会把自己弄伤的。”
此后,他有一年多没和父亲摔跤。一天晚上,他突然想起这事,便仔细地瞧了瞧父亲。结果却让他很吃惊,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魁梧,高大的肩膀也不如以前那般宽厚,他现在甚至可以平视爸爸的眼睛。
“父亲,你有多少磅?”
父亲慈爱地看着他,说:“跟以前一样,190多磅吧。孩子,你问这干吗?”
他咧咧嘴,说:“随便问问。”
父亲诧异地抬起头,不解地看着他。碰到儿子挑战的目光,父亲眯缝起眼睛,柔声问:“想较量一下?”“是的,父亲,来吧。”
父亲脱下外套,解着衬衫扣子,说:“是你自找的啊。”
母亲闻声赶紧从厨房跑了出来,一边跑一边喊:“哎,你们父子怎么又要摔跤?天哪!这可怎么办?”但父子俩全不理会。他们光着膀子,摆好架势,眼睛牢牢盯着对方,伺机动手。他们转了几个圈,同时抓住对方的膀子,然后各自使出自己的高招与技巧,企图绊倒、扭倒、推倒对方。室内只有他们的脚在地毯上的摩擦声和他们的喘息声。偶尔不时咧开嘴,显出一副痛苦的样子,母亲站在一边,双手捂着脸颊,哆嗦着嘴唇,一声也不敢出。
他终于把爸爸压在身下。“投降!”他命令道。
“做梦!”父亲说着,猛一使劲推开他,争斗又开始了。
但最终父亲还是被儿子重新摔倒在地,父亲显得很疲惫,儿子那冷酷的手牢牢地钳住了父亲,父亲绝望地挣扎了几下,停止了反抗,胸脯一起一伏,喘着粗气。
他问:“投降?”
父亲停了停,然后坚定地摇摇头。
他的膝头仍压在爸爸身上。“投降!”他说着,又加了点劲。
突然,爸爸大笑起来。他感到妈妈的手指头疯狂地拉扯着他的肩膀。“快松开,别弄伤了你父亲!”
他俯视着父亲,问:“投降吗?”
父亲止住了笑,湿润着眼,说:“好吧,我输了。”
他站起身,朝父亲伸出一只手。但妈妈已抢先双手搂住父亲的膀子,把他扶了起来,父亲咧咧嘴,对儿子一笑。他想笑,可又止住了,问:“父亲,没弄伤吧?”
“没事,孩子,下次——”
“是的,也许,下次——”
妈妈这次什么也没说。她知道这下一次不会再有了。
他先是看了看一脸慈祥的母亲,又看了看高大的父亲,然后转身向门外跑去,他穿过房门——以前常骑在父亲肩头钻进钻出的房门;他奔向厨房门——自己曾埋伏在那后面,与父亲说“捉狗熊”的门,冲出屋外。
外面黑黑的。他站在台阶上,仰头望着夜空,满天星斗。他不禁流下眼泪,眼泪咸咸的,苦苦的,他不知是高兴,还是悲伤。
邮局内外
——[美国]托·R·蔡斯
一个年轻人想取回自己早上寄出的信,邮递员利用职务之便横加刁难,引起了在邮局等候取信人的不满。
最后,年轻人不得不把写给情人的诗背给大家听,才拿回了信。
天异常闷热,偏又没有一丝风,这更增加了人的烦躁。西边的天空已聚拢了一些乌云。
邮局窗前,人们早已排成长队,站在那里眼巴巴地等着。他们中,有来领取社会保险支票的老人,有来领取从家里寄来的包裹、手里持着粉红色卡片的学生,有商人、秘书,还有家庭主妇。
队伍中每个人都已汗流浃背,他们眼巴巴盯着那紧闭的邮局窗口,等得十分心焦,他们中有的在慢吞吞地走,有的在唉声叹气,有的你一句我一句地在谈天论地,但话题却总离不开眼下这令人烦躁的天气。
邮局的窗终于打开了,排队的人立即向前拥挤。
“我今天清早寄了一封信。”排在队伍最前的那个年轻人说,“寄出去了吗?”
“还没有,怎么了?”邮递员回答道。
“我可以把信件要回吗?”年轻人问。
年轻人脚上穿着凉鞋,身穿蓝色的牛仔裤。他的头发虽然留的不像某些年轻人那样长,但蓬松着,看样子也不短,估计是艺术院校的学生,他们多作此打扮。
邮递员怀疑地打量着他,问道:“为什么呢?”
“我想加几句话。”年轻人应道。他说话时,神情有些激动,显然要加进去的话很重要。
“那你可以写一封信再寄去。”邮递员建议道。
“因为我还想把信中的一些话删掉。”年轻人说。
“那同样可以在另一封信里进行。”
“那怎么可以。”年轻人说,“这是写给我情人的信。”
后面排队的人群中传来了不耐烦的抱怨声。年轻人急得满头大汗。
“你一定是第一次给别人写情书,是不是?一切都要讲求完美。”邮递员不无幽默地说。
后面排队的人中有几个人听了,偷偷地笑起来。
“你不会明白的。”年轻人争辩说,“这是一首诗,一首只有她才能懂的爱情诗。我可以把信要回来吧?”
这下,许多人都忍不住嗤嗤地笑起来,年轻人的脸腾地一下红了。
“只有她才能懂?这爱情诗是关于你们未来的吗?”邮递员说,“这下你不想寄了?”
“不,要寄。”年轻人强调说,“但在寄出之前,我要改其中一行,实际上要改的只是一个字——因为这个字可以改变这行诗,改变这节诗的面貌!”
邮递员皱着眉头,不高兴地说:“你的意思是说,你的这首诗会因你改了某一个字而面貌不同?”
“哦……对,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是这样的。”
“不过,你想过没有,就为了这一个字,就要我翻遍今早邮寄的全部邮件吗?”
“倘若你愿意……就请帮个忙吧!”
“我不愿意!”邮递员说。
“可这是你的义务!”年轻人大声地说,“我知道有这些规定。我是在法规中行使我的权利!”
年轻人的衬衣——从肩胛以下,全都被汗水湿透了。
“把名字和地址写下来!”邮递员板起面孔,一边说,一边把一支铅笔和一本便笺推到年轻人的面前。
这个年轻人急忙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潇洒地在便笺上留下名字和地址。邮递员把这一页从便笺本上撕下来,慢吞吞地走开了。年轻人转过身来,他很抱歉地对大家说:
“实在不好意思,我原来不知道这事竟会如此麻烦。”
年轻人很难为情地又转过身子。这时,邮递员拿着一个信封和一个表格来了。
“把这个表填好,然后签名盖章。”邮递员说。
年轻人把表填好,交给了邮递员。
“身份证拿来!或者驾驶证也行?”邮递员要求。
“我有我们大学的卡片。”年轻人说。
“那有什么用。”邮递员说,“我需要的是官方的证明。需要的是能够证明你是什么人的证件——证明这封信确确实实是你的。”
“但是,你可以从这表格和信上看出这信是我寄的。”年轻人说,“两个名字是一样的。”
“可是,我仍然不能肯定这信是你投寄的,”邮递员说,“又没有来回的地址。”
排在后面的人听了这话,都认定了邮递员公报私仇,故意为难。便七嘴八舌地指责他。
“如果你没有身份证,那我就只有把信打开,看里面写的内容了。”
“可是,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年轻人争辩道,“里面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写给我情人的诗。”
“我只有亲见,才能相信那是真的,”邮递员坚持己见,反驳道,“里面写的可能是一首诗,但有可能不是你写的,而是他人写给你情人的,你就想从中获利。甚至还可能是份秘密文件,因而你就想阴谋窃取它。”
这下,又引起了后面的人对邮递员的指责。
“我是把信封打开好,还是不打开好呢?”邮递员问。
“假如你一定要这样的话,你就打开吧。”年轻人无可奈何地说。
邮递员得意洋洋,笑嘻嘻地把信封撕开。
“不错,这是一首爱情诗。”他大声地向大家宣布,“但怎么让我相信它出自你手?”
大家听了,纷纷拥到前面来,指责邮递员的无礼。邮递员站在柜台后面,恼怒地向人们瞪了一眼,仍然蛮不讲理,毫不退让。
“它确确实实是我投寄的。”年轻人肯定地说。
“那么,拿出证明来。”邮递员强词夺理地说,“这样吧,你把这首诗背出来吧!”
这下,大家被激怒了。“不背!”“毫无职业道德,告他去!”愤慨的叫声,不绝于耳。
邮递员不得不让了步:“只背最后几行吧。”
年轻人的脸涨得通红。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远方,好像他的正前方就是宽广无垠的旷野,好像站在他面前的邮递员、那邮局的墙壁,根本不在他的视野之内。
“我梦见遥远的地方,
有一个多情的姑娘,
她的笑声宛如银铃,
她的摩挲好似沙沙细雨的温馨。”
人们听得那样仔细,虽然他们不太懂诗。
当年轻人深情地背完爱情诗,人们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祝愿与支持。邮递员呆呆地站着,脸白得就像周围的墙。他愣愣地没有把信交给年轻人。年轻人一把从他手上抢过那封信,就急急忙忙地走了。
这时,风刮过人们的脸庞。起风了,雨也下来了。
沃夫卡和祖母
——[前苏联]阿·阿克谢诺娃
九岁的沃夫卡被父亲送到乡下祖母那里去度假,祖母每天让他劳动,一点也不宠爱他,所以他不喜欢祖母。
后来他从维佳口中得知祖母的为人便喜欢上了祖母,度假结束时,沃夫卡流泪了。
沃夫卡的母亲三年前因病去世了,他和当船长的父亲生活在北部的摩尔曼斯克。由于父亲常年出海,小沃夫卡多寄居在邻居家,后来父亲决定把他送到乡下祖母那里去度假。
刚开始,小沃夫卡不太喜欢祖母。沃夫卡已习惯于所有亲朋好友都娇宠他,可这位祖母却并不溺爱他。
就在第一天,沃夫卡扭伤了脚,他极需要祖母来安慰他,但祖母却平静地说:“别哭啦!你又不是小孩子!”这还不算,还让他去商店买面包。沃夫卡委屈极了,但也只得照办。
沃夫卡一瘸一拐地从商店回来,把面包往桌上一扔,说:
“给你面包。”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什么态度?”祖母生气地说。
沃夫卡也不答话,扭头就去睡觉。他嘴上说不想吃饭了,心里却希望祖母来哄他,并拉他去吃饭,但祖母什么也没问,也没叫他去吃晚饭。早晨起来,沃夫卡还得打水、买面包,然后到地里帮祖母干活。沃夫卡感觉祖母很没人情味。
有一次,他对祖母说:“您写信让父亲来接我回去吧!”
“为什么?你会慢慢适应这儿的。”祖母答道。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父亲。你让我整天劳动,我现在是放假,我应该休息,是你剥夺了我休息的权利。”
“别人都在干活嘛,你又不是小孩子。”
“可我才上二年级!我不过才九岁。”
“九岁怎么了?我九岁的时候,早就下地劳动了。”
沃夫卡采取消极怠工的方式对付祖母,他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干活了。有一天,他没去商店买面包,晚上祖母说:“今天我们不吃晚饭了。因为没有面包吃。”结果沃夫卡只得饿着肚子去睡觉。事后,祖母对他说:“孩子,那样做是没有用的,要知道,你还要住在这里,而且也会喜欢我的。”
沃夫卡生气地瞪着祖母,一言不发。
有一天,沃夫卡跟他的好朋友维佳谈起了他的祖母。可维佳却对他说:
“你误会了你祖母,你祖母在村里非常受人爱戴。她是个好人,而且她懂很多,甚至还会治病。我们有个邻居有一次头疼得厉害,吃什么药都不管用,而你的祖母很快就用草药把他治好了。”
“她真懂那么多吗?”沃夫卡兴致勃勃地问道。
“一点不错,”维佳答道,“她能识别所有的草木,她还特别善于洞察人们的内心世界。”
“这我相信。”沃夫卡说,“她总能知道我在想什么。”
有一次沃夫卡和祖母一起到大森林里去。祖母在森林里如入家门:每一棵小草、每一棵树木都成了她的老相识。祖母告诉沃夫卡各种各样的小草:瞧,这棵小草专治头痛病,那棵小草专治心脏病。
“你是如何掌握这些知识的?”沃夫卡问。
“我在乡下住了一辈子,我的母亲特别熟悉这些草木,是她告诉我的。”
“奶奶,你是如何治好那个人的头疼病的?”沃夫卡决心问个明白。
“哪一个?”
“你们村上的,他头疼得很厉害,吃什么药都不管用。”
“我已经记不得了,”祖母说,“噢!我记不太清楚了。怎么治好的?你看到了吧,我知道头疼时吃那种草药管用。”
“那为什么吃那些管头疼的药就不管用呢?”
“因为他并不相信那些药能令他好起来。”
“那他相信你吗?”
“是的,我把草药给他,并告诉他,过三天就会好的。果然三天后他就好了。”
现在,沃夫卡已经喜欢上了祖母,他决心要做一个像祖母一样的人。从此,祖母让他干什么,他都乐意去干。他明白祖母为什么不像别的亲友那样娇惯他。
一天,从摩尔曼斯克拍来一封电报,祖母看了电报后说:“嘿,这下你该高兴了!”
“父亲要来吗?”
“不,是你要回去啦!”
“为什么?”沃夫卡问道。
“因为你父亲希望你回去。”
“那您一个人多孤单!”
“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到我这儿来;如果不愿意,说明你不爱你祖母。”
沃夫卡想对祖母说,他非常爱她,但终究说不出口,眼泪却禁不住流了下来。
节日
——[俄国]谢·阿·沃罗宁
娜季卡被丈夫抛弃后,终日酗酒成性。最后,年迈的母亲跪着求她戒酒,她答应了,从此一家人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每天都像过节一样。
阿列弗季娜·尼科拉耶弗娜正在家陪着孩子们玩,邻居的小孩慌忙地跑了进来,怯生生地说:
“阿列弗季娜太太,您的娜季卡喝醉了。倒在面包房旁边的水沟里。”说完就跑开了。
笨重虚胖的老太婆阿列弗季娜·尼科拉耶弗娜慌忙走出了家门,不出声地颤动着嘴唇。走了没多会她就气喘起来,于是她放慢了脚步,艰难地、每走一步都点头般地晃动着脑袋。
面包房离她的家不算太远,不过都是上坡路,因此阿列弗季娜不时停下来,喘一会儿气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