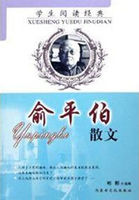“我家马蒂从来不打我一下。”她说,“正如你刚才所言,他一下班就闷声不响地回家,一句话也不说。他从来不带我上街逛逛,在家里老是坐在椅子里消磨时间。他也买东西给我,但是每次总是闷闷不乐的,因此我也不稀罕那些东西。”
卡西迪太太伸出一只胳膊抱住她的好朋友。
“我很同情!”她说,“可是,不是人人都能找到一个像杰克那样的丈夫。假如大家都像他,婚姻就无缺憾了。你听说过那些心怀不满的妻子吧?她们缺的就是一个男人回到家里,每星期踢断她一根肋骨,然后用接吻和巧克力奶油冰淇淋来补偿。这样的生活才是她们需要的。我要的是一个有主人派头的男人,喝醉了揍你一顿,没有喝醉抱你一阵。我从不想与那种没有魅力的男人交往。”
芬克太太叹了口气。
正在这时,门突然被打开,紧接着一阵响动在过道传来,是卡西迪先生回来了,只见他两只胳膊都夹着包裹。玛米飞身向前吊住他的脖子。她那只完好无损的眼睛里闪烁着爱情的光芒,与那个被追求她的人打昏并拖到茅屋里来的毛利女郎醒过来时眼中闪烁的光毫无二致。
“噢,亲爱的!”卡西迪先生高声大叫。他丢开包裹,用力地抱着她举了起来。“我买了巴纳姆·贝利剧场的票;如果你打开那个有绳子的包裹,你一定会发现那件绸衬衫——哦,晚上好,芬克太太——我才见到你,对不起。老马蒂近来好吗?”
“他近来不错,噢,谢谢你的问候。”芬克太太说,“我得上楼去了,马蒂快回来吃晚饭了。明天我将你要的花样带下来给你,玛米。”
芬克太太上楼来到自己的房间,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是一种说不出什么名堂的哭泣,这种哭泣只有女人才懂,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只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这是女人伤心时短暂而绝望的哭泣。难道他对她根本不关心?他们从不拌嘴,他回到家里就懒洋洋地东靠靠,西靠靠,一副忧郁、痛苦的样子,他倒是个蛮不错的供应商,可是他忽略了生活中的香料,无法使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芬克太太感觉生活中的船要停泊了,好没意思,她的船长的活动范围介于葡萄干布丁和吊床之间。他要是时不时走过来拍拍船帮或者在后甲板上顿顿脚该多好!她多么希望有一次开心的航行,在快乐岛的几处港口逗留。而现在,她的这个美好愿望看来是无法实现了。她同她的练拳对手在平平淡淡的若干回合中,没留下一处伤痕可以给人看,她厌烦透了。在这方面,她一度痛恨过玛米。看那玛米,时时带着伤口和青肿——礼物和接吻是她的止痛药膏——同她那好斗的、粗暴的、可爱的伴侣正进行着一次难忘的开心的航行。
芬克先生七点钟回家。他恨透了家务事,也不喜欢在安乐舒适的家门以外闲逛。他是坐有轨电车上下班的人,他是吞食了猎物的蟒蛇,他是倒下来就躺在那儿不动的大树。
“晚饭怎么样?合不合口味?”芬克太太问马蒂。
“唔!不错,很好吃。”芬克先生咕哝了一声。
吃过晚饭,马蒂单穿着袜子,找了张报纸,坐在那里看。
起来吧,新时代的但丁,为我歌唱地狱里最安全的角落,好让那光穿袜子坐在屋内的先生有个好去处。耐心的姊妹们由于亲属关系或者责任心通常会无任何怨言,不管他的袜子是丝的、棉纱的、莱尔线的,还是羊毛的,难道除了一言不发,就不能写出新的一章?
第二天是劳动节,卡西迪先生和芬克先生一整天不要上班。工人们得意洋洋地参加游行,或者聚在一起取乐。
芬克太太一早就把花样给卡西迪太太送过来了。玛米已经穿上了新的绸衬衣,连她那只挨了打的眼睛都勉为其难地放射着节日的光芒。杰克的忏悔是慷慨大方的,他们已经订了美妙的计划,包括逛公园、野餐、喝比尔森啤酒。
芬克太太是充满复杂的心情回到自己房间的。玛米是多么幸福,虽然这种幸福使她伤痕累累,但也是有补偿的。这种幸福能让玛米一人独享吗?马蒂·芬克同杰克·卡西迪肯定不相上下,难道他妻子就永远不挨揍也得不到爱抚吗?芬克太太突然想到一个让她自己都感到窒息的主意。她要让玛米瞧瞧,她的丈夫也会动拳头,事后说不定比杰克更为情意绵绵。
对芬克一家来说,劳动节过得同平时的假日一样正常。厨房里的洗衣槽里,两个星期的脏衣服已经浸泡了一夜。芬克先生单穿着袜子坐着看报。难道劳动节就是在劳动中过去吗?
妒火在芬克太太的心中升高,而升得更高的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如果她的先生想揍她——如果他一直不想表明自己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有他的特权,不想表明对夫妻关系的兴趣,她就得刺激他尽他的本分。
芬克先生点着烟斗,用穿着袜的脚趾轻轻地擦着另外一只脚的脚踝。他很满意目前这种生活状态,就像一块未溶化的羊油嵌在布丁里面,这就是他的平稳的极乐世界——舒舒服服地坐着,从报纸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耳听妻子洗衣服时肥皂水的溅泼声,闻着已收拾进去的早餐和即将摆出来的午餐的美味。他满意极了,他心里又怎么会冒出打老婆的念头。
芬克太太开了热水龙头,将搓衣板插进洗衣槽。这时,卡西迪太太开心的笑声传了过来。这笑声像是一种嘲弄,是向楼上从未挨过揍的新娘卖弄自己的幸福。芬克太太该采取行动了。
她突然像个泼妇似地转向那个看报的人。
“你这游手好闲的懒鬼,”她大叫道,“我整天不休息,忙得焦头烂额来服侍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到底是人还是离不开厨房的狗?”
马蒂惊愕地抬起头,一时间他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芬克太太怕他不会动手,因为还没有惹得他上火,就跳上前去,朝他脸上狠狠地一拳,同时对他感到一阵热爱,那是她好些时日都没有感到的。“你站起来,马蒂·芬克,拿出你的魄力!”啊,她想就要感到他拳头的分量了,只为了表示他关心她,只为他心中还有她。
芬克先生跳了起来,因为玛吉另一只手猛地一挥击中他的下巴。在这可怕而又幸福的时刻,她闭上了双眼,等候他的回击,快来吧!她念着他的名字,她向盼望中的一击迎过去,为这一击她等得好辛苦。
在下面一层的套房里,卡西迪先生正满脸愧色地替玛米的那只眼睛搽粉,准备出游。从楼上传来女人的洪亮的声音,毫无疑问是家庭冲突发出来的声音。
“马蒂同玛吉在吵架?”卡西迪先生猜测,“想不到他们也来这一手。我要不要跑上去,问他们要不要纱布卷儿?”
卡西迪太太一只眼珠亮得像钻石,另一只至少像浆糊。
“哦!哦!”卡西迪太太突如其来地含含糊糊地应着,“噢,你先别去,让我——让我先去看个明白。”
她快步登楼。她的脚才踏上上一层楼房的过道,芬克太太就从厨房门口猛地奔了过来。
“啊,玛吉,”卡西迪太太压低嗓音愉快地叫道,“怎么?他打你了?啊,他打你了?”
芬克太太奔过来,脸贴着好友的肩膀,伤心地哭泣。
卡西迪太太捧着玛吉的脸,轻轻地抬了起来,看见她满脸泪痕,红一阵,白一阵,可是在她那又白又红、带着雀斑的柔软的漂亮脸蛋上却找不到被打的痕迹。
“告诉我,玛吉,”玛米求她,“让我进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打你了吗?他怎么动的手?”
芬克太太的脸又一次失望地埋到她好友的怀里。
“求求你,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进去。”她哭泣道,“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声张。他没有打我,一下都没有,他——他在,啊,上帝,他正在洗那堆脏衣服。”
出名
——[俄国]契诃夫
米佳·库尔达罗夫深夜闯进父母家,神情亢奋。
全家人十分震惊,米佳把一份报道自己发生交通事故的报纸交给了父亲。
夜里12点钟,米佳·库尔达罗夫疾风般地冲进父母的住宅,转眼间跑遍了每个房间,神情十分激动。那时父母已经上床休息了,妹妹还躺在被窝里读着一本小说的最后一页,几个上中学的弟弟也已经睡着了。
“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双亲惊奇地问道,“告诉我,孩子,你怎么了?”
“噢,先别问!我怎么也没料到!没有,我怎么也没料到呀!这……这像做梦一般,太出人意料了。”
米佳哈哈大笑起来,坐到安乐椅上,他兴奋得站也站不稳了。
“这怎么可能?你们想像不到!”
妹妹跳下床来,把一条被子披在身上,走到哥哥跟前。几个弟弟也醒了。
“发生了什么事?你脸色不好呀!”母亲又一次关心地问道。
“我没什么,真让人高兴,好妈妈!要知道,现在整个俄罗斯都知道我了!真的!以前只有你们知道这世界上有个十四等文官米佳·库尔达罗夫,而现在呢,整个俄罗斯都知道了!好妈妈!哦,太不可思议了!”
米佳跳起身来,又跑遍了每个房间,然后又坐下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给我们说清楚吧!”
“你们不问世事,从来不看报纸,也不注意众所周知的事情,可是报纸上有那么绝妙的东西啊!只要有什么事情发生,马上就会公诸于世,什么也瞒不住。我是多么幸福啊!啊,上帝呀!原先只有知名人士上报、出名,而现在我也上报了,我出名了!”
“你说什么?在什么报纸上?”
父亲脸色变得苍白起来,母亲望着圣像,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弟弟们跳下床来,都穿着一个式样的短睡衣,走到哥哥跟前。
“不错!报导我!现在整个俄罗斯都知道我了!您,好妈妈,把这份报纸收起来作个纪念吧!没事拿出来读读。你们请看!”
说着米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递给父亲,用指头戳戳蓝铅笔画过圈的地方。
“看一看吧!”
父亲戴上眼镜。
“快点呀!”
母亲望着圣像,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父亲咳嗽了声,念起来:
“12月29日晚上11点钟,十四等文官米佳·库尔达罗夫……”
“听见了吗?我出名了,快,不要停下来,接着念。”
“……十四等文官米佳·库尔达罗夫走出坐落在小勃龙纳亚街的科兹欣啤酒馆时,已醉得不成样子……”
“我这是和谢缅·彼得罗维奇在一块……一切细节都写到了!接着念吧!念下去!听着!”
“他已走不稳路了,突然,他跌倒了,正倒在停于该处的一位马车夫的马蹄子底下,马车夫是尤赫诸夫斯基县杜雷基纳村的一个农夫。受惊的马从库尔达罗夫的身上跳过去,拖着的雪橇从他身上辗了过去,车上面坐着莫斯科的二等商人斯捷潘·鲁科夫。马在大街上狂奔,但终于被几个看管院子的人拦住了。起初库尔达罗夫人事不省,被送至警察局,医生给他作了检查,说他的后脑勺受到撞击……”
“那是碰在车辕上所造成的。好爸爸,别停下来,继续念!”
“……他后脑勺受的撞击系轻度的震荡。警察对事件的发生经过作了记录。受伤者已予以治疗……”
“他们叫我用凉水冷敷后脑勺。没有了吧?对,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现在全俄罗斯都传开了!快拿过来!”
米佳接过报纸,郑重叠好,放进了口袋。
“我得让马卡罗夫看看去,还要给伊丽尼茨基一家人看看,还有娜塔莉娅·伊万诺夫娜、阿尼西姆·瓦西利伊奇,我都要让他们知道,我去了,回头见!”
米佳戴上别着帽徽的制帽,又兴奋地、疾风般地冲出了家门。
第一次登台演出
——[前苏联]H.伊萨耶夫
由于剧中主角突然发病,我被迫临时上场。 舞台上,我与另一主角配合得一团糟,却赢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一位在本世纪非常有名的戏剧演员讲述了自己第一次登台演出的过程。
“我初次登台演出是在外省,当然,那个剧的名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剧本是我们剧院老板的弟弟写的。
“在剧中,我扮演一个小角色。我整个的戏就是走进商人梅尔卢佐夫家的客厅并且说:‘先生,普罗科普·普罗科普耶维奇来了。’梅尔卢佐夫回答说:‘请。’接着,我就出戏了,上场的该是悲剧演员藻霍夫,他扮演梅尔卢佐夫的一个股东。
“我的那句台词已被我背得滚瓜烂熟了。演出前一整天,我都在田野里向大自然寻找灵感。演出开始了,我迈着发抖的脚步来到前台,我小声说:‘先生,普罗科普·普罗科普耶维奇来了!’梅尔卢佐夫说:‘请。’我转过身,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来到后台的。刚到后台一下子就倒在助理导演的身上了。可他严肃而明明白白地对我说:‘喂,老弟,你听好,悲剧演员藻霍夫,就是你刚才报告说他来了的梅尔卢佐夫的那个股东生病了……你瞧,他睡得像死人一样。现在只有一个应变办法,刚才你在台上讲的话反正观众谁也没听见,你告诉梅尔卢佐夫说,你来了……他懂!’
“助理导演不由我说什么,就把我推向前台。我又出现在梅尔卢佐夫的客厅里。我走近茶炊,恭恭敬敬地说:‘先生,我是普罗科普·普罗科普耶维奇,我来了。’接着傻乎乎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场内一片寂静。谁也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梅尔卢佐夫非常焦急,他猛然站起来在舞台上走圈子,两眼发出炯炯光芒。他大声喊叫,因为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该如何做。
“然后,他走到我身边,气愤的脸都抽搐了。他问:‘喂,怎么样?和我合伙买条货轮?’
“他那副要吃人的样子令我非常害怕,我又怎能不跟他‘合作’?我吓得脸色苍白,手里的茶杯也掉在地上了,我赶紧站起来说:‘好!’
“梅尔卢佐夫听后一下坐到椅子上,好像挨了一颗子弹似的。本来第一幕结尾和整个第二幕他都要劝我同他合伙买货轮,而我本应不同意这种做法,直至最后,我都要拒绝他。我现在突然表示同意,梅尔卢佐夫简直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他的妻子、正剧演员基尔金娜想赢得时间挽回局面,便介绍我同他们的女儿娜斯坚卡认识。我早对娜斯坚卡一见钟情,因此,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把椅子靠拢她身边。
“这时候梅尔卢佐夫镇静下来了,他建议沿伏尔加河往下游走。我当然没有意见,表示同意。梅尔卢佐夫又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去了。因为戏剧的主要冲突是梅尔卢佐夫要乘刚买的轮船沿伏尔加河往下游走,而我,即普罗科普·普罗科普耶维奇却与他意见相反,坚持要往上游去。
“现在我把梅尔卢佐夫要和我绝交的主要王牌无情地打掉了,他现在真的是毫无办法了。在这难堪的寂静中,我在想对娜斯坚卡说什么话好呢。但是她的母亲抢在我的前面了。
“她说:‘普罗科普·普罗科普耶维奇,您看,娜斯坚卡长得那么漂亮,做一个未婚妻该有多好……’
“我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幕落。
“在后台,梅尔卢佐夫走到我跟前,狠狠地提起我的西服领子说:‘你信不信,如果你再讲话,我会掐死你。’
“当第二场开始的时候,梅尔卢佐夫悲痛地告诉观众,刚买的船在离萨拉托夫不远的地方沉没了,他也因此破产了。全场观众看着我,期望我讲两句关于我的生意的事,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说。
“梅尔卢佐夫来到妻子和女儿跟前,又向她们重说了一遍刚才向观众说过的关于轮船沉没的话。以后的剧情是:梅尔卢佐夫的妻子回娘家了,他女儿——娜斯坚卡进了修道院,而破了产的梅尔卢佐夫沦为乞丐到处流浪。这时,我突然感到,舞台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舞台后面也没人了。
“我面色苍白,站起来离开茶炊,神情凄惨地向观众伸出一只手,用颤抖的声音问道:‘先生们!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幕落。
“第二天,当地的省报写道:我们欣喜地发现一个悲剧天才在昨天的演出中初露锋芒。这讲的就是我。”
错误
——[前苏联]左琴科
列宁让值班秘书送来一份农业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名单, 却说成“我要农业人民委员会的全体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