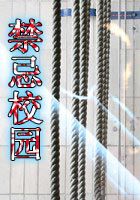“说实在的,你盼的不是儿子,盼的是旗王爷的宝石顶戴。可是,那颗石头真有那么好吗?我倒觉得那颗破石头是个祸害,让骨肉分离,兄弟成仇。谁要是迷上那颗石头,谁就会疯了。”
太阳落山前,自黄河西岸划来一条木船。一个下身穿着肥大短裤、光着膀子的汉子划着桨,一个喇嘛牵着马站在船上,那人是金巴。船行至黄河东岸,金巴牵着马走上了岸。船夫将船拴在岸边的桩子上。
“船也要拴吗?怕它跑了?干脆上了羁靽算了。”金巴哈哈大笑。
“不是船自己要跑,是担心黄河水把它带跑。”船夫回答说。
黄河岸边草丛中飞出很多蚊虫,向他们二人袭来。二人拔了一把草挥舞着赶蚊子,爬上陡坡走到了船夫住的窑洞前。
“您就在外面坐一会儿。我也是不住窑洞里的,里面全是耗子。我烧点水吧。”船夫说。
“跟耗子为邻,看来你过得可够热闹的。”金巴说着坐到窑洞门口的石块上。
“以前下雨的时候,没办法得进窑洞睡。但自从上次那件事后,我发誓再也不住窑洞了。”船夫边说边忙活着烧水。
“上次怎么了?”
“下了一场大雨。除了我,其他船夫都缩在窑洞里,结果全部被黄河的洪水冲走了。唯独我当时没在窑洞里,所以逃了一命……”
“下大雨时你不在窑洞去了哪里?睡在外面?”
“我想,真是佛祖保佑我避开了一场灾难。”
“佛祖?什么佛?”
“您听我说呀,下雨的那天,我起初也在这个窑洞里睡来着。闪电雷声不断,河床里的黄河水咆哮不休。我忽然听见一个女子来打我的门……”
“女子?来救你的是一个女佛?”
“我出去一看,见一个年轻女子,后面还有几个人牵着马。趁着闪电的光亮,还看见一个健壮的喇嘛被绑着站在他们中间。我怕是强盗来了。”
“被捆绑的喇嘛?”金巴忍不住问。他想到了失踪的旺丹。
“是啊,身材高大的那个喇嘛双手背过去被捆了一个结实。那个姑娘说,帮我们渡一下河。我说,黄河是不能在夜里渡的,再说下着这么大的雨呢。姑娘向我扔了一小袋银子说,你若帮我们渡了河,这袋银子和我们牵着的马都归你。你若是不肯,我们现在就把你扔进河里。我没办法,只好说可以……”
“真的让他们渡了河?”
“我的佛爷!那一晚,我以为自己死定了。那也没法子。我领着他们上了船。在大浪中,船简直像一片枯树叶子一样……我别说划桨了,站都站不住,只好趴在船上,死死抓住了船沿儿。他们虽然也跟我一样趴倒了,却在哈哈大笑。不管怎样,船到了黄河西岸。他们带着被绑的喇嘛消失了。我有气无力地躺在黄河岸边上,知道自己还活着,但还是怕被洪水卷走,又赶快站起来拼命地往高处跑……”
金巴想,旺丹是从这儿被带过黄河的。
“你说的佛,就是那些人?我听着怎么像是强盗?”
“是佛啊,肯定是佛。那些佛来,才让我避开了一场灾难……”
“你怎么说他们是佛呢?”
“就说他们的头头,那个年轻姑娘吧,也就是二十岁左右的年纪。但她那种坚定的样子,果敢的气势,看起来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一样呢……”
“你仔细说说,是怎样的姑娘?”金巴问。他知道,要了解绑架旺丹的是什么人,这很重要。
“天仙一般美貌的女子。两个耳朵上戴着金耳坠。我从未见过那样的耳坠……”
“什么耳坠?”金巴紧追不舍。
“两只耳朵上戴了两匹金马。”
那定是专门定做的耳坠。专门定做金耳坠的,定是特别富有的人家……金巴想着。
“然后呢?”
“他们走了以后,我跑到高处又躺了半天。那时候已经是早晨了。我看到黄河东岸拴着几匹马,那是那些人留给我的马,也就是说,它们已经是我的马了。我又想到有了一小袋银子,一摸裤腰,小袋子不见了。当时我夹在裤腰上,想必是在洪水中掉了。不过,我没觉得遗憾,活命最要紧。再说黄河东岸的那几匹马都是我的了。我在黄河西岸上发愣了一整日。黄河水红浪翻滚。真不知我昨夜怎么安然无恙地渡了这大水?想想就觉得后怕。第三日,我划着船回到了黄河东岸。一看,我的佛啊,跟我相邻而居的船夫们跟他们的窑洞和草棚都不见了。因而我才知道,那一夜一个女子带着几个人逼迫我渡黄河,是为了救我的命。那是你们蒙古的女佛啊,我的佛……”
“你那几匹马呢?”
“从黄河西岸看的时候,几匹马还拴在东岸来着。但等我划到东岸时它们都不见了。”
“那你银子也没了,马也没了啊。”金巴笑。
“是啊,不过,那两天我是个富人。我有满袋子的银子,还有好几匹马。”船夫也笑。
“可惜你拥有那些东西的时间也太短暂了。”
“可不是?等以后我的两个儿子长大成人时,我会告诉他们,你们的父亲曾经是个富人呢。只是后来我那些财产都被黄河洪水卷走了,所以才变成了穷人……”船夫说着大笑。
“你说他们带着一个被捆绑的喇嘛?”金巴又问了一次。
“那个喇嘛十几天前又从这里向东渡了黄河。是我帮他渡河的。”船夫说。
“什么?”
“那是十几天之前的事。那晚我刚要回黄河东岸,身材高大四十多岁的一个喇嘛来了,求我帮他渡黄河到东岸。我刚想让他交银子,定眼一看便认出是那一夜被绑架的喇嘛。我没敢说什么,就帮他渡河了。”
“那喇嘛去哪儿了?”
“谁知道呢?下了船就向东跑了……”
金巴再也没说话。他明白了,旺丹被人绑架由此到西,又在十几天前从这里东渡。黑夜来临,远近被黑雾吞没,岸下黄河呼啸着。蚊虫一刻不停地袭击着他们。
“你一直在这里待下去吗?”金巴问。
“待着吧,过两年把老婆孩子接过来,养猪养鸡,黄河岸边也可以种点什么,就这样过日子呗。”船夫说着,用汗衫擦着赤裸的胸脯。
万年不息的黄河之水,在他们脚下滚滚流淌……
乌仁陶古斯回旗府住了半个月,又回到了满巴扎仓。阳光明媚的一天,乌仁陶古斯的侍女色日吉手持针线坐在转经路边大石块儿上,像是在缝着什么。正在这时,苏布道达丽走了过来。
“缝什么呢?”苏布道达丽问。
色日吉害羞地笑了笑:“哈屯让我缝这个东西,我不大会呢。”
“缝得不错呢,你真手巧。”苏布道达丽夸赞着她,细看她手中是一件婴儿服。
“是婴儿服?”苏布道达丽问的时候脸都白了。
“是呢……”
“给我看看。”
色日吉把手里的婴儿服递给了苏布道达丽。苏布道达丽翻来覆去地看,果真是一件婴儿服。
“你家哈屯……怀孕了?”
“不知道啊。”
这么点儿大的孩子知道什么呢,苏布道达丽想着回头走去。说实在的,有什么可问的?一见缝婴儿服,她就断定乌仁陶古斯肯定是怀上了。多年较量的结果,我们还是输了。这么一想,她心里愤愤不平,眼泪哗啦流了下来。
“啊,苏布道达丽哈屯啊,近来可好?”苏布道达丽听见声音抬头一看,金巴腋下夹着褡裢,自山下上来。她知道他最近一段时间出门了,骄阳野风中明显晒黑的脸上带着健康快乐的微笑。
“啊,您好吗?多日不见了,又去了哪儿?”苏布道达丽礼节性地问,金巴已走到了跟前。
“去陕西,又到了阿拉善……”金巴又说,“你的脸色不好,病了吗?”
“还好……”
“你还是为不能生孩子在发愁吧?有什么好发愁的?真是奇了怪了。”
苏布道达丽用无神的眼睛望着金巴。
“说实在的,你盼的不是儿子,盼的是旗王爷的宝石顶戴。可是,那颗石头真的有那么好吗?我倒觉得那颗破石头是个祸害,让骨肉分离,兄弟成仇。谁要是迷上那颗石头,谁就会疯了。”
苏布道达丽欲说还休,愣着。金巴却走了。
回家一看,老协理和诺日吉玛都不在。她趴在炕上哭了一会儿,慢慢平静之后,望着房顶出了神。金巴说的话,还在耳畔回响。她自问,我到底为何这般痛苦?
真的呀,千万个人都没有那顶戴,不是过得好好的吗?我怎么就为那个没用的东西发愁,陷进了这个肮脏的争斗呢?
回想这些年经历的事,苏布道达丽忽觉肮脏龌龊至极!金巴说得对,那颗石头真是一个折磨人的祸害。可我为何想得到那个不祥之物呢?
屋子里静静的。她一人坐了很久,心里宽慰了许多,多年的仇恨苦闷仿佛都在消失。
她舒了一口气,盛了一碗茶。想起十八岁嫁到这个家,在这个家生活了二十四年,等于傻傻地生活了二十四年!以为当了富贵官宦家的哈屯,一直很知足。其实真是傻透了!没有快乐,也没有爱情。每天恨别人,遭人恨,为那些无缘由的恨而着急上火,还被推进最讨厌的喇嘛怀里……这个家不是人待的地方,是酝酿阴谋仇恨的地方,如狐狼之窝一般恶臭难耐……
苏布道达丽想着,金巴洁白的牙齿,俏皮的笑脸仿佛就在眼前。人这个东西真是奇怪。她见了油嘴滑舌的更登就厌恶不已,而对金巴却很有好感。是的,金巴一见面就嘲讽她,还流露些许看不起她的样子,但也不难看出,他也在为她惋惜。一想起比自己小十岁的金巴,她心里居然很是温暖!她还想起,有那么几次,金巴跟她说了几句笑话走掉时,自己久久望着他的背影……
她明白了金巴为何总是快乐而信心十足。因为他不使阴谋,不怀恶意,没有贪念,坦坦荡荡,那样的人怎能不快乐呢?好了,让人家快乐地生活下去吧,像我这样肮脏的人,想人家做什么?心里祝福他好好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