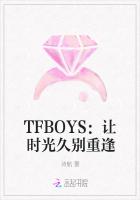“杜鹃”“咯咯”艳笑,并不回答,拉着张兆坤下了黄包车。她搂着张兆坤,进了“浣纱楼”妓院,来到自己的闺房,让小傻子等在门外。
刚走进闺房,张兆坤二话不说,抱起“杜鹃”,扔在架子床上。他扒下“杜鹃”身上的袄裙,如同发情的公狗,跳在她身上,疯狂地冲杀着。直到心满意足地过足瘾,张兆坤方才如释重负,喘息不止。
趁张兆坤兴致正好,“杜鹃”拉着他,笑“嘻嘻”地说:“奴家早就听说,你最喜欢娶姨太太,都不知道玩过多少女人,那就娶奴家当姨太太吧。”
张兆坤拍着“杜鹃”雪白的屁股,嘴里哼着《十八摸》,满不在乎地说:“奶奶的,俺今天就替你赎身,娶你当小老婆。至于你排老几,俺可是三不知,等查清再说。”
自从进了“浣纱楼”,连着十几天,张兆坤都没出来。陈光远见状,大喜过望,忙给九弟陈光逵发去电报。陈光逵本是第九混成旅旅长,带着本部人马,驻守在江西赣县,防备孙中山北伐。他接到陈光远电报,不敢怠慢,打开仔细观瞧。看罢,他马上召集第九混成旅士兵,端着曼利夏洋枪,连夜离开江西赣县,步行赶往宜春。第九混成旅士兵晓行夜住,隐蔽前进悄悄地来到宜春城外。
张兆坤离开宜春,总不见回来,暂编第一师士兵等得不耐烦了,又跑到道尹署大门外闹饷。褚玉璞、毕庶澄、傅铁嘴等人安抚不住,只得紧闭道尹署大门,不敢出来。关键时刻,陈光逵率本部人马,混进宜春城南门,将道尹署团团包围起来。褚玉璞、程善策、毕庶澄、傅铁嘴等人尚且不知,待到第九混成旅士兵杀进大门,他们来不及商量对策,都做了俘虏。只有程善策乘着混乱,跳过道尹署后墙,撒腿就跑。
陈光逵见状,带着第九混成旅士兵,在后面紧追不舍,嘴里大声喊道:“抓住那小子,别让他跑了。”
程善策吓得魂飞魄散,惶惶如惊弓之鸟,急急如漏网之鱼,狼狈逃出宜春城北门,躲到路旁树林里。陈光逵找不到他,让第九混成旅士兵胡乱放了几枪,只得悻悻离去。见第九混成旅士兵走远,程善策从树林里钻出来,直奔南昌而来。
眼见官长都做了俘虏,暂编第一师士兵乘机哗变,端着曼利夏洋枪,来到城里南大街,挨家挨户抢劫店铺。这里是宜春城最繁华地带,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哗变士兵蜂拥而人,把柜台、货架上的商品,抢个精光。就这样,数十家店铺的货物、钱财被抢光,掌柜、伙计被打伤。待到哗变士兵满载而去,陈光逵带着第九混成旅士兵,方才赶到南大街镇压,却发现哗变士兵早已一哄而散,踪迹皆无,不知去向。陈光逵接收张兆坤的十姨太金桂、十一姨太银杏、十二姨太慧慧、十三姨太霓裳、十四姨太扼子。
程善策来到南昌,悄悄地溜进进贤门。他在城里转了两天,打听到张兆坤住址,忙赶到“浣纱楼”,找到张兆坤。
两个人一见面,程善策痛哭流涕,哽咽着说道:“大帅,不好了,陈光逵带兵杀到宜春,解散了暂编第一师,俘虏了褚玉璞、毕庶澄、傅铁嘴……”
不等程善策说完,张兆坤如梦方醒,一把推开“杜鹃”,拔出毛瑟手枪,气急败坏地喊道:“奶奶的,俺上了陈光远的当,这就跟他拼命去!”
程善策抱住张兆坤,苦口婆心地劝解道:“大帅孤身一人,去了等于找死。趁姓陈的还顾情面,没对大帅动手,咱们还是赶快跑吧!”
张兆坤挣扎着,过了半晌,方才冷静下来,恨恨地说:“奶奶的,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便宜不了姓陈的,俺早晚要算这笔账。”
说罢,张兆坤、程善策、小傻子带着“杜鹃”,坐上黄包车,离开“浣纱楼”,赶到南昌火车站。他们坐上火车,沿着南浔铁路北上,在九江车站下车。他们换乘火轮船,溯长江西行,赶到湖北夏口。他们在大智门车站上车,沿京汉铁路北上,直奔北京。
张兆坤、程善策、小傻子、“杜在前门火车站下车,坐着洋车,回到“惜春院”。张兆坤板着脸,指着身后的“杜鹃”,对黄毕氏说道:“奶奶的,俺把她送来了,你替俺查一查,她排老几。”
黄毕氏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方才喜滋滋地说道:“大帅,奴家算清了,她该当十六姨太。”
张兆坤点点头,满不在乎地说:“奶奶的,其实甭管她排老几,只要能替俺挣大洋就行!”
程善策丢下张兆坤,悄悄地溜进五姨太红儿的闺房,两个人卿卿我我,好不亲热。张兆坤只当看不见,找“老鸨子”黄毕氏要过账簿,仔仔细细地核对账目,点收银圆。静下心来,张兆坤回首往事,愤愤不平。想当初,他拿红儿当诱俾,使用美人计,勾引程善策上钩,杀掉陈其美。想不到,今日他也中了美人计,因为“杜鹃”这个婊子,把好不容易拉起来的暂编第一师丢了,三不知变成二不知了。想到这里,他就觉得肉疼,少不得大骂陈光远几句。他找来“杜鹃”,拼命地折腾她,发泄仇恨。他折腾完了,又喊来小傻子,让他继续折腾“杜鹃”,弄得她鬼哭狼嚎,也不怕张大喜听见。
第二天,张兆坤带着小傻子,坐着洋车,离开“惜春院”。张兆坤赶到财政部,走进次长(副部长)签押房。他抬眼仔细观瞧,但见签押桌后面,坐着一个中年人,油头粉面,西装革履,煞是精神。
看罢,张兆坤一屁股坐在沙发椅里,让身子上下弹了弹,眼睛紧盯着中年人,大大咧咧地问:“俺是暂编第一师师长张兆坤,你是潘次长?”
中年人微微一笑,朝张兆坤点点头,彬彬有礼地答道:“俺就是潘复,潘馨航,不知大帅有何贵干?”
张兆坤欠起身,喜出望外,忙不迭地说道:“听你口音,也是山东人,咱可是老乡。财政部欠俺的军饱有二十万个大洋,得赶紧补上。”
此刻,身为次长的潘复暂时代理总长(部长),大权独揽,说一不二。他略一沉吟,拿过中国银行的支票簿,在上面填写二十万个银圆的金额。他从签押桌后面站起来,把支票递给张兆坤,爽快地说道:“既然俺和大帅是老乡,肯定得帮忙,就把军饱如数发给大帅。”
张兆坤见状,从沙发椅上站起来,奔到潘复身边,急不可耐地接过支票。反反复复地看罢,他不由得咧开大嘴,“呵呵”笑了,大声夸赞道:“奶奶的,潘次长果然爽快,你这个朋友,俺交定啦!”
潘复听罢,拍拍张兆坤的肩头,亲热地说:“大帅这么说,就见外了。今天晚上,请到寒舍玩一玩。”
有当时民谣为证: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遇老乡,舍命来相帮。
当天晚上,张兆坤坐着洋车,带着小傻子,嘴里哼着《十八摸》,来到西城石老娘胡同(今西四北五条胡同)潘复府邸。潘复早就等在府邸广亮大门外,待到张兆坤从洋车上下来,他走上前去,嘴里喊着“大帅”,一把拉住他,亲亲热热地走进广亮大门。
张兆坤一边往广亮大门里走,一边抬眼仔细观瞧,但见迎面是一座大影壁墙磨砖对缝,精雕细刻。拐过大影壁墙,就是外院,有三间青砖灰瓦的倒座房屋。他跟着潘复,穿过一座垂花门,绕过木制屏风,走进里院。除了身后垂花门,里院三面都是青砖灰瓦房,青砖到地墙面,灰瓦铺就硬山顶,房脊、房檐上装饰着砖雕。其中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正房、厢房前面,都有抄手游廊相通,廊边设有坐発、栏杆。院内青砖墁地,天棚上搭着葡萄架,葡萄架旁种着枣、石榴、海棠树,树下长着丁香、茉莉、月季花,另外还有太湖石、金鱼缸和盆景。正房后面,有一排两层髙的后罩房,也是青砖灰瓦房。正房与厢房拐角处有两个月亮门,分别通往东、西跨院。远远望去,东、西跨院都是硬山房顶铺着灰瓦,与中间四合院连在一起,形成东、西、中三个四合院。
张兆坤跟着潘复,嘴里哼着《十八摸》,迈进正房大门槛。屋里是方砖铺地,窗明几净,左、右有红木雕花隔断,把正房分成一明两暗三间,另外还有鹿顶、耳房、车房。如今正房被潘复当成赌场,有两个人围坐在红木八仙桌旁,正等着张兆坤打麻将。
潘复来到桌旁,指着一位身穿军服的人,向张兆坤介绍道:“这位是许琨、许教官,在曹大帅军官教导团当差。”
许琨朝张兆坤点点头,指着坐在自己旁边的女人,用淫邪的口吻说:“她是潘次长的姨太太,当年可是八大胡同的红姑娘,花名‘翠花’。”
潘复瞪了许瑕一眼,扭过头来,对张兆坤说道:“就他话多,大帅不要见怪,坐下来打几圈儿。”
听罢,张兆坤也不客气,坐在八仙桌旁,凑成一桌麻将。张兆坤是潘复的上门,吆三喝四地嚷个不停。几圈下来,他已经连闭三门,带来的赌注差不多都输光了。
张兆坤急红了眼,从口袋里掏出白天刚领的二十万个银圆支票,当场拍到八仙桌上,大声嚷叫道:“奶奶的,俺就不信,今晚翻不过本,咱接着来!”
这一把潘复继续坐庄,他手里握有一副好牌。花枝招展的“翠花”伸出玉手,摸了一张牌。她瞟了潘复一眼,打出一张“五条”。
潘复看到“五条”,登时眼睛发亮,兴高采烈地喊道:“俺和了,一条龙。”张兆坤见状,推倒麻将牌,把军饷支票推到潘复面前。他摇一摇头,埋怨“翠花”道:“奶奶的,你太笨了,咋总放炮。”
“翠花”扭过头来,强装笑脸,用揶揄的口吻问张兆坤:“奴家听说,大帅打牌没的说,今儿咋这么臭,跟打仗一样?”
张兆坤瞪了“翠花”一眼,从八仙桌旁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答道:“奶奶的,俺本想赌个心惊肉跳,没想到今天手气背,把军饷都输光了。”
潘复“哈哈”夫笑,用嘲弄的口吻说:“大帅独吞那么多军饷,今天才输这么一点儿,就七个不平、八个不愤。”
几个人还在斗嘴,张兆坤心里烦闷,围着八仙桌转圈儿。潘复见状,捡起桌上的支票,递到张兆坤面前,满不在乎地说:“大帅,快把支票收好,别耽误军务大事。”
张兆坤登时怔住了,过了半晌,方才迟疑不决地问道:“奶奶的,你这是啥意思?”
潘复把支票塞进张兆坤手里,和蔼可亲地答道:“咱们之间的老乡情义,不仅仅值这几个大洋。”
张兆坤热泪盈眶,激动不已,禁不住大声叫道:“奶奶的,潘次长够朋友,咱走着瞧!”
待到牌局散后,许琨凑到张兆坤面前,悄声问道:“暂编第一师散了架,大帅打算怎么办?”
张兆坤摆摆手,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答道:“奶奶的,俺现在是走投无路,能有舍好办法。”
许琨听罢,略一沉吟,用商量的口吻对张兆坤说:“既然大帅没有办法,不如买点礼物,去求曹大帅,事情兴许还有转机。”
“嗯——”张兆坤点点头,大大咧咧地说:“奶奶的「死马当作活马医,只能这么办啦!”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