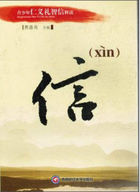乌林答没有做声,她捡起一根松枝,低着头在火塘边的灰里画道道,左一道右一道,好半会,她抬起头来,声音不髙,话语却是很坚定:“芍丹格格,我不是蒲公英,我是冬青,没有花,长在深山老林子里。不需要风,只需要雪花,在我和纳汉泰之间飘着的也是雪花“我知道他爱的是你“你也爱他。他的爱就像那飘着的雪花,只能一冬一季地在我心里想着,是不能有一生一世的。”
“乌林答,其实我……”芍丹很真诚地说。
“您别说了,”乌林答打断了她的话,继续说着,“现在你知道了我的心事,就把这事藏在我们俩的心里,不要再让第二个人知道,如果有第二个人知道了,也就是我离开虎尔哈部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亲人了,你和纳汉泰是我的亲人,我的命是你们给的,别因为这事让我离开这里,好吗?我不愿意离开你们、离开虎尔哈部。芍丹格格,你起个誓吧。”
“起誓?”芍丹沉吟着,看上去她有点左右为难。
乌林答握着芍丹的双手央求着“有了你的誓言,我乌林答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离开虎尔哈部,和你和虎尔哈部一起,在这安车骨水边打猎捕鱼过日子。”
“乌林答,我……那你答应我,一定要在今年秋祭的时候,接受神赐给你的阿哥。如果你答应了,我就起誓。”芍丹看着乌林答的眼睛,“你能答应我吗?”
“我答应你。”乌林答的眼睛里闪着泪花,“我们到月光下去起誓吧,卧勒多妈妈的眼睛在髙阔的天空里看着我们,满地月光是我俩誓言的见证。愿她保佑我们,让我俩的爱在神圣的秋祭之夜都能如愿!”
春带着细雨和风远去,夏就如枝头上的小鸟,热烈地在树梢上鸣叫。
温柔的仲夏之夜,鹿群迈着小心翼翼的脚步踏着月光来到水边,吃着鲜嫩的苔藓。打红围的日子到了。这个日子也是格格们的好日子,满林子的鲜花将她们装扮得花枝招展。
夏天是女人的美丽季节。
一缕阳光从顶上射进撮罗子,芍丹在梳理着乌林答长长的头发小扎尔珊甩着小腿歪歪倒倒地跑出跑进一会儿跑进来高兴地说:“额娘,小鹿来了!”一会儿又跑进来兴奋地说,“额娘它舔我手了!”
看着他那激动的小脸,芍丹的心里就像是喝了蜜似的,“那是小鹿喜欢你啊。”
乌林答戏谑地拽着他的小手把他拉到自己身边:“小扎尔珊,那小鹿水亮不?”
“水亮!水亮!”小扎尔珊兴奋地叫着。
“那就让它也做你的额娘吧,好不好?”芍丹微笑地看着小扎尔珊,“以前,额娘也有个白鹿额娘……”
“赛音!赛音!两个额娘!”他跑到乌林答面前,拉着她的手稚声稚气地说着:“安布(姨),两个额娘!”
芍丹拿起一朵大红的芍药花,插在乌林答梳好的小板头中间。
“安布,水亮!”小扎尔珊张着双手扑到乌林答的怀里。
“小不丁点的,你小窝楞刚开口,就整天满林子地叫。告诉我,说我水亮,你呢?”乌林答亲了小扎尔珊一口。
“巴图鲁!巴图鲁!”小扎尔珊两手握成小拳头,一脸严肃认真的子。
“扎尔珊,巴图鲁可是要有本事的,”芍丹说,“走,咱们到外边去,你给额娘练个摔跤的把式瞧瞧!”
“芍丹!”有人在外面喊着。
听声音是纳汉泰,芍丹和乌林赶忙牵着小扎尔珊的手走出去。乌林答双手相握在腰间,略蹲了蹲,向纳汉泰和富察行礼。
“哎哟嘿,乌林答,你这一打扮,真是让我的眼睛都花了!纳汉泰,你看看,她戴上这花多水亮!”富察啧啧地称赞着。
纳汉泰朝乌林答看了看,赞赏地说:“哦,是水亮!真要把咱虎尔哈部的萨尔甘追都给比下去了!”
听到这句话,乌林答挺髙兴,她朝纳汉泰莞尔一笑,站在了芍丹的身边。
纳汉泰向芍丹送过去一个火热的眼神,走过去把小扎尔珊牵了过来,笑吟吟地说:“来,老远地就听你在喊巴图鲁,来跟我练两招。”
小扎尔珊跟在纳汉泰的身后,稚气十足地一招一式地摇晃着身。
“赛音!有架势,是个巴图鲁的样子!”人们都欢笑着给小扎尔珊手。
“芍丹,今天我和纳汉泰带人上蛤蟆沟去打围,你和乌林答就别去了。”富察走到芍丹身边,笑眯眯地说。
“行,乌林答,把我们酿的都柿酒给他们带上。”芍丹吩咐着。“哎!大伯,”乌林答扬手招呼着,“您快来闻闻,过了一个冬天,这酒可香了!你来尝尝吧。”
“哎呀,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富察眉开眼笑地牵过小扎尔珊,“小阿哥,来,跟我去尝尝去。”
“芍丹,过了这个夏天,咱们虎尔哈部就要举行秋祭了,我……”纳汉泰走到芍丹面前,刚想说什么,又突然停住了。
“怎么不说了?”芍丹微笑地问着。
“等到秋祭的时候,我,我要把天鹅翎插在你的头上……”纳汉泰心情激动,满脸通红兴奋而又低声地说,“我要做小扎尔珊的阿玛。”
上天!芍丹的心里顿时倒海翻江许久她才抬起头来看着纳汉泰那充满期待的眼睛,犹豫着说:“纳汉泰,你怎么想起提这事了?”“这事我已经颠过来倒过去的想了两年了,想到我和舒穆禄和你之间的,曾经有过的恩恩怨怨想到在洪水里我答应做小扎尔珊的干阿玛,想到舒穆禄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保住小扎尔珊,我就想要娶你做我的福晋。可是,我又不敢跟你提这事,我怕提起舒穆禄让你伤心,现在舒穆禄走了两年了,咱虎尔哈的日子也消停了,我想,该是来办我自己的事的时候了,你说吧,你愿意不,我可是铁了心地来给你说这事的。”
“你这一说,让我心里乱糟糟的,不知该说啥好。这事过了秋祭以后再说吧,这事是咱虎尔哈安定下来的第一个大秋祭还有好多的事等着我们去做呢。”芍丹的话说到这,她停了停,看了纳汉泰一眼,又把眼光投向了远处,担心地说,“我怕秋祭的时候……!
“不,我不能再等了,我已经等了那么多年了,芍丹,跟我在一起吧,我会好好地照顾你和小扎尔珊的,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呢?”
“纳汉泰,我……我没有忘记你所给我的爱,可是,以往秋祭的情景都还深深的刻在我的心上,我害怕,不知道这又一个秋祭,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情和爱。”
“芍丹,我们的苦难都已经过去了,这个秋祭,是我俩在一起生活的开始,当年,我俩是在林子里相识的,今年,在秋祭的大神树下,你将成为我虎尔哈的福晋,小扎尔珊将是我虎尔哈的贝子。”
过去的一切在纳汉泰的眼前旋转,不由得他心潮澎湃,他激动地从脖子上取出贴身戴着的玉鹰,温柔恳切的说:“芍丹,你看,这个玉鹰,是我阿玛给我留下来的,只有虎尔哈的福晋应该拥有它,等到秋祭,我和你跳了婚礼之舞以后,这个玉鹰就将是你的。”
芍丹愣了:这个玉鹰怎么跟自己的那个玉鹰一模一样午后的阳光直射而下,金色的河边一片宁静。
老人们心满意足地翻晒着木架上的皮毛和山菜,撮罗子里传出小哈哈珠子闹觉的哭声。
大树下,年轻的女人袒露着白花花的胸脯,将鼓胀的乳房送到小哈哈珠子的嘴里。
“哒、哒、哒……”一阵激烈的马蹄声打破了宁静的原野,几十匹红鬃烈马像天边的云,朝金色的河边涌来。
天啊!是魔鬼出现,还是森林里的野猪变换成了人形?
一人们地老子,们一鹰,皮。大的,们下来,的脊背,胸前的两块肉疙瘩油光铮亮。他们吵吵嚷嚷的,后来的人还没有下马,前面的人已点燃了虎尔哈部的大撮罗子。
老林子里顿时一片混乱,人们就像山火里的飞鸟,满林子乱窜。野蛮的男人们疯狂地洗劫每一个撮罗子,把来不及逃走的虎尔哈部人赶到河边。有一个人拽着乌林答也往这里走来,他得意地朝着看样子是头领的男人叫唤:“头领!看我整得这个娘们,咋样?”那男人一看,顿时心花怒放,他色迷迷地盯着乌林答的身子,狠狠地看了好几眼,哈哈地笑了起来,笑得肚子上的肉都颤抖起来“哈哈!”满脸络腮胡子的头领一把揪住乌林答,“我真是他妈的有福,这个地方有山有水,还有你这水亮的萨尔甘追,我不走了,留在这里做你的爱根!”
“放下,你把我放下!”乌林答着急地喊叫着。
“放下?等你把我侍候好了再说吧!”他一把抱起乌林答,夹在里朝子里。
野蛮的男人们眼睛放光,淫荡地咧着嘴哈哈大笑。
乌林答的身子被横抱在那头领的腰里,她死劲地挣扎。
“尊敬的安达!”芍丹从远处飞奔而来,她把小扎尔珊塞到老玛法的怀里,镇定地走上前去,眼睛直盯着那阴笑的头领,“你把她放下!”
“凭什么?”那头领斜棱着眼睛,“我完颜乌奇迈是要她做我的萨尔甘!”
听他这一说,乌林答一愣她开始更用力地挣扎一个劲地喊着:“乌奇迈你松手我是安车骨的乌林答格格!”
“你她妈的放屁,安车骨完颜部的人早就让去年的大水冲没了,你凭什么说你是他们的人,想来讹我完颜乌奇迈?你以为这是在林子里现捡貂皮?再瞎诈唬,我他妈的立马就在这要了你的身子!来没等他“人”字喊出来,迎面而来的芍丹猛地冲了上来,她一把就拽开了乌林答。没等乌奇迈回过神来她手里的匕首已封在他肥胖的脖子上!
那些男人们操刀要冲过来!
芍丹厉声喊着:“你们谁敢上来我就像攮野猪一样,立时让他死在这里!”
男人们都愣在了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乌林答,还不快跑,等什么?”芍丹着急地喊着,“快带领着大家跑啊!”
“大家快跑啊!”乌林答一喊,族众们立刻四散逃去。
野蛮的男人们蠢蠢欲动有人想去追。
“谁敢动一步!”芍丹眼明手快,手上的匕首压在那头领暴起的脖筋上厉声地警告那些男人,“你们看!”
锋利的刀刃贴着乌奇迈肥胖的脖子划下去血流了下来。他吓得脸都变了颜色像野牛一样地吼叫着:“别动,别动!谁他妈的再动一步我要他的命!”
温柔的山风轻柔地在蛤蟆沟里飞翔。
一群鸟儿扑啦啦腾空飞起,髙髙的蒿草地里走来一拨人,他们身背弓箭扎枪,肩上搭着鹿、狍子、野兔等猎物,一边走一边扯着嗓子唱情歌!
手捧一颗野草莓,送给巴图鲁阿哥,
饿了你就当饭吃,渴了你就当水喝:
鲜果放着不耐久,吃在嘴里甜着心窝:
你问我可要点啥?也要一颗野草莓。
“哎,我说,你什么时候改邪归正了,怎么不唱也要萨尔甘追?”“去,去,边儿去,我这阵唱不是给你听的,要跟你唱的话,你能跟我走?再说了,你就是跟我走,我也不能要你呀!”
“得,得,得,这两天刚有了一个相好的萨尔甘追,就美得不知道姓啥了,你那一箭,我早就射过了!”
“你们别在这说疯话了,今天晚上是月圆之夜,咱们就在河边点火吃烤肉,到那时候,看谁的乌春唱得好,谁的莽式跳得棒,谁的萨尔甘追水亮!”纳汉泰看到阿哥们一个个兴髙采烈,也来了兴致,他,髙说。
“哟,是什么风刮的,咱穆昆达也要跟咱们一样了?”有人打趣地笑着说,“是不是今儿个晚上,咱们虎尔哈部就得有个福晋了?”“我是说你们,可没说我啊,”纳汉泰赶快一本正经地说,“别瞎说,我的福晋可是要在秋祭的时候,正格儿定的。走,快走吧!”
“赛音!”人们奔跑起来,一会儿就钻进髙髙的蒿草地,把纳汉在了。
“看这帮小崽子,一提到萨尔甘追,就像是吃多了黄花的狍子,跑得那个快,等到了村寨就得醉倒了!”富察笑着回过头来说,“纳汉泰,你也真是该娶个萨尔甘追,咱们虎尔哈部该有个福晋了!”
“大伯,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纳汉泰说,“想听听您的意思。”“噢您的事主要还是你自己掂量,你相中哪个萨尔甘追了,快告诉我吧。”富察喜出望外,眉毛都翘了起来。
“我相中的是芍丹,等到秋祭的时候,我要正式娶芍丹做我的福晋。”纳汉泰郑重其事,一字一句地说着。
“你跟芍丹商量好了?”
“我跟她说了,她说要等过了秋祭再说我不想再等了,我就要在秋祭前的那天去跟她提亲。”
“好,小扎尔珊也该有阿玛了。你真沉得住气,不显山不露水的,怎么到今天才跟我说?”富察有点不高兴了,“你知道,我是把芍丹当成亲生的萨尔甘追看的。还跟我见外?”
“大伯我怎么能跟您见外?没跟您说是怕您跟着忙活操心,累坏了身子骨,所以才没跟您说。现在离秋祭还有一些日子,您啊,到娶她那天,您就以她阿玛的身份送亲,就妥了。”
“看你,又说外道话了吧?我告诉你,这事我愿意累,不累,我还不高兴呢。我呀……”
“穆一昆一达!”跑在前面的人着急忙慌地返回来,惊恐不安地边跑边喊,“穆昆达,不得了了,咱们的村寨起火了!”
“什么?”纳汉泰大吃一惊,他手脚并用地爬上高坡,他看到村在的,正出“快,快跑,咱们的村寨出事了!”
看到乌林答和族众们就像飞鸟入林般逃得无影无踪,芍丹毅然举起匕首朝自己的腹部中去。说时迟,那时快,那头领眼快手快地在空中抓住了她的手,扬起一脚把她踹倒在地!
“打死她!”一声号叫,野蛮的男人们一拥而上,拔下腰里的野猪皮长鞭,劈哩啪啦地抽打着倒在地上的芍丹。长鞭像一条条毒蛇在丹的身上乱窜,她被打得翻来滚去,皮开肉绽,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好了,好了,都退下,我要看看她还有什么鸡零狗碎的本事,敢他妈的在我的脖子上架刀!”乌奇迈狞笑着走过去一脚,踩在她的背上,阴阳怪气地说,“想死,能那么容易吗?六月的雪能成啥气候?你他妈的是个好角,我敬佩你!赏你个全尸,也不点你的天灯,咱们一报还一报,让你也享受脖子上架刀的滋味。来人啊!”
“唬!”四个牛髙马大的男人应声跪在地上,“听头领吩咐!”“把她给我绑起来,用四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给我绑紧了,让她自己找死!”
“唬!”四个男人凶神恶煞地扑上来,绑人的绑人,架刀的架刀,不一会,芍丹就被绑在髙大的木架上。
火辣辣的阳光直射下来,木架上的芍丹就像是被扔在河岸上的鱼,被晒得冒油,她的头无力地聋拉在刀架上,一道道锋利的刀刃上下。
“哈哈!”乌奇迈得意地对着芍丹狞笑,他双手叉在水牛般粗壮的腰上,扬着肥胖的脸,阴阳怪气地说,“怎么样,这味道咋样,是不是比一把刀难受?你就好好地熬着,等着晚上喂狼吧!”
“打啊!”一阵猛烈的喊声从野地里平空响起,十几个男人像从地上来一,着来。
“哈哈,他们的男人来了,”乌奇迈像老虎发现了野牛,有了被追杀的对象,他亢奋得满脸通红,眼睛发出血红的亮光,脖子上暴出的青筋激动地颤抖,张牙舞爪地挥着青石刀大叫,“哈哈!我们这群饿虎正等食呢,上都给我上,杀了这些男人,这些女人就是我们的了!上,上,给我上啊!”
“不要命的,上来吧!”纳汉泰抢起手里的青石刀,一刀向一个先冲上来的人劈了下去。那人“嗷”地叫了一声,倒在地上。
“谁敢上来,这就是他的下场!”话音未落,纳汉泰已像一阵旋风,刮到木架面前,刀一横,和同时冲上来的四个族人团团地围在了的面前,虎视眈耽地与野蛮的男人们对峙着。
“纳汉泰!”芍丹悲伤欲绝地说着,“你快走快走吧,族众们和乌林答都已经逃走了,你也快带着他们逃吧!他们是狠毒的恶狼,不要为了我……”
“不!要死要活,咱们在一起,在一起!”纳汉泰挥刀砍断绑在芍丹身上的鹿筋,用刀把架在她脖子上的刀挑落在地。
虚弱至极的芍丹身子一歪倒在纳汉泰怀里。
看着满身伤痕的芍丹,纳汉泰怒不可遏,他指着乌奇迈骂着:“你还是人不是?竟然对女人下毒手!我都替你害臊把你的下巴壳藏到裤裆里去吧!”
乌奇迈气急败坏,他指着纳汉泰大骂:“呸!你他妈的哈什玛(林蛙)开了膛腿还得瑟个什么劲?你们都死到临头了,还在我的面前横!痛快地把头送过来,受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