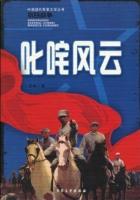“这么说来,妇女援助会要在壁炉山庄举办一场缝棉被聚会喽。”医生说,“苏珊,把你那些精美的盘子全都摆出来,还要多准备几把扫帚,又有一些人要名誉扫地了。”
苏珊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在她看来,男人根本就不了解某些事情的重要性。她觉得自己有点儿笑不出来,至少,等聚会晚餐的所有工作准备就绪,她才能松一口气。
“热的鸡肉馅饼,”她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土豆泥和奶油豌豆作为主菜,还有,亲爱的医生太太,这是个展现你新蕾丝桌布的好机会。溪谷村的人还从来没见过这种桌布呢,我相信到时候一定会引起轰动的。不知安娜贝尔·克洛看见它后会是什么表情呢,我很想知道。你会用你的蓝色和银色篮子装花吗?”
“是的,装上从枫树林里采来的三色堇和黄绿色的羊齿蕨。还有,我还想把你那三盆漂亮的粉红色天竺葵摆在屋里来。我们打算在客厅里缝棉被,如果天气暖和的话,我们就在门廊的栏杆边进行。我很高兴我们的花园里还有这么多鲜花盛开着。花园里从来都没有像今年夏天这样漂亮过,苏珊。我每年秋天是不是都会这样说?”
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准备。哪些人应该坐在一起,哪些人不应该坐在一起,比如说,西蒙·米利森太太就绝不能和威廉·麦克格雷太太坐在一起,因为她们之间有一些说不清的夙怨,从学生时代开始两人就不说话了。然后,还得考虑邀请哪些人参加的问题。除了妇女援助会的成员外,女主人还有权邀请一些宾客。
“我打算邀请贝斯特太太和坎贝尔太太。”安妮说。
苏珊看上去有些不赞成。
“她们都是外地人,亲爱的医生太太。”她说话的语气就像是在说,“她们都是鳄鱼”。
“我和医生也不是本地人,苏珊。”
“但是医生的叔公在你们搬来之前已经在这里行医几十年了。再说了,我们对贝斯特太太和坎贝尔太太一点儿也不了解。不过,亲爱的医生太太,这是你的房子,你想邀请谁就邀请谁,我没权表示反对。我还记得,许多年前,卡特·弗拉格太太举办缝棉被聚会的时候,也邀请了一位陌生的女人。她穿着棉毛绒布棉毛绒布:这种布料常用来缝制睡衣。衣服就来了,亲爱的医生太太,她说她从来不知道出席妇女援助会的聚会还要穿着正式!不过,这一点我们倒不用担心坎贝尔太太,她一向穿着都很得体。反正我是无法想象自己穿着绣满大朵大朵绣球花的蓝裙子到教堂去会是什么样子的。”
安妮也无法想象,不过她不敢笑出声。
“我倒是觉得那条裙子和坎贝尔太太的满头银发蛮相称的,苏珊。对了,她说想跟你要那道风味醋栗的食谱。她说她在收获节的晚餐上吃了一些,觉得味道很不错。”
“哦,好吧,亲爱的医生太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风味醋栗的。”随后,苏珊就不再对绣球花裙子发表什么不满了。即使坎贝尔太太下次穿着斐济岛本地人的草裙出现,估计苏珊也不会说什么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但是秋天还眷恋着夏天。终于,缝棉被聚会这一天姗姗而来,这天的天气一点儿也不像十月的天气,倒像是六月的天气。妇女援助会的成员能来的都来了,大家都满心期待着妙趣横生的八卦新闻和壁炉山庄的晚餐。此外,她们还可以饱饱眼福,欣赏一些可爱的时髦的新玩意儿,因为医生太太最近刚去了一趟镇上。
苏珊在厨房里忙进忙出,神气活现地在客房的女士们面前走来走去,向她们炫耀自己的围裙。她知道她们中谁都没有一条缀着五英寸长的钩针蕾丝花边的围裙,这条花边是她用第一百号丝线做的钩针蕾丝。一个星期前,就是这条钩针蕾丝花边,让苏珊在夏洛特敦展览上荣获了一等奖。她和雷贝卡·迪尤约好在那儿碰面,然后两人开开心心地逛了一天。当苏珊晚上回到家时,她觉得自己是整个爱德华王子岛最骄傲的女人。
苏珊表面上不动声色,可是思绪却异常活跃。
“西莉亚·瑞斯来了,她跟平时一样想来鸡蛋里挑骨头。她可别想在我们的餐桌上挑出什么毛病来。迈拉·穆雷穿着红色的天鹅绒裙子,对于参加缝棉被聚会来说,显得过于隆重了一点儿,不过她穿起来倒是挺漂亮的,至少裙子的面料是天鹅绒而不是棉毛绒布。阿加莎·德鲁,她像平常一样,眼镜用绳子系着。莎拉·泰勒……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参加缝棉被聚会了,医生说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不过,看她精神还挺不错!唐纳德·瑞斯太太,谢天谢地,她今天没有带着玛丽·安娜来,不过,不用问,她都会说出一大堆关于玛丽·安娜的事。上溪谷村的珍·伯瑞也来了,她可不是妇女援助会的成员。嗯,晚餐后我一定要仔细数一数汤匙的数量,这家人的手脚可不干净。坎德丝·克劳福德,她通常不太爱参加妇女援助会的聚会,不过,像缝棉被这样的聚会她可不想错过,这样可以展示她那漂亮的手和钻石戒指。艾玛·波洛克,她的衬裙都从裙子下面露出来了,当然,她是一个漂亮女人,可是这种女人都没什么头脑。蒂尔里·麦克阿利斯特,你可得小心点儿,不要把果冻打翻在桌布上,就像你在帕莫太太的缝棉被聚会上一样。玛莎·克洛瑟,你总算可以吃上一顿像样的晚餐了。你的丈夫不能一起来真是太遗憾了,我听说他每天只能吃些坚果之类的东西来充饥。埃德·巴科斯特太太……听说巴科斯特先生终于把哈雷德·瑞斯从米娜身边赶跑了。哈雷德是个软骨头,没什么骨气,正如《圣经》所说的,懦夫无法抱得美人归。啊,我们有足够的人来缝上两床被子,还有一些人可以帮着穿线。”
棉被铺在宽阔的门廊上,每个人的手指都和舌头一样快,手指飞舞,巧舌如簧。安妮和苏珊在厨房里忙着准备晚餐。沃尔特因为喉咙痛,所以那天没有去上学,他蹲坐在门廊的台阶上,隔着藤蔓看着缝被子的女士们。他喜欢听年纪比较大的人说话,她们说的那些关于四风港每个家族多姿多彩、或悲或喜、甜酸苦辣的人生戏剧,听起来惊喜交加,充满了神秘。
在所有的女性中,沃尔特最喜欢迈拉·穆雷太太。她的笑声最具感染力,她的眼睛周围的小皱纹洋溢着欢乐。她能把一个简单的故事讲得跌宕起伏,妙趣横生。她穿着樱桃红的天鹅绒裙子看上去令人赏心悦目。微微卷曲的黑头发,耳朵上戴着红色的小珠子,显得优雅得体。他最不喜欢瘦得像根针一样的汤姆·贾伯太太,也许是因为他有一次听到她说他是“一个病恹恹的孩子”。他觉得艾伦·米尔格雷太太看起来就像一只口齿伶俐的灰色母鸡,而格兰特·克洛太太就像是一只长了腿的木桶。大卫·兰森太太有着一头太妃一样颜色的头发,长得非常漂亮。当她嫁给大卫时,苏珊曾经评价说:“这个人太漂亮了,当农夫的妻子真是委屈了。”新婚不久的莫顿·麦克道哥尔太太看起来就像是一株枯萎的白色罂粟花。伊迪丝·贝利,是溪谷村的女裁缝,有着如轻云一般的银色鬈发和富有幽默感的黑色大眼睛,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一个老姑娘。他喜欢米迪太太,她是在场女性中年纪最大的,有着一双温柔、善解人意的眼睛,喜欢静静地倾听人家的谈话。他不喜欢西莉亚·瑞斯,她那不屑一顾的神情好像在嘲笑每一个人。
女士们还没有真正进入正题,她们还在谈论天气,讨论该在棉被上绣扇形图案呢还是钻石形花纹。沃尔特趁机利用这一时间欣赏周围的风景,世界好像张开了金色的臂膀拥抱着草地和树木。染上秋色的树叶渐渐飘落下来,砖墙旁边的蜀葵芬芳吐艳,白杨树沿着通向谷仓的小径一路施展着魔法。沃尔特陶醉在了如诗如画的美景中,当他被西蒙·米利森太太的发言拉回现实中时,女士们之间的谈话已经热闹非凡。
“那一家人因那场葬礼而远近闻名。大概你们谁也忘不了在彼得·柯克葬礼上发生的事吧?”
沃尔特急忙竖起了耳朵。这听起来似乎很有趣。但是令他失望的是,西蒙太太并没有说究竟发生了什么。看来,在场的每个人都参加了那场葬礼,要不然就是早已听说了这件事。“可是为什么每个人的表情都显得那么不自然呢?”
“虽然我们相信克拉拉·威尔森说的有关彼得的事全都是真的,但是彼得已经入土了,可怜的人,我们就让他入土为安吧。”汤姆·贾伯太太自以为是地劝慰大家,好像有人提议要把彼得从坟墓里挖出来似的。
“玛丽·安娜总是会说一些聪明话。”唐纳德·瑞斯太太说,“你们知道那天我们参加玛格雷特·霍利斯特的葬礼时,她说了些什么吗?她说:‘妈,葬礼上有雪糕吃吗?’”
一些女人听到这里心领神会地笑了,但大部分都没理会唐纳德·瑞斯太太。因为每次聊天,只要唐纳德·瑞斯太太一旦开口提到玛丽·安娜,她就会围绕玛丽·安娜说个没完没了。如果你给她一点儿鼓励,她的兴致会大增,更是喋喋不休。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不理会她,让她自讨没趣。如今,“你知道玛丽·安娜说了些什么吗?”已经成了唐纳德·瑞斯太太的口头禅,人人皆知。
“说到葬礼,”西莉亚·瑞斯说,“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康伯里·奈罗发生过一件挺恐怖的事。斯坦顿·雷恩去了西部,后来有人传言说他死了。他的家人发电报过去,让人把他的尸体装进棺材运回来,不久,尸体就被运回来了,负责葬礼事宜的沃莱斯·麦克阿利斯特建议他们不要打开棺材。葬礼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是还没等棺材入土,斯坦顿·雷恩本人却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后来大家一直不知道那具尸体是谁。”
“他们怎么处理那具尸体的?”阿加莎·德鲁好奇地问。
“哦,他们最后还是埋葬了他。沃莱斯说,葬礼不能延期。但是你根本不能说那是个葬礼,因为每个人都为斯坦顿的平安归来而喜出望外。道森先生把颂歌的最后一句话‘安息吧,基督徒’改成了‘令人惊喜的时刻’,不过多数人都认为他不该随意篡改。”
“你们知道玛丽·安娜前几天对我说了些什么吗?她说,‘妈,牧师是不是什么都知道?’”
“道森先生总是在紧要关头乱了章法,”珍·伯瑞说,“当时上格伦村还是他负责的教区之一。我还记得有个礼拜天,他把集会解散后,才想起还没进行募捐。因此他抓起一只捐献盘,跑到院子里一个个地讨。说真的,”珍补充道,“那些从未捐过的人碍于情面都捐了,他们不想当面拒绝牧师。但是,他那样做,实在有损他的尊严。”
“我最不满意道森先生的是,”科尼莉娅小姐说,“他在葬礼上的祷告词长得让人难以忍受。甚至有人都羡慕那些躺在棺材里的死人了。他在雷蒂·格兰特的葬礼上的祷告简直达到了他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我看见雷蒂的母亲都快昏倒了,因此我只好拿着雨伞狠狠地戳了一下他的后背,提醒他祷告已经长得让人忍无可忍了。”
“他埋葬了我可怜的贾维斯。”乔治·卡太太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尽管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二十年了,可是每当提到他时,她就会热泪盈眶。
“他弟弟也是个牧师,”克丽丝蒂娜·玛希说,“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还在溪谷村布道。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教堂里举行音乐会,因为他也是其中的一位发言人,所以就坐在讲台上。他跟他哥哥一样容易紧张,他坐在台上如坐针毡,坐立不安,他的椅子越来越往后退,突然连人带椅摔到了台下。我们在讲台下面摆放了一些花和盆栽植物,所以就只能看到他的一双脚跷在讲台上面。从那以后,他每次布道我都走神。他的脚实在是太大了。”
“雷恩的葬礼或许令人失望,”艾玛·波洛克说,“但至少比没有葬礼强多了。你们还记得克罗威尔家搞错的那个葬礼吧?”
提起这件事,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笑了。“给我也讲讲这个故事吧,”坎贝尔太太说,“波洛克太太,别忘了我们是新来的,对这里所有的家族传奇故事一无所知。”
艾玛不知道“传奇故事”是什么意思,但是她很乐意讲一讲这个故事。
“阿博纳·克罗威尔住在罗布里奇,他拥有当地最大的一片农场。在那个年代,他是一个风云人物,是托利派的要人,在岛上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娶了茱莉·弗拉格,茱莉的母亲是瑞斯家的,她的祖母是克洛家的,因此他几乎跟四风港的每个家族都扯得上一点儿关系。有一天,《企业日报》突然刊登了一条消息,说阿博纳·克罗威尔突然在罗布里奇去世,葬礼将在第二天下午两点举行。不知道为什么,阿博纳·克罗威尔本人并没有看见这则消息,当然那个时候乡下还没有通电话。第二天,阿博纳去哈利法克斯参加自由党的大会去了。两点钟的时候,人们陆陆续续赶去参加葬礼,大家都想早点儿去占个好位置,他们心想阿博纳是如此显赫的一个人物,去参加葬礼的人肯定会挤个水泄不通。的确,去了很多人,相信我。附近几英里的路上停满了双轮马车,一直到了三点钟,还有大量的人朝那里拥来。阿博纳太太气得都快发疯了,她努力想让人们相信她的丈夫并没有死。可是,起初大家根本就不相信她,她哭着对我说,他们似乎以为她把尸体埋起来了。后来大家终于相信了,但是却表现出一副很失望的样子,活像阿博纳就该死似的。而且他们还把阿博纳太太引以为傲的草坪和花圃践踏得不堪入目。凡是有点儿沾亲带故的,都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都打算在这里吃晚餐,住上一晚,但是朱莉家里并没有准备很多食物。当然,我们得承认茱莉并不会随机应变,这可把她忙得够戗。两天后,阿博纳回来了,而茱莉却病倒在了床上,她得了神经衰弱,花了好几个月才康复。她连续六个星期都没吃东西,嗯,几乎没吃什么东西,有人说,她后来曾说就算真的举办了一场葬礼,她也不会比当时那种情形更伤脑筋。不过我倒不相信她真这样说过。”
“那可不一定。”威廉·麦克格雷太太说,“人们在心情烦闷的时候,往往会说一些蠢话。茱莉的姐姐克拉莉丝,丈夫刚下葬的那个星期,就跟平常一样去唱诗班唱歌去了。”
“不仅连丈夫的葬礼没法影响她的心情,”阿加莎·德鲁说,“天大的事也不能影响她。她总是活得很快乐,喜欢又唱又跳。”
“我过去也很喜欢唱歌跳舞,在海岸上,那里没人听得到。”迈拉·穆雷说。
“啊,但是你现在变得理智成熟多了。”阿加莎说。
“不——,是更加愚蠢了。”迈拉·穆雷慢悠悠地说,“蠢得都不敢去海岸跳舞了。”
“刚开始的时候,”艾玛决心把被打断的故事讲完,“他们以为报纸上刊登的那则消息是谁在开玩笑,因为阿博纳几天前刚输掉了一场选举。但是结果发现,那则消息是为住在罗布里奇另一端的那个阿博纳·克罗威尔刊登的,他真的死了,不过在本地并没什么亲戚。事情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可是人们过了好久才渐渐忘记阿博纳带给他们的失望。”
“毕竟人们赶了那么远的路,而且还是在农忙时节,风尘仆仆赶去,结果却扑了空,难免有些失望,这也是很正常的。”汤姆·贾伯太太解释道。
“而且人们都喜欢参加葬礼。”唐纳德·瑞斯太太兴致勃勃地说,“我想我们都像孩子。我带玛丽·安娜去参加她叔叔戈顿的葬礼,她玩得开心极了,她告诉我说:‘妈,我们能不能把他挖出来,再将他埋回去,这样就可以多玩一会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