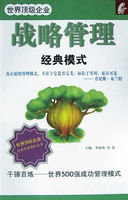“你真准备掺和这事,亲爱的医生太太?”苏珊问。刚才她在餐具室擦银餐具,听到了她们的大部分谈话。
“我不该吗?苏珊,我真想写篇‘扑闻’。虽然我很少见过安东尼·米切尔,但是我喜欢他,我敢肯定,如果他的讣闻就像《企业日报》上那种陈词滥调,他一定会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的。要是把安东尼惹急了,会有不少麻烦的。”
“安东尼·米切尔年轻时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亲爱的医生太太,不过他们说他有点儿爱胡思乱想。他跟贝丝·普拉姆并不般配,不过他的日子过得还算体面,也偿还了他的债务。当然,他娶了最不合适的姑娘。不过,尽管贝丝·普拉姆现在就像是情人节的滑稽演员,但当时她确实漂亮得像幅画。亲爱的医生太太,我们中的一些人,”苏珊叹口气总结说,“都记不起她当时的模样了。”
“妈咪,”沃尔特说,“后门廊周围都长满了金鱼草,在餐具室的窗台上有对知更鸟在筑巢。你不会把它们赶走的,对吧,妈咪?你别打开窗户,那样会把它们吓走的,好吗?”
安妮见过安东尼·米切尔一两次。他住在下溪谷村,那幢灰色的小房子在云杉林和大海之间,房子旁边有棵大柳树,就像是一把巨大的雨伞。虽然下溪谷村的人们大多数都找康伯里·奈罗的医生看病,但是吉尔伯特时不时要去安东尼家买干草。有次安东尼运了一车干草来壁炉山庄,安妮带着他参观这里的花园,他们发现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她很喜欢他。他满是皱纹的脸瘦削、友善,他黄褐色的眼眸透着勇敢、精明,从不迟疑,也从不会被欺骗——也许被骗过一次,贝丝·普拉姆的浅薄和美貌迷惑了他,将他骗进了愚蠢的婚姻中。然而他似乎从来都没有为此沮丧或不满意。他只要能耕种、栽种、收割,他就很知足,就像那片阳光照耀的老牧场一样。他的黑发日渐稀少,银发苍苍,他很少笑,有着淡泊宁静的心境。他耕种了一辈子的那块土地,给他带来了面包和快乐,征服的愉悦,以及对悲伤的安慰。现在,他就埋葬在那块土地附近,安妮真为他高兴。他也许“死得很开心”,不过他活着的时候也很开心。康伯里·奈罗的医生说,当他告诉安东尼·米切尔说可能没有康复的希望了,安东尼却笑着回答说:‘嗯,有时候,人生真是有点儿单调。现在我老了,死亡也许可以带来改变。我真的很好奇,医生。’甚至就在米切尔太太那杂乱无章的荒谬话语中,也能捕捉到安东尼真实的一面。安妮花费了一个傍晚的时间,在房间的窗边写出了《老人之墓》,并且很满意地诵读了一遍。
风的声音扣人心弦,
轻轻拂过松树林间。
海洋在轻轻呢喃,
声音越过东边的草原。
天幕垂下雨帘,
轻唱着让他长眠。
茵茵草地如此宽广,
绿色连绵四面八方。
耕种的农田丰收在望,
苜蓿上,斜照夕阳。
轻风送来果园的花香,
他种下的树茁壮成长。
哪怕星光黯淡无光,
也依然守在他的身旁。
旭日初升,灿烂辉煌,
阳光照耀着他的睡床。
沾满晶莹露珠的青草,
温柔地伴他进入梦乡。
在他生前的那么多年,
对万事万物都充满爱怜。
他已经在这里长眠,
他所钟爱的一切都与他相伴。
海洋的呢喃,
在为他唱着挽歌,直到永远。
“我想安东尼·米切尔会喜欢的,”安妮俯身探出窗户,感受着春天的气息。在孩子们的花园里,歪歪斜斜地冒出了几排莴苣。枫树林后的落日显示出轻柔的粉色。空谷那边传来了孩子们欢乐的笑声。
“春天是多么可爱啊,我真不想去睡觉,真不想浪费春天的任何时光。”安妮说。
一个星期后的一个下午,安东尼·米切尔太太来壁炉山庄拿“扑闻”。安妮心里暗自得意,对她朗诵了一遍,可是安东尼太太并没有显示出特别满意的神色来。
“哎呀,写得真的很活泼。你把很多东西都写得很好。但是……但是……你没有提到他去了天堂。你不能确信他到天堂了吗?”
“我太确定了,所以觉得没有必要专门提起,米切尔太太。”
“嗯,也许有人会怀疑的。虽然他是个绝对虔诚的教徒,但是他……他并不常去教堂。而且‘扑闻’中没有说明他的年龄……也没有提到花。唉,你为什么不提一提棺材上的花圈呢?我得说,花是最有诗意的东西呀!”
“真对不起……”
“哦,我不是责怪你,我根本不想责怪你。你已经尽力了,而且听起来也很漂亮。我该付多少钱?”
“什么……什么呀?不用给钱,米切尔太太。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嗯,我知道你很可能会这么说,所以我给你带了一瓶泡蒲公英的红酒。如果你老是打嗝,喝点儿会让胃舒服些。我本来还想带一瓶药茶的,只是担心医生会不喜欢,就没有带。如果你想要一点儿,又不想让医生知道,你只用给我说一声,我就会偷偷给你送来。”
“不,不必了,谢谢。”安妮淡淡地说。她还没有从“活泼”这个评价中回过神来。
“随便你。你最好还是留一点儿。今年春天我再也不需要购买什么药了。去年冬天,我的堂兄马拉奇·普拉姆死了,我让他老婆把他留下的三瓶药都给了我。这种药一买就是十二瓶。那个寡妇本想把剩下的这些药都扔了,不过我什么东西都舍不得浪费。我自己用一瓶就够了,我把另外的两瓶给了我的雇工。我告诉他说:‘就算这药没什么用,但是也不会有害的。’既然你不准备为这个‘扑闻’收钱,那我就实话告诉你,我真的舒了口气,因为我现在手头很紧。尽管在这一带,D.B.马丁的殡葬收费是最便宜的,但葬礼花费真的很大。我的这套丧服还是赊欠的。要是我不去把欠账结了,我就会觉得自己跟没有服丧一样。还好,我不用再买一顶软帽。这顶软帽是十年前我妈妈去世时我做的。幸好它和我身上穿的黑衣服还很相配,对吧?你真该看看马拉奇·普拉姆家寡妇的打扮,还有她那张黄蜡脸!好了,我得走了。我真的感谢你,布里兹太太,虽然……不过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而且那首诗还算不错。”
“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和我们共进晚餐呢?”安妮问,“家里只有我和苏珊,医生出门去了,孩子们要在空谷举办他们的第一次野餐。”
“我很乐意,”安东尼太太说着,高兴地坐回她的椅子,“真高兴能多待一会儿。等你老了,你也会懒得走动,而且,”她补充说,粉色的脸上浮现出陶醉的笑容,“我是不是闻到了油炸防风根的味道了?”
一个星期后,当安妮看到《企业日报》后,她几乎要心疼起她的油炸防风根了。在报纸的讣闻栏中,看到了那首《老人之墓》——但全文有五节,而不是原先的四节!第五节是这样写的:
一位出色的丈夫、朋友和帮手,他是上帝创造的最好的好人。
一位出色的丈夫,温柔又真诚,亲爱的安东尼,百万人中挑一就是你。
壁炉山庄的人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在接下来的那次妇女援助会上,米切尔太太对安妮说:“我在后面又添加了一节,希望你别介意。我只是想稍微赞美一下安东尼……是我侄儿约翰尼·普拉姆写的。只用了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把这一节写出来了。他就像你一样……他看起来不是很聪明,但是他会写诗。这是他母亲传给他的……她是维克福德家的人。普拉姆家的人一点写诗的本领都没有——一点都没有。”
“真遗憾你刚开始没有想到让他为米切尔先生写‘扑闻’。”安妮冷冷地说。
“可不是吗?但是我一心只想着为安东尼送别,都没想到他会写诗。后来他母亲给我看了一首他写的诗,描写了一只松鼠掉进一桶枫糖浆里淹死了……真的非常感人啊。不过你的诗也很好,布里兹太太。我想,把两个人的诗合到一起,就显得非同一般了,你觉得呢?”
“是的。”安妮只好违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