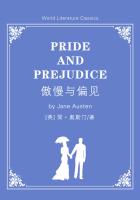“我觉得我必须过来一趟,亲爱的,”科尼莉娅小姐说,“给你解释一下刚才那个电话。我弄错了……真对不起,我的莎拉表姐其实还没有死。”安妮强忍住笑,给科尼莉娅小姐在门廊上找张凳子坐下。苏珊也在门廊上,她在给侄女格拉蒂斯的一个衣服领子钩爱尔兰式的花边,这时她抬起头,客气地招呼道:“晚上好,马歇尔·艾略特太太。”
“今天早上从医院传来消息说,莎拉昨晚去世了。我觉得应该通知你们,因为她是医生的病人。但后来才知道那是另外一个莎拉·切斯,而莎拉表姐还活着,而且可能会继续活下去,谢天谢地啊。坐这儿太愉快,太凉爽了,安妮。我总是说,要想吹吹风就得来壁炉山庄。”
“苏珊和我都很喜欢这迷人的星空。”安妮说着,把正为楠做的粉色平纹薄纱裙子放在一边,双手紧扣放在膝盖上。找个借口偷个懒也并不是不可以。最近这些天,她和苏珊都忙得没有时间休息了。
月亮即将升起来,即将升起的时刻比高悬在夜空还要迷人。虎纹百合在人行道旁“如火焰般明亮”,忍冬花的香气飘荡在天空,像是插着一对梦幻的翅膀在自由飞翔。
“空谷那边有人被谋杀了吗?”科尼莉娅小姐问。的确,从空谷那边传来的号叫声就像是有人在火刑柱上受刑一样。但是安妮和苏珊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帕西丝和肯尼斯一整天都待在那儿,他们要在空谷举办一场盛宴。说起切斯太太,吉尔伯特今天早上去镇上了,所以他应该知道她的实际情况。我很高兴她康复得这么快,这多亏了吉尔伯特,别的医生都不同意他当初的诊断,他还真有点儿担心。”
“莎拉表姐去医院的时候就警告我们说,除非我们百分之百地确信她已经死了,否则就别急着把她埋起来,”科尼莉娅小姐说,她使劲地摇着扇子,她心里暗自奇怪,医生的妻子为什么总是看起来神清气爽,“你不知道,我们一直有点儿害怕,觉得她的丈夫是被活埋了的——埋他的时候看起来还像是活的一样。但等到有人想到这一点时,一切都太晚了。他是理查德·切斯的哥哥,那个理查德今年春天才从罗布里奇搬到这里来,买下了老莫赛德的农场。他是个怪人。他说搬到乡下来是为了图个清静——在罗布里奇他整天都要躲着那些寡妇们。”科尼莉娅小姐本来要加上“和那些老姑娘们”,但是考虑到苏珊的感受,所以就省去了。
“我见过他的女儿思黛拉,她常来唱诗班练习。我们相互还很投缘。”
“思黛拉的确是个可爱的姑娘——很少有姑娘会像她这样动不动就脸红。我一直都很喜欢她。我和她母亲以前是好朋友。可怜的莱斯特!”
“她母亲很年轻就去世了的?”
“是啊,那时思黛拉才八岁。理查德独自把她抚养大的。可理查德竟然是个不信教的家伙!他说女人只是一种重要的生物而已……反正就是那个意思。他总是喜欢信口开河。”
“不过在抚养女儿这个事情上,他看起来做得还不错。”安妮说,她觉得思黛拉·切斯是个非常迷人的姑娘。
“噢,思黛拉是无可挑剔的。我也并不是说理查德就没有头脑。但他对小伙子们就不近人情了——他从不让小伙子靠近他女儿,可怜的思黛拉这辈子连一个男朋友都没有!对于那些想和她交往的年轻人,理查德把他们挖苦得无地自容。他是你见过的人当中最会挖苦人的家伙。思黛拉对他毫无办法……她母亲以前也对他无可奈何。她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总是和人对着干,但是这对母女好像并不明白这一点。”
“可我觉得思黛拉似乎深爱着她的父亲。”
“哦,是的。她很崇拜理查德。当一切称心如意的时候,理查德是个颇受欢迎的男人。但是他应该多考虑考虑思黛拉的婚事。他必须知道,他不可能长生不老的——不过你听他说话时,你会觉得他真是这样想的。当然,他还不是很老——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但是他们那家人都有中风的毛病。等他死后,思黛拉该怎么办呢?我看只有孤苦伶仃,孑然一身,等着老死。”
苏珊一直沉浸在她复杂的爱尔兰玫瑰花样上,这时抬起头,态度坚决地说:“我不赞成老一辈的阻止年轻人自由恋爱。”
“如果思黛拉真的喜欢上了谁,也许她父亲就不得不接受,不会给她施加太大的压力。”
“那你就错啦,亲爱的安妮。只要思黛拉的父亲不喜欢,她就永远不会结婚的。我还要告诉你另外一个人,他的人生也要被毁掉了,那就是马歇尔的外侄——埃尔顿·丘吉尔。他的母亲玛丽下决心,千方百计阻止他结婚。玛丽比理查德更喜欢对着干——要是她是个风向标,吹南风时她就一定会指向北方。你知道,家里的财产都攥在她的手里,等埃尔顿一结婚,财产就得交出来。每次只要他喜欢上一个姑娘,不管怎样,她总会使出各种招数棒打鸳鸯。”
“实际上,这不能全怪玛丽吧,马歇尔·艾略特太太?”苏珊干巴巴地质疑,“有些人认为埃尔顿很花心。我听说别人叫他花花公子。”
“因为埃尔顿长得英俊,姑娘们都倒追他,”科尼莉娅小姐反驳说,“他有时会逢场作戏,然后离开那些姑娘,就当是对她们的一个教训,这怪不着埃尔顿。但有一两次他确实喜欢上了很不错的姑娘,可玛丽每次都把他们活活拆散了。这是她亲口告诉我的,她说她问过《圣经》了——她总是喜欢‘问《圣经》’——她从《圣经》里找了一些章节,每次都拿出来警告埃尔顿,反对他结婚。我看不惯她这种古怪的做法。她为什么不去教堂,像四风港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做个举止得体的人呢?可是她就不这样,她肯定是自己搞出了一套宗教来,坚持‘问《圣经》’。去年秋天,那匹很贵重的马得病了——价值四百元的马呢——她不是去罗布里奇请兽医,而是去‘问《圣经》’,结果翻到一节:‘赏赐的是主,取走的也是主。主的名字应该被颂扬。’要是她去请兽医,她的马是不会死的。想想看,《圣经》的章节竟然被这样滥用,亲爱的安妮。我觉得这是对主的大不敬。我就这样明白无误地告诉她了,但我没讨到一个好脸色。而且她坚持不装电话,当有人开口跟她提起这事,她就说:‘你以为我会对着墙上的一个盒子说话吗?’”
科尼莉娅小姐停下来,她说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她这个小姑子的怪毛病总是让她心烦意乱。
“埃尔顿一点儿也不像他母亲。”安妮说。
“埃尔顿像他父亲……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男人。艾略特家的人永远都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和玛丽·艾略特结婚,虽然他们丘吉尔家跟艾略特家结婚也算是高攀了。玛丽还是姑娘的时候,个子瘦瘦高高,总是神经兮兮。当然她有很多钱——她玛丽姑妈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她了。但这不是他们结婚的理由,乔治·丘吉尔真的很爱她。我不知道埃尔顿是如何看待他母亲反复无常的毛病的,不过他一直都是个好儿子。”
“你知道我刚才想到了什么吗,科尼莉娅小姐?”安妮莞尔一笑,“如果埃尔顿和思黛拉坠入情网,彼此不都是件好事吗?”
“他们没机会相爱的,就算是爱上了,也不会有结果。玛丽会哭哭啼啼,理查德会马上让这个乡巴佬吃闭门羹,尽管他自己现在也是个乡巴佬。而且思黛拉也不是埃尔顿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姑娘——他喜欢娇艳活泼的。而思黛拉也不喜欢埃尔顿这种类型。我听说罗布里奇新来的牧师对她含情脉脉。”
“是不是那个看起来像是贫血,而且眼睛还很近视的牧师?”安妮问。
“而且他的眼睛是对金鱼眼,”苏珊说,“如果他要含情脉脉地看人,那模样一定会很恐怖。”
“至少他还是个长老会教徒,”科尼莉娅小姐说,好像这一点就能弥补他的许多缺陷,“嗯,我该走了。我发现要是我在露水中坐久了,我的神经痛就要发作。”
“我送你到大门口。”
“你穿上那件裙子,看起来真像一位女王,亲爱的安妮。”科尼莉娅小姐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赞叹。
安妮在门口遇见了欧文和莱丝丽夫妇,请他们到门廊坐坐。苏珊已经回屋去给刚回家的医生准备柠檬水了。孩子们也一窝蜂地从空谷回来了,他们一脸困倦,却兴高采烈。
“我赶车过来的时候,听见你们在那里大吵大闹,”吉尔伯特说,“整个村子里的人肯定都能听到你们的叫喊声。”
帕西丝·福德把她浓密的蜂蜜色鬈发甩到背后,对他吐了吐舌头。帕西丝最喜欢“吉尔伯特叔叔”了。
“我们正在模仿咆哮的托钵僧,所以当然要大声叫喊了。”肯尼斯解释说。
“看看你的衬衫都脏成什么样子了。”莱丝丽很生气地说。
“我摔在黛做的泥饼上了。”肯尼斯说,声调里透着一丝得意。他很不喜欢穿妈妈为他做的这些衬衫,洗得干干净净,浆得生硬笔挺,穿起来很不自在,可每次去溪谷村他都得这样穿。
“亲爱的妈妈,”杰姆说,“我能去阁楼拿一些旧鸵鸟毛吗?我要缝在裤子后面当尾巴。明天我们玩马戏团游戏,我要当鸵鸟。我们还要弄一头大象来。”
“你知道吗?养一头大象一年就要花费六百元钱呢。”吉尔伯特一本正经地说。
“可一头想象的大象一分钱都不用花。”杰姆耐心地解释说。
安妮笑了:“我们在想象力方面从来不需要节俭,谢天谢地。”
沃尔特什么也没有说。他看起来有点儿疲惫,心满意足地坐在母亲身旁,将他黑色的脑袋倚靠在母亲的肩膀上。莱丝丽·福德看着他,觉得他天生有着一张天才的脸孔……有一种遥远而超然物外的神情,似乎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灵魂,地球不是他的栖身之所。
在这样一个金色日子的金色时刻里,每个人都感到无比幸福。教堂的钟声越过港口,悠扬朦胧,悦耳动听。月亮在水面上变幻着形状,沙丘闪烁着迷蒙的银光。空气中飘荡着薄荷的清香,那些玫瑰花虽然不在眼前,但它的芳香让人无法抗拒。安妮虽然已经有了六个孩子,但是她的眼眸依然年轻,她如痴如醉地望着草坪,觉得月光下的一棵小伦巴第白杨是全世界最纤细、最顽皮的。
然后她又开始琢磨起思黛拉·切斯和埃尔顿·丘吉尔的事来,直到吉尔伯特问她在想什么,可不可以说出来让大家一起分享。
“我在认真考虑怎样去撮合一对男女。”安妮回答说。
吉尔伯特露出一副绝望的神情,看着大家。
“你们知道,我一直担心这一幕又会重新上演。我已经尽力啦,但是真没有办法改变一个天生的媒人。她对这种事满腔热忱。她撮合的婚姻已经不计其数。要是让我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根本没法睡上一个踏实觉。”
“但是他们都过得很幸福,”安妮抗议说,“我真的是个做媒专家。想想我撮合的婚姻,西奥德拉·迪克斯和路德维克·斯彼德——斯蒂芬·克拉克和普利希·贾德纳——珍妮特·斯威特和约翰·道格拉斯——卡特博士和艾丝米·泰勒——诺拉和吉姆——多维和贾维斯……”
“噢,我真的服了。欧文,我的这个妻子从来都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对于她来说,什么都可以结为一体,连蓟都可以结出无花果的。我看她一直会对做媒乐此不疲,直到她什么时候长大了才会罢手。”
“我想她还促成了另外一桩婚姻。”欧文说,微笑着看着他的妻子。
“那不是我,”安妮赶紧说,“那都是吉尔伯特的功劳。我当时还极力劝阻他别想为乔治·摩尔做手术。做梦都还梦见在百般劝阻他——有几次梦见自己劝阻成功了,醒过来后冷汗直冒。”
“好了,俗话说,只有幸福的女人才能当媒婆,所以里面也有我的功劳,”吉尔伯特得意扬扬地说,“那么,你头脑里的那对新的‘受害者’是谁呢?”
安妮冲着他笑了笑。做媒是一件微妙而谨慎的事情,有些事情连丈夫都不能知道。